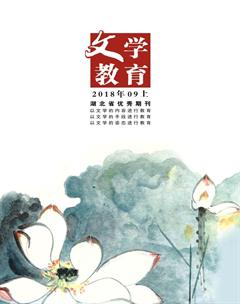論石一楓《借命而生》喜劇性效果的營造
內容摘要:《借命而生》以杜湘東長達二十年的命運浮沉,折射了時代的變遷,顯現了主人公性格的愚頑,并通過對傳統社會角色的消解與顛覆,使文本的敘述呈現出一種喜劇性效果。在其敘述背后,彰顯的是社會權力傾軋下個人奮斗的無力與終結,也使其承載了一定的社會意義。
關鍵詞:石一楓 《借命而生》 喜劇效果 社會意義
石一楓的《借命而生》在揭示時代的致命傷的同時--一個多元混亂的社會表象背后,赫然矗立的無堅不摧冷酷無情的商業邏輯以及由此形成的單向度一體化的價值系統對人的赤裸裸的壓迫”,也對主人公杜湘東性格作了悲憫的嘲諷,使其文本潛藏著一種喜劇性的內核。
一.時代變遷下的荒謬邏輯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有這樣一段話:“歷史不斷前進,經過許多階段才把陳舊的生活形式送進墳墓,世界歷史形式的最后一個階段就是喜劇。”[1]杜湘東身經三個大的變革時代,喜劇色彩在時代的變遷中,隨著價值觀念的更迭以及舊有形式的逝去,也必然會出現。
1.權力:個體命運的操控者
如同福柯在《性史》中所論述的,“權力無所不在,它來自各方”,“權力是多重的力量關系,存在于它們運作的領域,是這些力量關系相互之間的依靠”,“人們始終處在權力‘之內”[2]。社會的發展與權力的運行相始終,杜湘東的命運更是牢牢地被權力所掌控,無論是分配到看守所,還是目睹曾經抓捕的犯人,借助權力以極小的代價洗白自己,都注定了他被權力所吞噬的命運。所以,對警察責任的堅守,只能成為自導自演的不合時宜。權力在其身上的不斷發作,一系列打擊的出現讓人目不暇接,荒謬的喜劇性質凸顯。而權力的轉接又是如此迅速,當洗白的許文革在幾年之后,也成為被權力拋棄的“零余者”之后,讀者也會發出輕微的訕笑:擁有權力者只是一時,在權力之上有更大的權力,個體的命運只是權力選擇的結果。
2.他人:不公事件的助威者
權力侵襲掉了公平,這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偶爾伴隨的沉痛,只是,在讀者為杜湘東憤憤不平之時,目睹這一事件的他者所流露出的習以為常,卻加劇了社會的權力失范。他們的凜然正氣,言辭表象的大仁大義,愈加揭露了“荒唐”的社會自身邏輯,如果將其稱作是一次集體行為的無意識妥協,那么,在杜湘東獨自持槍追捕逃犯后,他們實行的曖昧的暴力行為,卻是一場有意識的集體欺凌。杜湘東在明里暗里的抱怨后,終于陷入到不抓捕逃犯誓不罷休的執念。
3.發展:對時代和個人的不同態度
出逃事件已為人所遺忘,代價是杜湘東升遷的無望,以及永遠被釘子恥辱的十字架。他以畢生的追捕作為洗刷的條件。當尋找到犯人的線索時,他以為可以一洗前恥,其他人卻漫不經心,在欣喜與失落的強烈對比中,讀者似乎瞥見了一個興致勃勃的年輕人,突遭否定之后的茫然無措。欣喜營造得越是強烈,結果就更加耐人尋味,諷刺效果也更加強烈。時代的弊病讓個體的正常行為顯得不合時宜,發展中的社會對時代的錯誤選擇原諒,對個人的失誤永遠銘記,讀者也覺莫名,而此前的閱讀體驗,又使得結果在讀者的預想之中,因此在文本閱讀不斷與心里預想契合的情況下,荒謬性就轉為了一種喜劇性。
如果說時代在發展中呈現出了某種荒謬的喜劇色彩,我們也無法否認,杜湘東自身所裹挾的與時代相背離的價值取向,也無疑會加劇他的喜劇性。
二.命運浮沉中的性格頑疾
現代美學理論家伍夫楹和周朔對喜劇作過以下論述:“喜劇就是對于在特定社會關系和社會沖突中已經喪失了存在根據和價值卻又自以為合理和有價值,或以合理和有價值的假象掩蓋不合理、無價值的本質的自相矛盾、荒唐背理的現存事物的否定性的審美反映。”[3]杜湘東以殘存的個體英雄主義對抗整個時代,本身就有一種唐吉坷德式的愚頑。
1.愚鈍:環境成為假想敵
杜湘東懷才不遇的憋悶,讓他對整個環境采取了一種對抗的姿態。表彰會上的冷漠,工作中的自我折磨,都是一次次顧影自憐的自我展覽。他親手設置了一個假想的敵人--整個環境,并以自我的行動設置障礙物,阻斷與環境的溝通。之后他每一次的想要升遷,都注定了失敗。然而,這種天真的想法本身就帶有一種不切實際。著名哈佛學者王德威在論述《駱駝祥子》中祥子所呈現的喜劇性時也作過以下論述:“祥子受騙于自己的奢望,而這一障蔽從犬儒的角度來看,無疑是十分可笑的。在理想的驅使下,祥子性格中的愚鈍性顯得多于悲劇性。”[4]同樣的,杜湘東也受困于自己的奢望,而忽略了自己親手設置的障礙物。
2.固執:毫無價值的追捕
杜湘東的“好人”標簽源自他對警察身份的尊重,隨著犯人出逃,對職業的尊重轉變為一種迷戀。之后每一次的追捕,都是對高貴職業的尋找,以不合時宜的執念維系作為警察的尊嚴。拒絕發財致富,以一種近乎自虐的方式堅守警察的榮光,這種無意義,卻只暴露出了崇高的虛弱。不惜生命的抓捕犯人,只是心中涌動的激情在作祟。他拽住時代的尾巴,將逃跑事件一次次展演在他人跟前,每一次拼盡全力,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不合時宜。在不斷的受挫中,他其實演變成又一個“老吳”,丟失了曾經的榮光,以手中的職權扣留、糟踐許文革,以一種從前所不屑的手段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固執使他一步步走向了愈加卑賤的境地,他價值的失落,在在引人深思
如果說杜湘東本身所具有的愚鈍與固執的性格,使文本的喜劇性效果得以強化,那么,對傳統社會角色的顛覆與消解無疑會使喜劇效果得到進一步的加強。
三.傳統社會角色的消解顛覆
為了強化文本的喜劇效果,作者借助于反諷這一方法,對傳統的社會角色進行顛覆性書寫。反諷一詞源自希臘文eironeia,指對某一事件的陳述和描繪,包含著與人所感知的表面的意識正好相反的含義,事實與表象之間形成對照齟齬。角色顛覆是其一種。布魯克斯給“反諷”下了一個最普遍的定義:“反諷,是承受語境的壓力”。[5]
1.警察:丟失榮光的“憋悶”者
杜湘東是警察,卻與我們想象中運籌帷幄、揮斥方遒的英雄大相徑庭,相反,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不斷遇挫的憋悶者。傳統社會認知中的正義、勇猛的警察通過一種戲仿式的敘述,被消解殆盡,成為了一個郁郁不得志的繁瑣之人。杜湘東在面對逃犯許文革時的無能為力,也消解了傳統警犯小說的英雄主義神話,他一次次的追捕、調查被置換成了他人眼中的軸與不合時宜,這種敘述手段無疑強化了文本的喜劇效果。作者由此消解了宏大的英雄主義神話,將主人公放置在最瑣屑的日常生活中,在一種顛覆性的敘述中,讀者會心一笑,生起目睹英雄人物貼近地面的快感。
2.逃犯:滿懷激情的“奮發者”
許文革們是逃犯,在常規認知里,與暴力、邪惡相呼應,可是,他們卻是意氣風發的懷揣夢想的理想主義者。作者賦予了兩種角色與社會認知完全相反的內容。姚斌彬被抓捕,在被抓捕后的一笑,毫無疑問地彰顯了自己的勝利,警察不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相反,他在一步步走向逃犯所設置的圈套,成為一枚被計算的棋子;許文革身上的義無反顧的氣概,足以使之凌駕于杜湘東之上。如果說杜湘東以抓捕犯人的執念,贏得了屬于警察的最后一絲榮光,可是當許文革主動回來自首,最后一絲榮光也被泯沒殆盡了。在一次次的較量中,作為象征警察這一符號的杜湘東,總是處于被戲耍的位置,許文革允許“他作為影子纏繞在自己身邊”,在“俯瞰他,揣摩他,戲耍他”,至此,角色的顛覆性所帶來的喜劇效果被推向了高潮。即使在最后許文革自殺之時,杜湘東將其救下,還原了一點警察的榮光,卻發現,他所欣羨的卻是逃犯的活法,“他依稀也想過那樣去活,而許文革卻替死去的姚斌彬活了出來。”杜湘東對許文革表現得越是羨慕,這種反諷的敘述張力越是明顯,喜劇性也表達得愈加充分。
四.結語
《借命而生》這篇小說,通過杜湘東這一充滿喜劇色彩的人物塑造,時代的殘忍性凸顯無疑,而懷揣夢想的年輕人在時代面前的艱難掙扎與負隅頑抗,為我們解讀時代與人性提供了一種參考,如同著名學者孟繁華所評述的,“石一楓能夠用如此繁復、復雜的情節、故事,呈現當下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呈現我們內心深感不安、糾結萬分又無力解決的問題。”[6]時代的發展會隱沒掉個人的價值訴求,但是公平與正義,總體性權力與市場經濟的分離,無疑是消除此種歷史性沉疴的最重要手段。借用社會學家孫立平的論述:“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中國最需要的是一種勇氣,一種能夠正視既得利益格局、沖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轉型陷阱邏輯,走出目前僵局與困境的勇氣。”《借命而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眺望時代的窗口,一種打破僵局的訴求,而這也是這篇文本的價值所在。
參考文獻
1.陳福民《石一楓小說創作:一塌糊涂里的光芒》[J].《文藝報》.2011,(11)
2.石一楓《借命而生》.《小說選刊》[J].2018,(01)
3.孫立平《用公平正義打破轉型陷阱》 《南風窗》.[J].2012(04)
注 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1
[2]福柯.《性史》[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1,91,92,93
[3]伍夫楹.周朔.《新美學教程》[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1,227
[4]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2016,5,168
[5]布魯克斯.《反諷一種結構原則》 《新批評文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6]孟繁華.《當下中國文學的一個新方向—從石一楓的小說創作看當下文學的新變》[J].文學評論.2017(4)
(作者介紹:鐘莎,寧夏大學人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