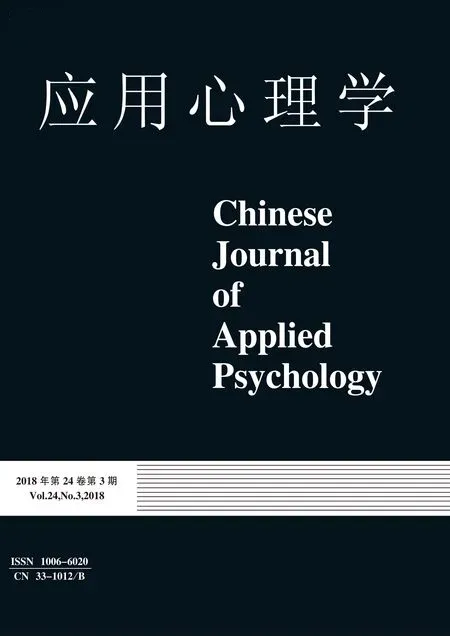共情能減少中國人的差別信任*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心理學系,武漢 430072)
1 引 言
1.1 差別信任
Fukuyama(1996)認為中國社會屬于低信任社會。由于中國人的社會聯系主要發生在家庭中,他們很少信任家庭或家族以外的人。盡管關于中國社會是否屬于低信任社會尚存在爭議(Buchan & Croson,2004),但中國人很少信任陌生人的觀點得到不少研究的支持。如2013年發布的《社會心態報告》顯示,約70%的中國人表示不敢信任陌生人(王俊秀,楊宜音,2013)。李小山,趙娜,周明潔,劉金和張建新(2016)通過問卷調查發現,中國人的人際信任水平從親人、熟人到陌生人依次顯著遞減。梁雅君(2015)通過信任游戲的經典范式發現,無論在意識水平還是無意識水平上,親疏關系對中國人的人際信任產生顯著影響。Song,Cadsby和Bi(2012)發現在中國,情感型信任,即以對交往雙方關系強度的感知為基礎的信任(Johnson & Grayson,2005)比認知型信任具有更大的作用。眾多研究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傾向根據關系親疏決定信任水平,相信親近的人,不相信陌生人。
本文將這種“只信任親近的人,不信任陌生人”的現象稱為差別信任。盡管參照關系親疏決定信任水平合乎情理,但過于依賴這一標準會妨礙陌生人之間的人際合作、信息共享,甚至造成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引發社會沖突。由于差別信任存在諸多弊端,研究者試圖找到一種減少差別信任的心理學方法。
1.2 共情與差別信任
共情既是一種理解和感受他人情緒和狀態的能力,也是在理解他人所處情境的基礎上,產生的與他人相似的情感反應(Eisenberg,Eggum,& Giunta,2010)。一個處于共情狀態的人會穿著另一個人的鞋子,戴著另一個人的眼鏡去體會他所在的世界。研究發現,共情能顯著預測人際信任(Feng,Lazar,& Preece,2004)、社會合作(Rumble,Lange,& Parks,2010)、親社會行為(Stocks,Lishner,& Decker,2009),促進社會紐帶的形成。可以說,共情在社會交往中發揮巨大作用。
信任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基于對他人意向或行為的積極預期而愿意承擔風險的心理狀態(Rousseau,Sitkin,Burt,& Camerer,1998)。本文猜測共情能緩解差別信任有兩點原因。首先,中國人對陌生人持有消極的內隱態度,將陌生人和消極屬性(如懷疑、欺侮)聯系得更緊密(袁曉勁,郭斯萍,2017)。由于共情能顯著減少個體對外群體成員的偏見(Vescio,Sechrist,& Paolucci,2010;Vorauer & Sasaki,2014),對外群體成員產生更積極的態度和行為(Batson,Chang,Orr,& Rowland,2002;Wang,Kenneth,Ku,& Galinsky,2014),因此共情有可能促進指向屬于外群體的陌生人的信任,進而減少差別信任。
第二,情感型信任在中國人的人際交往中發揮重要作用(Song et al.,2012),但在中國人的差序格局式人際關系中,個體與陌生人形成的情感聯結十分疏遠(費孝通,1998)。由于共情能促進個體與他人產生情感聯系,對他人的期望更敏感。因此,處于共情狀態的中國人可能因為在意陌生人的情緒狀態對其表示信任。
為檢驗共情能否增強中國人對陌生人的信任,減少差別信任,研究者一共開展了3個實驗。在實驗1中,被試被安排與一位身份不確定的虛擬人物完成信任游戲。實驗2和實驗3分別通過文章和圖片記憶任務誘發被試的共情狀態,以證明共情與差別信任之間的因果關系。
2 實驗1
2.1 實驗對象
某高校65名學生(男24人,女41人)參與本實驗,年齡在17到28歲之間(M=20.92,SD=2.43)。
2.2 實驗材料
2.2.1 共情誘發材料
參照Batson,Early和Salvarani(1997)啟動共情的方法,研究者編寫了一段300字左右的共情誘發材料。這段材料介紹了一位大學生李瑤的近況:父親患上重病,因此自己無心準備研究生入學考試。
2.2.2 共情狀態量表
采用Baston等人(1997)編制的6項目共情狀態量表,讓被試對自己在“同情的、心軟的、慈悲的、溫柔的、溫暖的、感動的”上的情緒感受強度進行7點評分(1=完全沒有,7=十分強烈)。本實驗中,該量表的α系數為0.82。
2.2.3 信任游戲
信任游戲是測量人際信任水平的常見手段(Johnson & Mislin,2011)。參照Xin和Liu(2013)的方法,本實驗讓被試想象自己手中有10元錢,并可將10元錢的任意一部分投資給李瑤(X,0≤X≤10)。錢一旦投資給李瑤就膨脹為原來的3倍,李瑤再將3倍金額中的任意一部分返還給自己(0≤Y≤3X)。被試投資給李瑤的金額代表他的信任水平。實驗表明,假想信任游戲能很好地預測實際信任行為(Buchan & Croson,2004)。
2.3 實驗設計與程序
實驗1通過2(共情水平:高、低)×2(關系距離:陌生人、表姐/妹)的混合設計初步探討共情狀態與差別信任的關系。
被試首先閱讀關于李瑤的近況介紹,然后在被告知李瑤分別為陌生人、表姐/妹的情況下,與其完成假想信任游戲。隨后,被試對自己的積極情緒(快樂、欣喜,α=0.95)、消極情緒(悲傷、沉重,α=0.80)進行5點評分。最后填寫自己的性別、年齡。
2.4 實驗結果
首先,共情狀態得分最高和最低的33%(n=21)被試被劃分為高、低共情組。獨立樣本t檢驗表明,高共情組的共情水平(M=6.21,SD=0.41)顯著高于低共情組(M=4.21,SD=0.79),t(30)=10.31,p<0.001,Cohen’sd=2.53。兩組被試在積極情緒、消極情緒上均無顯著差異(t(40)=0.07,p>0.05;t(40)=0.17,p>0.05)。
被試在李瑤分別為陌生人、表姐/妹時,對其的信任水平見圖1。2×2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發現,關系距離的主效應顯著,F(1,40)=49.26,p<0.001,η2=0.55。共情水平的主效應不顯著,F(1,40)=2.12,p>0.05。關系距離和共情水平的交互作用顯著,F(1,40)=5.47,p<0.05,η2=0.12。進一步簡單效應檢驗發現,當李瑤是自己的表姐/妹時,高(M=9.43,SD=1.07)、低共情組(M=9.48,SD=1.25)的信任水平沒有差異,t(40)=0.13,p>0.05。當李瑤是陌生人時,高共情組的信任水平(M=7.90,SD=2.30)高于低共情組(M=6.43,SD=2.56),t(40)=1.97,p=0.056,Cohen’sd=0.60。實驗結果表明,誘發共情能增強個體對陌生人的信任,進而減少差別信任。

圖1 當李瑤為不同身份時,被試的信任水平(M±SE)
盡管實驗1發現共情水平與差別信任存在相關,但并未證明兩者間的因果關系。實驗2通過文章記憶任務操縱被試的共情水平,進一步明確狀態共情與差別信任的因果關系。
3.1 實驗對象
64名大學生被隨機分配到共情組和控制組。實驗最后獲得有效樣本55人,其中共情組33人(女18人,M=20.73,SD=2.08),控制組22人(女13人,M=20.18,SD=2.06)。
3.2 實驗材料
3.2.1 記憶材料
共情組的記憶材料是一位留守兒童十分思念父母的故事。控制組的記憶材料是對香料沉香的客觀介紹。兩段文章的字數均在550字左右。
3.2.2 共情狀態量表
同實驗1,本實驗中該量表的α系數為0.95。
3.2.3 信任游戲
同實驗1,僅游戲對象改為參與本實驗的陌生人、關系不錯的朋友、父母。
3.3 實驗設計與程序
本實驗采用3(關系距離:陌生人;朋友;父母)×2(實驗條件:共情組,控制組)的混合設計,其中關系距離為被試內變量,實驗條件為被試間變量。因變量為被試投資給游戲對象的金額。
被試被告知要完成一個記憶力測驗,以避免猜到實驗目的。在完成文章記憶任務和共情狀態量表后,被試分別想象和參與本實驗的陌生人、關系不錯的朋友、父母進行信任游戲。隨后,被試對自己的積極情緒(快樂)、消極情緒(悲傷)進行5點評分。最后,被試需完成一道與記憶內容有關的選擇題,并猜測實驗目的。
3.4 實驗結果
總共9名被試的數據被作廢(7人未能正確回答記憶檢測題,2人猜出實驗目的)。首先,獨立樣本t檢驗表明,共情組的共情水平(M=4.98,SD=0.96)顯著高于控制組(M=1.95,SD=1.11),t(53)=10.81,p<0.001,Cohen’sd=2.96。兩組被試在積極情緒、消極情緒上沒有顯著差異(t(53)=0.71,p>0.05;t(53)=0.80,p>0.05)。
以投資金額為因變量,進行3(關系距離)×2(實驗條件)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表明,關系距離的主效應顯著,F(2,106)=114.89,p<0.001,η2=0.68。實驗條件的主效應顯著,F(1,53)=6.36,p<0.05,η2=0.11。關系距離和實驗條件的交互作用顯著,F(2,106)=3.48,p<0.05,η2=0.06。進一步進行簡單效應檢驗發現,當游戲對象為陌生人時,共情組的信任水平(M=5.88,SD=2.23)顯著高于控制組(M=4.18,SD=2.01),t(53)=2.86,p<0.01,Cohen’sd=0.79;為游戲對象為朋友時,共情組的信任水平(M=7.76,SD=1.97)高于控制組(M=6.59,SD=2.52),t(53)=1.92,p=0.06,Cohen’sd=0.53;當游戲對象為父母時,兩組被試的信任水平沒有差異,t(53)=0.61,p>0.05。結果再次證明,誘發共情能減少差別信任(見圖2)。

圖2 被試對不同游戲對象的信任水平(M±SE)
盡管實驗1、2發現處于共情狀態下的個體愿意向陌生人投資更高的金額。但按照信任的定義,信任者除了對被信任者做出積極行為外,還會預期這樣做能獲得正向反饋。為證明共情增強個體對陌生人的信任,而非僅僅促進利他行為,實驗3將讓被試預期游戲對象返還給自己的金額。
4.1 實驗對象
64名大學生被隨機分配到共情組和控制組。實驗最后獲得有效樣本60人,其中共情組26人(女15,M=21.38,SD=2.43),控制組34人(女19人,M=20.29,SD=2.17)。
4.2 實驗材料
4.2.1 記憶材料
兩組被試均需記憶10張圖片。其中共情組記憶能讓人產生共情的圖片(如一位衣著破爛的小孩用羨慕的目光看著街邊正在玩耍的孩子);控制組則記憶普通的圖片(如一位老人在打籃球)。
4.2.2 共情狀態量表
同實驗1,本實驗中該量表的α系數為0.94。
4.2.3 信任游戲
同實驗1,但實驗對象改為你不認識的同齡人、關系最好的朋友。此外,本實驗要求被試預期游戲對象返還給自己的金額。
4.3 實驗設計與程序
本實驗采用2(關系距離:陌生人;好友)×2(實驗條件:共情組,控制組)的混合設計,其中關系距離為被試內變量,實驗條件為被試間變量。因變量為被試在信任游戲中的投資金額、預期游戲對象返還給自己的金額。
在本實驗中,被試被告知要完成一個與圖片記憶有關的測驗。首先,被試對10張圖片進行記憶,每張圖片記憶5秒。在完成記憶任務和共情狀態測驗后,被試分別想象和不認識的同齡人、關系最好的朋友完成信任游戲。除了回答自己愿意投資給對方的金額,被試還要估計對方返回給自己的金額。最后,研究者讓被試猜測實驗目的。
4.4 實驗結果
首先,獨立樣本t檢驗的結果表明,共情組的共情水平(M=5.26,SD=1.23)顯著高于控制組(M=3.00,SD=1.25),t(58)=7.02,p<0.001,Cohen’sd=1.77。2(關系距離)×2(實驗條件)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發現,關系距離的主效應顯著,F(1,58)=166.96,p<0.001,η2=0.74。實驗條件的主效應不顯著,F(1,58)=0.59,p>0.05。關系距離和實驗條件的交互作用顯著,F(1,58)=5.36,p<0.05,η2=0.085。進一步的簡單效應檢驗發現,當信任對象為陌生人時,共情組的信任水平(M=5.27,SD=2.25)高于控制組(M=4.32,SD=1.55),t(58)=1.92,p=0.06,Cohen’sd=0.50;當信任對象為好友時,共情組(M=8.12,SD=2.18)和控制組(M=8.41,SD=1.78)的信任水平沒有差異,t(58)=0.58,p>0.05(見圖3)。

圖3 被試對不同游戲對象的信任水平(M±SE)
以預期回報以因變量,進行2(關系距離)×2(實驗條件)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發現,關系距離的主效應顯著,F(1,58)=121.92,p<0.001,η2=0.68。實驗條件的主效應不顯著,F(1,58)=0.24,p>0.05。關系距離和條件的交互作用顯著,F(1,58)=3.91,p=0.05,η2=0.06。進一步簡單效應檢驗發現,當信任對象是陌生人時,共情組的預期回報(M=8.60,SD=5.94)高于控制組(M=6.49,SD=2.95),t(34)=1.66,p=0.10,Cohen’sd=0.72;當信任對象是好友時,共情組(M=15.25,SD=7.80)和控制組(M=16.04,SD=6.36)的預期回報沒有差異,t(58)=0.43,p>0.05(見圖4)。實驗3說明誘發共情減少了個體對不同關系距離他人的預期回報差異,因此真正地減少了差別信任。

圖4 被試對不同游戲對象的預期回報(M±SE)
本研究通過3個實驗發現:誘發共情能減少差別信任。在實驗1中,對虛擬人物的共情水平更高的被試,對該人物的信任程度更少受關系距離的影響。實驗2和實驗3分別通過文章、圖片記憶任務操縱被試的共情水平,結果發現共情組被試對陌生人的信任水平高于控制組,表現出更低的差別信任。實驗3進一步證明共情組被試對陌生人有更積極的行為預期,因此是真正地對陌生人產生更高水平的信任。
在以關系為本位的中國文化中,中國人傾向對陌生人抱有消極認識和強烈的戒備心理(袁曉勁,郭斯萍,2017)。但在共情的作用下,人們一方面可能對陌生人的可靠程度做出更客觀的判斷,形成認知型信任;也可能對對方的處境感同身受,形成情感型信任。由于以往研究發現中國人的情感型信任和認知型信任聯系得十分緊密(Chua,Morris,& Ingram,2009),共情還可能同時通過上述兩種心理機制減少差別信任。
此外,盡管本研究證明共情能緩解差別信任,但Cikara,Bruneau,Bavel和Saxe(2014)發現個體的共情水平同樣會受到關系距離的影響。不過,以往研究已經發現一些促進個體對陌生人產生共情的方法,如強調雙方的相似性(Batson,Lishner,Cook,& Sawyer,2005);簡要描述共情對象的心理狀態(Bruneau,Cikara,& Saxe,2015)。本研究的意義在于證明中國人的差別信任并非不可破除的桎梏。對于感性的中國人,誘發共情能夠緩解關系距離對人際信任的不利影響。根據本研究的結果,為獲得重視人情、關系的中國人的信任,強調雙方相似性、表達自己心理感受的“打情感牌”式方法可能是不錯的選擇。
當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研究采用假想信任游戲測量人際信任水平,降低了生態效度。其次,由于研究以大學生為實驗對象,因此結論是否適用于更重視關系、更講人情的年長人群,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證明。為了更清晰地描繪共情與差別信任間的關系,未來研究還可進一步探討在不同信任主題(如分享信息、借錢)下,共情對差別信任的影響,或者明確共情減少差別信任的心理機制。此外,在現代化過程中,依靠制度、規則減少差別信任是否比誘發共情更有效?這一問題也值得深入研究。
6 結 論
誘發共情能提高中國人對陌生人的信任水平,進而減少中國人的差別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