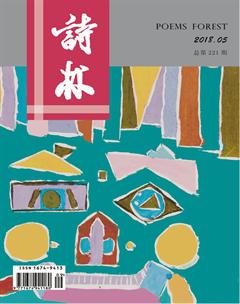暴露的巢 (組詩)
龔學明
雪夜讀父親舊信
三十年的積雪紛紛揚揚
落在臉上的輕
落在心里的重
無聲的歲月悄悄回來
夜中沒有找到源頭
一場雪比雨的喧嘩更真實
遠去的日子
在記憶里不再說話
告訴我真相是什么
天空對一棵樹的牽掛
距離的苦痛由思念填補
快樂和知足實在
母親的病痛飄飄忽忽
兩個男人
一起守護,辨別真偽
雪中有死的音訊
白色的表情不可回避
一個個伯父離去
根的懷舊用比淚的沉重鋪滿
那年我22歲
我向窗外看世界,已感寒意
“父親,不是我不回信
而是我已慌亂”
雪 寶
雪的光映照人間
一年中難得的景致
就像一世中只一個母親
漫天飛舞的雪,在改寫
自然的饋贈;如果苦難也為必須
冬天的漫長和廣大
需要克制:雪是外在的
歡樂,賜予信心
匆忙而堅定
雪寶是我母親的名字
她出生于火熱的八月:外祖父
性情冷峻,對冷中之美癡迷;
母親是他們的第一個女兒
生活不易
外祖父母有詩人的悲憫
母親,熱情如火,清純似水
一輩子的雪不時融化
時間的淚水由多而少
一個冬天的名字,暗喻
路上高高低低,視野荒蕪
她填不平突兀的事故,我
眼見她兩眼茫茫,驚慌無助
今天,我愛融化前的雪
我愛母親:我容忍紛紛揚揚
像我母親的晚年在嘮叨
多么親切,彌足珍貴
故鄉的苦楝子
比圣女果略小的苦楝子
我嘗過:為什么有果子之型
無幸福之甜?我故鄉的
苦楝子苦澀,沉默
我的家族并不蓬勃
長在場院東側的苦楝樹
高挑隨意:在歲月的升落里
風左右苦楝葉的飄拂,沒有人會反對
我故鄉的苦楝樹安逸
不說話的父親長大,成為父親
秋天人世金黃,我們收獲了
一籮筐苦味濃濃的苦楝子
奶頭一般的苦楝子喂養生活
貧困的父母開始祭祀先祖
我沒有見面的血液在燭火中
啜飲,一只只苦楝子在一旁觀看
虛 度
窗外的時間被玻璃隔絕
過往的歲月像這燦爛的陽光
已遮蔽了陰冷
一棵樹被明亮的光片布滿
如我心目中的重要人事
因時間遠去而越發圣潔
我在室內,母親在說話。
早上的光彌足珍貴,坐在溫暖中的
母親不停嘮叨,而我句句在聽
心滿意足
她更多的是回憶:平淡,瑣碎。
只是陳述,不去描繪
但親切舒適,就像近在身邊
只有當她停下的間隙
我心有驚恐:墻上的時針嘀嗒聲清脆
如同追趕,或奔走
而光線移動
不知不覺母親已陷入陰影
當母親再次開腔
她說到了“死”字,在——不經意間。
還 原
藍頭巾:你無處不明亮,
而我由陰影組成。
——扎加耶夫斯基《弗美爾的小女孩》
這個村莊荒草環繞
河灣上風聲很急
而你沒有鞋子
茅草屋頂不遮掩貧瘠
好脾氣的男人
入贅或領養
只有一人時唉聲嘆氣
春天的光照著幸福的眼睛
也賜予陰影中的陌生
沒有母愛的男孩
在孤獨中
尋找不可能的鞋子
但他不愿呼喊,也不哀求
他用沉默作為被子
——如果軟弱源于天生
愛的溪水澆灌開朗的花朵;
強勢的風自以為是
自私自利
花朵低頭,隨遇而生
但這是個春天
你有沒有哭——
死去的爹娘不是親爹親娘
遠方的親娘你喚作好娘
你有沒有哭
空蕩蕩的夜晚
你渴望中的鞋子冰冷
這不是個春風十里的春天
這不是百鳥囀鳴的春天
在陰影中
你的張望驚恐
你溫暖的鞋子要到快20歲穿上
你怎么長大
那個可憐的孩子
是我春天中的父親
暴露的巢
有一只鳥巢,滿是幼鳥,落在地上。
——(美)弗羅斯特《暴露的巢》
這也好:一下子直面人世。
我們生下,從一棵高大的歷史之樹
從家族的巢中
誰也說不清是偶然
還是必然
孩子們的到來
我們期待而又擔憂
有時想多后便覺殘酷
為了一個家族的繼續
將無意義的事情當作
有意義來做
我目睹了父親的離去
聽說了先祖去世時的悲苦
當看到新生孩子的臉滿是
沒有打開的皺紋,緊鎖的眼
我沉默:人生其實早已
設定
只慶幸可以一起走過
蹣跚走出冬天的病危通知
我看到枝葉們迅速長高
鳥試探離巢。
也懂得察言觀色
開始流淚和憂傷
陽光照在墓碑上
——父親兩周年祭
哦,陽光,突然熱烈
如同催促——
受到關懷的青草開始茂盛
在遠方,陽光一定也照在
父親的墓碑上:那是撫慰
還是要喚醒什么
生生不息的力有時隱藏
而現在,它得到指示,交給無處不在的
光和熱:
但父親的骨殖不為所動
一個人的曾經經歷必須保留最堅硬部分
包括尊嚴和榮譽,神圣的親情,愛
他的血和肉沒有離去
他的氣息轉換
為什么一棵新芽初露的木槿樹令我親切
為什么白玉蘭略有憂傷的眼神熟悉
為什么柳絲下垂,隨意而舒適……
我穿行在父親的世界里
輕聲抽泣,淚濕春天
父親當已轉世:兩歲的孩子
他的嘴唇鮮紅,烏黑的眸子里收藏
羊的柔情,虎的沖動;
當看到某一風景,
他有神奇的一瞬
陌生,但似曾來過——今后,
這樣的感覺頻現。
今天啊,我見到的第一個兩周歲
漂亮男孩就是父親
我流著淚說:父親,我們再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