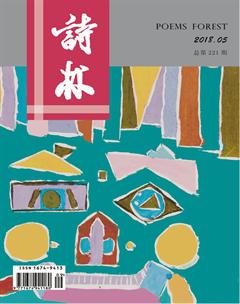空山寂(組詩)
水子
空山寂
整座山,似被長裙裹著
略顯稀薄的朦朧之美,飄在一座道觀的凹凸
間
為一個外鄉女子設置了千百道帷帳
深山的晨景,蜿蜒而陡峭
我們拾級而上,鳥鳴堆積成若干巨石
高調占據愛情中的位置,三角梅
偶爾出現,最終接納了它們迎風的世相
我幾乎忘掉自己是來自北方的人
直到夢幻的針尖穿透絕壁,成為梵音的一個
引子
神性的鳥類,開始晨禱、沐浴、禮佛
喜歡的事,都在石徑上行走
那扇我曾為之徘徊的赭紅門,那條再次
隱身而去的小青蛇,帶來的回聲
從此消失在畫板上
原路返回
聽窗外鳥叫,應該是我每天
做的第一件事:偷偷釋放出漫山遍野的憂傷
在綿綿細雨中一直走,并反復伸出左手
揚起微不足道謎一樣的水霧
我以為這是最浪漫的上坡或下坡
所有人都不在的時候,成群結隊的草木
集體跑過來,用暗香魅惑
突然而至的傷口
它們不停地發出前所未有的低吟
并真理一樣原路返回
念經不知疲倦的麻雀,落在我的前方
我們對視的一瞬,窺見彼此
成為孤兒那些年,從來不懂低頭的美德
弱小不過如此,在更高的臺階上
似乎我是唯一的注目者,在一個地方升起思
想
另一個地方的艾草便會發出苦澀的纏繞
令人時時為之迷路
上坡路
我為一段上坡路著迷
昨日的湮沒,斷開連綿不絕的矮灌木
沿一個短句下山
浮云將山體攔腰抱起,似乎低到了腳下
它們制造出陰暗,又仿佛橫空出世的死結
有高調,務實之牙齒。使空山傾倒,時間成讖
細微的風在我第一句話后面停下
空中拋物一樣,拋出感情的弧形線
有人用現實主義延續它
不存在的,藍霧之城抱緊純凈的嬰孩
最后,熱暴力持續上升
人心偏向我們永遠陌生的云朵,落下
輕柔的細雨來
西山,南山
無需知道是西山還是南山
那時,我第一次被鳥兒從夢里拉出來
看清它們的族群,置錯邊界
原型除外,木紋和香案的虔誠清晰可見
像游人幻化的木棉。花開無聲
花謝時聽到萬籟靜止
山中女神的長發錯位了我走過的山路
佛曲向左移動詩人們的傾聽,到大山深處
他們的眼中盡是消解,是圣徒歸來
我仍保持紅酒的姿態,高腳杯跟緊驚慌
在一個小角落,側目奢華俗世
不愿為任何人飲下虛詞
我還是醉在第二杯酒中——
偶然回憶起晚宴上獨坐的人,所沉寂的
未經持刀人打破的排列
迷 失
我省略掉的——
唯有穿墻而過的緩慢古琴聲
幾朵扶桑花,視我為熟人,而不是
海市蜃樓中神情恍惚的游客
多情一如青苔,倚墻而望
寬廣得遼闊:唇際的歧途,戛然而止的古代
百年榕樹被風吹了百年,氣根懸垂
指向真,也指向假。粗壯的樹干繞過我,繞過
高墻
依然偶遇呢喃的琴曲,愁腸百轉的輪回
我是擅自闖入,下一秒才學會失憶的人
隔世風景未變,體內早已無刺。矮如苔蘚的植 物
每根刺的天真,都與我隔著一條銀河的寬
只是重疊于此刻的濛濛細雨
有人輕輕拋過來古巷的寂靜,再遞給另一群
體內有海的人,完成一次觸手可及的緩慢
琴聲從未傳來
——我承認,我一無所有
青石板踩在腳下,無法還原雨中的私生活
細微的沙沙聲,讓我與一架古風琴并肩而立
當年的老史密斯無家可歸,久居在琴鍵上
與我共持光陰里的舊賬本,向自己宣讀
我們眼內都有沙子,生在孤島
口袋里裝滿人間煙火、大河之波和海潮擊岸
古老的味道,離岸的顫動。那些寄生在
沙粒內的腳印還給踏板一個去處。好像琴聲
從未傳來
實木紋理,私藏著忽左忽右的高低音
我被這種高低音推出門外,過分的安靜
浮現出300年前的曠達,
空巷子總是不見一人
對面壁立石刻垂直墜下百年的孤獨
依然是謎一樣幽深
我真的來過嗎?今人風雅,淡藍的感傷
再大不過芭蕉葉——
侵 入
但是,沒有一個事物
使老榕樹旁邊的一棵木棉,深邃而遙不可及
親近它,花朵與枝干同時失去島嶼
許多礁石凸顯,獲得與失去的雙重效應
我嘗試著走下沙灘,青石如一件舊物
麻雀的蹦跳擋在前方,眼神卻是我們的
那是傳說的引拉,正在移向天空通過海面
遠遠襲來的歡愉,像花朵上掉落的古建筑遺
風
侵入歸途中所有的時間
雨中輪渡
微雨安靜,輪渡船按住海水
浪潮努力向上,涌起的濤聲能讓島嶼轉身
此刻,這浪潮在白色的泡沫中
已接近沉淪。又被一雙大手推向高處
再沉落。我怎么忍心回頭——
站在船邊淋雨
一只海鳥的鳴叫聲,也濕漉漉的
黃昏已遠,博大的海域在我的前方
那陌生的,低于自己的事物
正逆風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