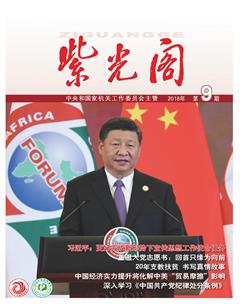讓積極財政政策更加積極
趙福昌
我國通過供給側結構改革,力促低端產能出清和高端新經濟、新動能快速發展,經濟取得積極向好態勢;但經濟轉型升級本身面臨不確定性,又逢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加碼升級,使得當前經濟呈現穩中有變的新情況:2018年上半年投資增速創下6%的歷史新低,其中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長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5個百分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增長9.4%,增速較2017年同期下降1個百分點,投資和消費增勢雙雙低于預期,疊加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值此背景之下,穩增長需求日益強化,已超過防風險成為當前經濟發展的首要矛盾,迫切需要讓積極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效促進經濟穩定發展。
科學把握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性本質
從經濟學概念來說,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擴張性,著力強調基于經濟走勢而相機做的適度政策刺激與擴張的抉擇,常用的手段是增支、減稅等,通常赤字率是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指標。其次,政策效果提升對積極財政政策而言更為重要,擴張性政策如果執行效果不佳,政策乘數和帶動效應就趨于弱化,也難以發揮應有的政策作用,相反,不采取擴張政策而通過結構優化提升資金效率,同樣能夠發揮積極的效果。所以,積極財政政策在強調擴張性政策要素的基礎上,存量資金盤活統籌、結構優化、效率提升等也是政策更加積極的重要方面,在目前防風險與經濟下行雙重壓力下,財政既是穩增長的重要抓手,也是防風險的重要方面,打破資金分配固化、提升財政資金的效率和效益,是積極財政政策更加積極的重要內容。
充分利用積極財政政策的積極(擴張)空間
從傳統的積極財政政策出發,政策更加積極首先體現為擴張性的加碼,包括增支(對應著增加赤字)、減稅等方面。
一是著力加大財政支出空間、加快支出進度。積極財政政策,首先要關注的是赤字率。目前我們的赤字率,基于政府債務占GDP比重40%左右的水平,按照國際通行理論看空間是有的,但是考慮到2018年積極財政政策安排時積極力度不減(2018年財政赤字率2.6%,與2017年2.38萬億元規模相同,但考慮到預算穩定調節基金比2017年多調入1500億元,同時,地方專項債的發行繼續加碼5500億元,等等,綜合看積極財政政策力度不減),年內提高赤字率并非必然選項。在這種背景下,積極財政政策在支出方面發力,更多地應該把年初確定的積極財政政策落實到位,加快專項債券發行和使用進度。基于上半年專項債發行使用進度情況,財政部8月14日發布關于做好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工作的意見,要求加快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和使用進度。要求各地至9月底累計完成新增專項債券發行比例原則上不得低于80%,剩余的發行額度應當主要放在10月份發行,接下來就是要抓好專項債券加快發行和使用進度的落實,在推動在建基礎設施項目上早見成效。
二是著力提高減稅降費空間。第一,流轉稅方面,重要的就是增值稅稅率下調,從17%和11%兩檔分別下調到16%和10%,在當前財政收支平衡趨緊的情況下實屬不易。能否進一步減,需要統籌市場企業需求和財政預算平衡來考慮安排。下一步要做好政策落實,體現減稅效果。第二,企業所得稅方面,包括所得稅減半征收和提高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和范圍等。現在政策已經明確,中小企業減半征收,到2020年以前政策不變,對于中小企業而言減稅力度不亞于特朗普減稅;同時,小微企業還有一個界定范圍標準問題,類似于稅收的“起征點”,已經從經營收入十幾萬元提高到幾十萬元乃至百萬元的水平,范圍已經相當寬了,就減稅力度而言也在加碼。所得稅另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加計扣除,從2018年至2020年底,將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 由科技型中小企業擴大至所有企業,初算全年減收650億元。再者,稅收留底政策落實到位,確保政策紅利盡快釋放。另外,個人所得稅方面,討論中的個人所得稅修法的減稅效果明顯,現在正在程序中,包括起征點的提高、各類專項扣除的完善,需要加快進度。第三,抓好“降費”的落實。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對合理的“費”的降低,要保證在實際工作中不折不扣落實,同時積極探索進一步降費的空間;二是非規范的“費”,按學理說這不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內容,但是,事實上卻增加了企業的負擔,如企業運行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乃至一些需要“打理”的費用等,需切實減輕企業的負擔。
三是充分發揮財政資金政策的杠桿和引導作用。“四兩撥千斤”是財政資金政策的重要功能,在充分發揮財政增支、減稅政策的基礎上,還需要強化財政資金政策的杠桿和引導作用。第一,明晰財政實質,充分利用市場的作用。過去由于對市場化方式調動資源的財政本質說不清楚,導致我國的PPP、政府引導基金等方式在執行過程中出現偏差,又不得不采取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強化管理,帶來一些不利影響。但是,市場的負面清單靠列舉的方式,恐怕難以列舉得完,也就是說靠“堵”達到完善是非常困難的,因此,我們可以考慮對這些利用市場資源的方式,對其財政本質予以明確,比如需要舉債的就納入政府債務限額管理,其余的項目以項目歷年可以產生的現金流為限進行合作或補償,將政府事務和市場自行決策的界限分清,政府管好政府的事務,企業的市場自主管理,比如項目產生收益能夠還本付息的,應該鼓勵,甚至在提升管理的基礎上進一步放松專項債的管控。調動市場資源,形成合力,提升積極財政政策的效力。第二,發揮財政資金擔保作用,助力解決企業發展困難。比如,當前小微企業成為解決就業和經濟創新發展的重要載體,但是融資難、融資貴仍是重要發展制約,財政可以發揮資金擔保作用幫助企業解決發展難題。國家已明確將加快組建國家融資擔保基金,落實不低于600億元基金首期出資,協同省級融資擔保和再擔保機構,支持融資擔保行業發展壯大,擴大小微企業融資擔保業務規模。第三,優化存量結構,提升政策資金積極效果。過去,由于經濟和財政都是高速增長,很多發展的問題都是通過增量解決的,由于存量資金的統籌整合需要打破利益的藩籬,推進有難度而駐步不前。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換擋降速,財政收入由于我國特殊的稅制增速下降更加明顯。過去積極財政政策靠增量調整的思維需要轉變,這就需要打破支出結構的固化,把依托全面績效管理貫穿到預算管理全過程,以績效結果為主要依據,實現財政支出項目的評估退出機制,進而實現部門支出的優化調整,通過存量結構的優化,為積極財政政策創造空間。這就需要財政進一步加強地方預算執行管理、加快支出進度、盤活存量資金,加力積極財政政策,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提升政策效果需要統籌考慮的幾個問題
一是減收與減支同步進行,營造政策的積極空間。減稅降費導致的減收應該與減支并行,積極財政政策措施不能只管減收,不管減支。這就需要減收的同時,積極轉變政府職能,該取消的機構和供養的人員就要取消,否則只是簡單地把取消收費的供養人員簡單地轉為財政供養人員,必然擠占積極財政政策的資金空間,進而影響積極財政政策效果。
二是積極財政政策要對接補短板、經濟轉型。讓積極財政政策效果發揮好,政策的重要發力和落腳點要與經濟轉型升級和補短板結合起來,同時也需要與穩增長的效果集合起來,著眼政策效果,重點做好基礎設施投資,既要有效保障在建基建工程的資金需求,又要推進建設一批重點基建項目,同時還要補發展和民生需要的短板,重點推進補短板、優化結構、促進轉型升級等領域的基建項目,補技術領域、民生領域的一些短板。這樣的要求,實際上就是提高投資的有效性。積極財政政策還要對接高質量發展。財政政策要有助于新產業發展、新動能的轉換,稅收政策總量減稅,但高污染高耗能要結構性加稅,以節約資源,實現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財政支出和稅收優惠政策應進一步調整經濟結構,引導經濟提質增效。
三是做好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政策工具,貨幣政策側重總量調控,財政政策側重結構調控,只有兩者緊密配合、松緊適度,才能形成最佳合力促進經濟穩定健康發展。之前基于防風險放在首位的政策安排,形成了過緊的金融環境,使財政單方面發力穩定經濟增長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做好積極財政政策安排的同時,需要在統籌權衡防風險與穩增長的基礎上,貨幣政策適度寬松,財政、貨幣政策有機協調,合力促進經濟穩定和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