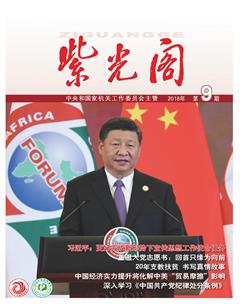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及啟示
梁仁志
官吏考核制度事關行政效率、吏治清明乃至民心向背,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國歷代統治者多重視對官吏的考核。韓非子認為:“明主治吏不治民。”唐太宗李世民把“選用廉吏”作為治國安民的四大方針之一;漢宣帝劉詢曾感嘆:“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他對以稱郡守為代表的地方官吏在國家治理中重要性之高度肯定可見一斑。
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為古代社會的有序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今天的相關制度建設提供了有益的歷史鏡鑒。
發展演變
原始社會是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萌芽階段。中國早在黃帝時期就開始立百官、制典章、舉賢能,堯、舜時期官吏考核制度正式萌芽,《尚書·舜典》中就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的記載,意思是說,舜每隔三年就要對官吏的政績進行考核,經過三次考核,昏庸的官員將被罷免,賢明能干的官員將獲得提拔,于是,各項工作都順利地開展起來。舜正是通過考核官吏,使“優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激發官吏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形成階段。據《禮記》記載,西周實行“以八法治官府”“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等官吏考核制度,即所謂的“八法”“六計”。“八法”是對政府部門的考核,主要考察各部門間隸屬關系是否清晰、是否嚴守部門職責范圍、部門間的聯絡溝通是否遵守相關規定、部門常規事務處理是否得當、各部門是否按章辦事等等;“六計”則主要是從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辯等六個方面對官吏加以考核。春秋戰國時期,官吏考核制度開始形成比較完備的法律法規。秦國實行“上計制度”和“法官法吏制度”,并頒布專門的《為吏之道》。“上計制度”是中央通過預算和決算方式考核地官吏,即要求地方官吏每年年初把賦稅收入預算上呈朝廷,年終再把實際收入和開支損耗等報告朝廷,中央政府兩相比較,就可以判斷出相關主政官員之政績優劣。“法官法吏制度”是指秦國在朝殿、丞相和御史衙門各置法官一名,在地方郡縣衙門各置法官和法吏一名,讓他們學習、核對法令,并負責向吏民進行法律條文的宣傳和解釋工作,以使“吏不敢以非法遇(愚)民,民又不敢犯法”。《為吏之道》是一套較為完整的官吏行為規范,也是官吏考核和升黜的基本標準。其中規定,吏有“五善”,即中(忠)信敬上、精(清)廉毋謗、舉事審當、喜為善行、龔(恭)敬多讓,“五者畢至,必有大賞”;也有“五失”,即夸以迣、貴以大(泰)、擅裚(制)割、上弗智(知)害、賤士而貴貨貝。這些標準既講信念、責任,又講能力、作風,讓官吏為官做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從而做到心中有數、知所進退。
漢魏時期是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發展階段。漢代官吏考核主要有“上計”和“監察”等制度。漢代的“上計制度”在秦國的基礎上有較大發展,它是由地方官吏定期向上級呈報上計文書,匯報地方各方面治理情況。當時,中央設置計相掌郡國上計,郡國設置上計吏、上計掾等掌地方上計。據《漢書》記載,漢宣帝劉詢曾“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漢武帝劉徹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將全國分為十三州部,每州部設一刺史“以六條問事”,負責監察郡國守令,漢朝正式建立國家監察制度。上計制度以賞為主注重考績,監察制度以罰為主注重考失,兩者相輔相成,大大提高了官吏考核的成效。相較于漢朝,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官吏考核制度更趨完善。魏明帝曹叡曾令散騎常侍劉劭定“都官考課七十二法”,制度規定頗為嚴密,惜未得到切實推行;西晉杜元凱“為黜陟之課”,通過嚴明升降制度對官吏加以考核;北魏孝文帝更是“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陟”。
唐代是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成熟階段。唐時尚書省下的吏部位列“六部”之首,“掌天下官吏選授勛封,考課之政令”,其下置主事、司封、司勛、考功四司,其中考功司專門負責文官考核。各級地方官員對其所轄官吏也負有考核之責。與此同時,中央設御史臺負責監察內外諸官,地方設十道負責監察州縣行政。這些機構互相配合,形成較為嚴密的官吏考核體系。唐代考核官吏的主要標準是所謂的“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指“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格勒匪懈”,注重考查官員的德才識能;“二十七最”則注重考查官員的政績。唐代考核官吏的主要程序則分司考、校考兩步。司考即初考,由本部門負責主事官員主持,凡應考官吏須具錄當年功過行能,主事官員當眾宣讀,公評優劣,考績定等,考核結果報送尚書省備校考;校考由尚書仆射和侍郎負責,考功郎中和員外郎主持,并由皇帝親派使臣校之,因此得名。
宋、元、明、清時期是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完善和繼續發展階段。主要制度基本因襲唐制而略有損益。這一時期的官吏考核重點由“任賢使能”逐步轉向加強對官吏的控制,這與當時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趨勢不斷加強是一致的。宋設審官院負責考核京官, 考課院負責考核外官,并置御史臺負責糾察百官。宋朝官吏考核為每年一考,官員三年為一任,任滿根據歷年考核結果決定黜陟。考核標準大體沿襲唐代。宋太祖趙匡胤將“四善”改為三等:政績優異者為上,職務粗理者為中,臨事弛慢者為下;宋真宗趙恒又將“四善”的內容進一步調整,改為公勤廉干、惠及民者為上,干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貪婪者為下。宋朝還強化了監察權,給予御史“聞風彈人”之權,御史甚至可以彈劾宰相。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了近乎全覆蓋的官吏考核辦法,考核分考滿與考察兩種形式。考滿按年資、政績進行考核,考核結果有稱職、平常、不稱職三種,據此決定被考核官員黜陟;考察按貪酷、浮躁、不及、老、病、罷軟、不謹等七條標準執行。為進一步強化官吏考核制度的威懾力和影響力,朱元璋還將考核 制度與禮儀制度相結合,制訂了朝覲之法,亦稱“察典”。每三年舉行一次 ,即于丑、辰、未、戌年舉行,將外官朝覲者分三等,稱職無過者,賜坐有宴;有過稱職者,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不予宴,序立于門,讓官吏有強烈的榮辱感,從而激發他們勇于作為的工作激情,遏制他們無所作為甚至貪贓枉法的不端行為。清朝以“四格八法”考察官員,評定官吏職守、政績情況。“四格”指“守、才、政、年”四項標準;“八法”指:貪與酷者,革職提問;軟與不謹者,革職免官;年老與病者,退休離職;才力不及與治事浮躁者,酌情降調。
主要特點
一是規章制度完備化,考核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從各方面明確了具體標準和方式方法,使官吏考核工作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考核工作流于形式。同時,在具體考核過程中,中國古代統治者普遍重視定性與定量結合。例如,唐朝 在考核地方主政官員時,既以所轄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民風發展的總體狀況對其政績進行定量考核,以衡量其工作能力;又用“四善”等標準,對其政德、政風和為官操守進行定性考核。
二是考核機構專職化,考核工作成為常態、有責可追。秦漢時期的御史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考功郎、考課尚書郎,唐朝的吏部考功司、考功郎中、考功員外郎,宋朝的審官院、考課院,明清時期的考功清吏司,都具有專門考核官吏的職責,體現出中國古代官吏考核機構的專職化發展。通過設置專門的官吏考核機構,不僅使考核工作更加專業化、常規化、系統化,還確立了官吏考核工作的責任追究機制,確保考核工作的系統性、嚴肅性和權威性,對于推動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工作的不斷進步和吏治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考核內容標準化,考核工作目標明確、依據清晰。中國古代官吏考核,非常看重官吏在人口、農業、水利、盜訟、災情、教育、治安等七個方面的實際成績,同時注重在地方的口碑,即要求官吏能夠做到德才兼備。從秦國的《為吏之道》,唐代的“ 四 善 ”“二十七最”,到宋代的“四善”,清代的“四格八法”等,對官吏考核之內容都規定得比較具體、細致和全面,能較為全面地衡量一個官吏的實際政績,使考核工作持之有據、易于執行。
四是考核程序層級化,考核工作層層落實、有效推動。中國歷代官吏考核基本都遵循著大體相同的程序:先由部門主事官員對下屬官吏進行初考;再由京師各部門和地方政府將初考情況具文送至中央主管機關,由中央主管機關委派專職官員進行復考;最后再將復考情況上奏皇帝,由皇帝親自裁定批準。中央考核地方,上級考核下級,考核程序自下而上層層推動、級級落實,使考核工作落到實處。
五是考核過程公開化,考核工作公開透明、防止舞弊。如漢代考課就實行公開評議,即采用會議形式,主考官員向被考核官吏提出各種問題,被考核官吏須當堂作答,再由主考官員結合被考核官吏先前提交的“年度工作總結 ”等相關文字材料,定出考核等次。漢光武帝劉秀就曾親自“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皇帝率先垂范,郡守等地方大吏自然也以同樣方式考核屬官,公開考核官吏在漢代遂成風氣。唐代在考核官吏過程中,主考官員須當眾宣讀應考官吏提前具錄的當年功過行能,然后公評優劣,考績定等。
此外,將官吏考核制度與監察制度有機結合,也是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一大重要創造。
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具有種種優勢,因而能夠有力推動吏治的發展和行政效率的提高,為社會秩序的良性發展起到重要保障作用。當然,由于階級和時代局限性,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制度也存在一定問題。例如,缺乏自下而上的官吏考核監督機制,考核只局限于上級對下級的監督,而缺乏下級對上級、百姓對官員的監督;官吏考核與專制制度相結合,使其具有鮮明的等級性,難以做到同一標準面前一視同仁;中國傳統“人治”社會的特性使得考核的具體規章制度和標準難以落到實處等等。但毋庸置疑,它對于今天建立更加科學、合理、公正、有效的官員考核制度,仍具有重要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