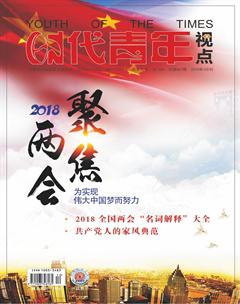熟讀而靜思 善讀而啟智
胡殊佳
西漢劉向盛贊書籍:“書猶藥也,善讀可以醫愚。”微言大意中折射出對世人“善讀”的殷殷期盼。《論語》中亦有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懇切的古語無一不在啟發我們:多讀更要善讀。
蒲松齡、臧克家等人認為多讀書必當有益,而叔本華反彈琵琶,將讀與思對立起來闡釋了權威對于思想的壓迫。事實上在文化淺表化、閱讀碎片化的時代,學思之辯已登堂入室,亟待學者們商榷一番。
書籍如同一劑補品,內化于心而不可囫圇吞食。面對浩如煙海的古典文獻、不勝枚舉的名家力作,何以要飽覽、含英咀華?毋庸置疑,非圣人無一達到這種境界。毛澤東在少年時代讀書極為細致,邊邊角角都不放過,并在書旁都做了注記,收獲了人生中不易的財富。王陽明在閱讀程頤程顥的理學著作時,靜坐七天七夜,于幽篁中悟出心學真諦。讀書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大補”則會“消化不良”,適得其反。高爾基說“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萬丈階梯,高聳入云,仍需拾級而上,才能在點滴積累中勖勉、砥礪前行,不斷進步。
思想如同一架桅桿,在迷茫的大海里撐起舟楫,揚帆起航。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閱讀之道在于靜思。朱熹曾談起讀書之道“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人是會思考的蘆葦,在理性之水的澆灌下才能拔節生長,盡顯風姿。猶記鵝湖之會碰撞出的思想之光,康有為空谷足音般批駁舊經書的言辭。卡夫卡說“書必須是人們用來鑿破心中冰封海洋的一把斧子”閱讀不是用權威同化人類,而是用開闊的視界,為人類提供一個思考的平臺和載體。
盡信書不如無書,我們要敢于質疑,突破桎梏。盲從是一陣洶涌的浪濤,無形中把人推進暗無天日的深淵。書籍自古被視為權威的象征,不辨是非的運用不但不能啟智,還會蒙上人們的眼睛。當然,理性和智慧的光芒從來就沒有熄滅過,敢于質疑書中觀點的大有人在,薄伽丘在《十日談》中用綠鵝的故事深刻揭露了《圣經》的禁欲思想,在黑暗的時代打開了一道裂痕,人類的理性之光便從此滲進來,自此光耀人間。可見,叔本華的觀點大有可取之處。迫于外力的壓迫,人的思想便如彈簧一般萎縮殆盡,最終喪失思考的能力。
朱熹曾說:“讀書之法,在于循序而漸進,熟讀而靜思”書不在多,在于有物。讀不厭精,貴在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