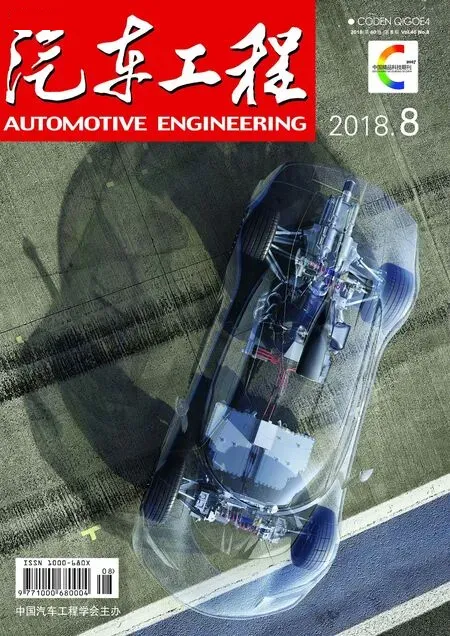基于有限元法的汽車盤式制動器蠕動顫振建模與分析?
張立軍,徐 杰,孟德建,余卓平
(1.同濟大學汽車學院,上海 201804; 2.同濟大學智能型新能源汽車協同創新中心,上海 201804)
前言
汽車制動器摩擦顫振是一種在極低車速和較低制動壓力下,由制動器摩擦振動激發的非線性振動噪聲問題[1-3]。近年來,隨著全球范圍內自動變速汽車的加速普及,和城市交通擁堵情況日益加劇,制動器摩擦顫振問題日益突出,成為困擾工業界和學術界的前沿難題。
制動顫振的發生機理復雜,影響因素眾多,大多數研究認為制動盤-摩擦塊間的黏滑自激振動是引起制動顫振的根本原因[4-5]。為了更深入地分析摩擦顫振的關鍵影響因素,獲得有效的控制措施,建立面向對象的制動器摩擦顫振模型,進行制動顫振性能預測與改進措施評價,正在成為業界的研究熱點問題。
目前,針對制動顫振的仿真主要包括基于多體動力學和有限元方法的瞬態動力學分析。多體動力學模型一般包含制動器以及轉向節、下擺臂等懸架部件[6],部分模型還通過集總彈簧和質量來模擬輪胎[7]。多體動力學方法可再現最基本的黏滑振動現象,但由于摩擦接觸關系過于簡化,仿真結果與試驗仍存在較大差異。摩擦學的最新研究[8-9]發現摩擦特性與載荷、接觸面積分布等因素密切相關。因此,有限元方法對于摩擦接觸特性的建模更加真實有效。例如,Brecht等[10]最早建立了2D盤塊接觸有限元模型,詳細分析了黏滑運動的發生過程,接觸壓力的分布以及極限環特征。Hoffmann等[11]同樣基于簡化的2D摩擦片-剛體有限元模型,重點分析了黏滑運動發生時接觸面內的局部振動與變形特征,表明微觀運動對于宏觀的黏滑振動存在重要影響。Uchiyama[12]等建立了制動角總成有限元模型,分析了接觸壓力、摩擦因數特性、材料彈性模型對制動顫振的影響,但文中對于部件的非線性振動特征分析較少,與試驗結果也只是進行了定性對比。
在此背景下,本文中針對某實際制動器,根據其結構和工作原理對制動器各部件之間的接觸連接關系進行了準確定義,建立了制動角總成的摩擦顫振瞬態動力學有限元模型。其中,文中所指的制動角由制動器總成和轉向節兩部分組成。通過仿真與試驗結果對比,表明所建立的有限元模型具有良好的預測精度,為改進措施的評價提供了重要基礎。
1 制動器顫振有限元模型
1.1 制動器瞬態動力學有限元模型
建模的主要假設條件包括:(1)各部件的材料分布均勻,除摩擦片外,其余部件各向同性;(2)部件的密度、彈性模量為常數,不隨溫度變化;(3)忽略制動盤與摩擦片的磨損,摩擦片處于未使用時的厚度;(4)不考慮接觸面表面形貌的影響,所有的接觸面均為硬接觸,切向摩擦特性與所采用的摩擦模型有關。
某通風盤式制動器有限元模型如圖1所示,包括制動盤、摩擦片、制動背板、制動鉗、保持架、活塞、導向銷等10個部件。模型以六面體單元(C3D8R)為主,局部復雜結構以五面體單元(C3D6R)進行過渡,單元總數58 971,節點總數81 339。全局坐標系的定義如下:制動盤圓周方向為X向,制動盤徑向方向為Y方向,制動盤軸向方向為Z向。為了避免出現尺寸很小的單元,以提高計算效率,對制動鉗和保持架的復雜結構進行了適當簡化。

圖1 盤式制動器有限元模型
1.2 各部件材料屬性定義
采用有限元自由模態分析與部件錘擊法模態試驗結果對比調整方法、確保前4階模態振型一致和模態頻率誤差小于5%的原則,確定各個部件的材料屬性,包括密度、彈性模量和泊松比,如表1所示。其中摩擦片的彈性模量在面內和面外方向有所不同,具有各向異性。

表1 各部件材料屬性
1.3 各部件連接關系定義
制動器摩擦顫振的頻率往往低于制動器系統和懸架系統各個結構部件的最低模態頻率,部件自身的彈性變形較小,但各個部件之間的連接關系具有重要影響。結合實際制動器的結構和工作原理,重點考慮了導向銷連接襯套、制動背板與保持架之間彈簧片的作用,對各個部件間的接觸連接關系進行更準確的定義。表2列舉了各個部件之間的連接關系和各連接關系在有限元仿真軟件中建模設置的方法。各零件連接關系見圖2。其中,導向銷襯套的剛度參數獲取非常困難,現有研究中極少考慮,本文中采用有限元法近似求解其剛度特性(表3),硅橡膠的材料屬性參照文獻[13]。

表2 各部件連接關系

表3 導向銷襯套和彈簧片剛度參數
1.4 摩擦接觸特性
各個摩擦副間的法向力和切向摩擦力通過摩擦接觸模型來實現。ABAQUS提供了一種摩擦因數的數值大小隨相對速度的增大呈指數衰減的摩擦特性模型。當相對速度較小,不考慮黏滯摩擦時,具有良好的仿真精度。本文中特別設計了制動器低速拖動試驗,測量發生顫振時盤塊間的動態摩擦力[14],進而近似計算出動靜摩擦因數。根據軟件提供的公式(式(1))擬合得到圖3所示的摩擦特性曲線,其余摩擦副根據材料屬性和潤滑條件,采用恒定的摩擦因數,詳見表2。

式中:μs為靜摩擦因數,μs=0.3283;μd為動摩擦因數,μd=0.2925;dc為衰減系數,dc=0.0813;為接觸點的相對速度。

圖2 各零件連接關系示意圖

圖3 指數衰減摩擦模型
1.5 邊界條件和載荷設置
制動盤帽部與輪轂之間通過螺栓連接,只存在繞Z軸的旋轉自由度,因此將全部螺栓孔節點耦合到制動盤中心的參考點(圖4(a)),并對參考點設置繞Z軸的速度邊界條件,如圖5所示。針對保持架與轉向節一體化結構,為了簡化模型,縮短計算時間,僅截取實際起到保持架作用的部分,在斷面施加固定端約束,即限制全部6個自由度,如圖4(b)所示。

圖4 部件約束條件

圖5 制動盤速度邊界條件
一般情況下,蠕動顫振發生時的壓力水平大約為0.3~1MPa,仿真中在活塞底面和制動鉗活塞腔端面分別施加大小為0.6MPa的均布壓力,詳細的加載過程如圖6所示。

圖6 制動壓力加載歷程
1.6 分析步設置
制動顫振屬于典型的非線性瞬態沖擊問題,存在復雜的接觸分析,適合采用顯示動力學方法[15]。文中整個仿真過程分為兩個分析步。第一個分析步的時間很短,此分析步用以施加制動時的實際制動壓力,以提高模型的收斂性;第二個分析步對制動盤進行約束,并使制動盤開始轉動。
2 仿真結果分析
2.1 黏滑振動特征
下文將分別從盤塊相對速度、能量轉換關系特性和摩擦副之間的接觸狀態3個不同的角度著重分析黏滑振動的基本特征。
2.1.1 盤塊相對速度
摩擦片黏滑振動特性如圖7所示。由圖7(a)可以看出,制動器表現出典型的黏滑振動特征,盤塊間接觸狀態呈現周期性的黏著或滑動狀態。從圖7(b)和圖7(c)可以看出,隨著轉速逐漸增大,處于黏著狀態的時間逐漸縮短,滑動狀態的時間逐漸增加(摩擦片與制動盤速度相近的時間段變短),1.7-1.8s內摩擦片X向運動相圖(圖7(e))也符合黏滑運動的普遍規律。
2.1.2 能量轉換關系
圖8為發生黏滑振動時各種能量的輸入、耗散和轉化關系,結合摩擦片X向速度可以判斷出黏滑狀態的切換時刻。由圖可見:制動盤勻加速轉動的邊界條件相當于對系統持續做功,提供了能量輸入;在黏著階段,摩擦力為內力,不耗散能量,輸入能量大部分轉化成了彈性應變能;在滑動階段,彈性應變能迅速通過摩擦作用耗散,黏性耗散作用相對較小。
2.1.3 摩擦副接觸狀態分析
摩擦接觸面上各節點根據傳遞的法向力和相對速度的不同,可能分別處于脫離、黏著或滑動狀態。盤塊摩擦副從黏著到滑動過程中接觸面內節點的狀態變化過程如圖9所示。首先需要說明的是由于仿真中無法考慮磨合過程,受到載荷轉移效應的影響,接觸面內會存在很大一部分節點處于脫離接觸狀態(黑色點型)。實際上經過磨合過程,接觸狀態會更加均勻,接觸面積會更加大。
1.500 1s(圖9(a))時,接觸面內大部分節點處于黏著狀態,但在接觸壓力較小的邊緣區域開始出現局部滑動;在下一時刻(圖9(b)),處于滑動狀態的節點大量增加,但仍有很多節點處于黏著狀態;隨后(圖9(d)所示),幾乎全部節點處于滑動狀態,表明摩擦片產生了整體滑動。因此,宏觀上摩擦副從黏著到滑動的過程在微觀接觸面內存在非常復雜的演化過程。首先出現局部滑動,之后再逐步擴展到整個接觸面,同時伴隨有節點狀態的反復變化。

圖7 活塞側摩擦片黏滑振動特性
2.2 盤塊摩擦副摩擦特性
摩擦片與制動盤間法向力和切向摩擦力如圖10所示,施加后,盤塊摩擦副間的法向力基本穩定。隨著制動盤轉動,切向摩擦力逐漸增大,直至產生滑動,開始出現黏滑振動。圖10是發生黏滑振動時切向摩擦力的動態變化過程。結合圖11可以很容易地將每個周期劃分為黏著和滑動兩個階段,從滑動階段進入黏著階段后摩擦力迅速增大,直到超過最大靜摩擦力再次發生滑動。
如前所述,摩擦副的整體與局部摩擦特性之間存在一定的區別和聯系。單個節點的摩擦因數波動范圍與仿真設置參數相同(圖12(b)),某些時刻會小于滑動摩擦因數,而摩擦副整體的等效摩擦因數較小(圖12(a)),最大摩擦因數約為0.31,比仿真設置的靜摩擦因數0.328 2小6%左右,與文獻[11]的結論相似。因為整體的摩擦特性是對接觸面內所有節點積分的結果,從2.1.3小節也可以看出各個節點的狀態在反復變化,不可能同時達到最大靜摩擦力,所以宏觀表現出的摩擦因數比仿真中設置的要小。從瞬態特征來看,單個節點的摩擦因數波動沒有明顯的規律,而摩擦副整體呈現出典型的黏滑特征。

圖9 活塞側摩擦片接觸面節點狀態分布
2.3 制動鉗振動特性
圖13為制動鉗活塞側端部某節點的位移、速度、加速度時間歷程和X向加速度的時頻圖。制動鉗沿X向的位移幅值(圖13(a))最大,Y向次之,Z向的位移變化很小;隨著轉速增大,X向振動速度幅值(圖13(b))不斷增大,其他方向基本不變;X向加速度幅值最大,其頻譜表現出明顯的倍頻特征,隨著轉速增大基頻趨近于91Hz,主要頻率成分集中在100-500Hz。

圖10 活塞側摩擦片與制動盤間法向力和切向摩擦力

圖11 活塞側摩擦片切向摩擦力(0.8-0.9s)
2.4 黏滑振動頻率與系統固有頻率關系
黏滑振動表現為簡諧振動與張弛振動的綜合,當轉速較高時處于黏著狀態的時間很短,振動形式越來越接近于簡諧振動。由此可見黏滑振動的發生頻率與系統的固有頻率之間必然存在一定聯系。
基于瞬態動力學仿真模型,增加線性攝動分析步,提取系統的固有頻率。需要說明的是,線性攝動分析中摩擦接觸面內所有節點只能同時處于黏著或滑動狀態,瞬態動力學分析的結果表明盤塊摩擦副大部分時間處于滑動狀態,其余摩擦副大多數時間處于黏著狀態,據此可以確定線性分析的基準狀態。
由仿真分析結果可以看出:結構的第1階模態頻率為98.6Hz,表現為制動鉗與摩擦片整體沿制動盤切向的振動。隨轉速增大,瞬態分析發現制動鉗振動頻率逐漸接近91Hz,瞬態振型也與第1階模態振型非常相似,證明黏滑振動與系統的固有屬性密切相關。

圖12 摩擦副整體與單個節點摩擦因數

圖13 制動鉗振動特征
3 試驗與仿真結果對比
3.1 試驗設置
(1)試驗對象:1輛裝備自動變速裝置的緊湊型轎車,制動器配置為前通風盤和后實心盤盤式制動器。
(2)測點布置:在左前制動器的制動鉗活塞側端面布置1個3向加速度傳感器,分別測量沿制動盤的周向、制動盤徑向和制動盤面法向的振動加速度,并在左前輪制動器液壓回路中放置油壓傳感器以檢測制動壓力(圖14);同時,在駕駛員右耳側布置1個傳聲器以測量車內噪聲;所有信號通道的采樣頻率為10 240Hz。
(3)試驗工況:采用坡道空擋下坡工況,可以完全排除動力總成和傳動系統影響,僅由車輛沿坡道方向的重力分力驅動起步,希望盡可能產生持續時間長的穩態信號。

圖14 制動鉗三向振動和油壓傳感器布置現場圖
3.2 仿真與試驗制動鉗振動特性對比
本文中通過對比坡道空擋下坡工況制動鉗測點與瞬態動力學仿真中對應位置節點的三向振動加速度、速度、位移和X向加速度的頻域、相圖特征,驗證瞬態動力學仿真模型的正確性。為了便于對比,選取如圖15所示30-36s的穩態顫振過程,此時對應的制動壓力為0.65MPa,考慮到活塞密封圈造成的啟動壓力,實際制動壓力與仿真設置的0.6MPa相近。

圖15 制動鉗三向振動加速度與制動壓力
仿真與試驗結果對比如圖16~圖19所示,制動鉗的三向振動加速度、速度、位移特征非常相似。制動鉗X向運動相圖相近,表明仿真模型可再現試驗中黏滑振動的基本振動模式。從頻譜特征來看,試驗與仿真結果的基頻相近,倍頻成分幅值都逐漸減小,仿真結果以前4階為主,而試驗結果前7階成分(600Hz以內)都比較明顯。

圖16 制動鉗三向振動加速度試驗與仿真結果

圖18 制動鉗三向位移試驗與仿真結果

圖19 制動鉗X向加速度頻譜試驗與仿真結果
仿真存在的不足是仿真結果的振動幅值比試驗結果大3~4倍。下面根據制動顫振的特點和仿真模型對于實際系統所進行的簡化,對可能的原因進行分析。如2.4節所述,制動顫振的發生頻率與系統的固有頻率接近。雖然自激振動與強迫振動的發生機理完全不同,但從振動傳遞的角度看,其與共振又非常相似。當發生共振時,系統的振幅主要由阻尼決定,而仿真模型中沒有考慮阻尼的影響。
實際制動系統的阻尼主要包含以下因素:(1)導向銷連接襯套阻尼,本文中只考慮了襯套的剛度特性,但對于橡膠材料,其必定存在較大的阻尼效應;(2)消音片,盤塊摩擦副是發生黏滑振動的直接部件,仿真中摩擦力的波動幅值與試驗測量結果相近,表明仿真模型對于激勵源的建模是準確的,制動背板(與摩擦片固聯)與制動鉗或活塞之間存在消音片,其彈性和阻尼效應非常大,會使振動傳遞特性顯著改變;(3)接觸阻尼,仿真中全部接觸面為硬接觸,沒有考慮接觸表面微觀形貌引起的接觸剛度和接觸阻尼。
4 結論
(1)基于有限元法的制動角總成仿真模型可很好地再現典型的蠕動顫振現象,仿真與試驗結果的制動鉗振動特性非常相似。
(2)發生制動顫振時,盤塊間呈現典型的黏滑振動特征,隨著轉速增大,處于黏著狀態的時間越來越短。
(3)在一個振動周期內,黏著階段外界輸入能量主要轉化為系統彈性應變能,摩擦力作為內力不做功,滑動階段彈性應變能大部分通過摩擦力做功耗散。
(4)制動顫振是由盤塊間的黏滑振動引起的,但從微觀角度來看,摩擦接觸面內各節點從黏著到滑動狀態的轉化并不是同時發生的,而是首先在接觸壓力較低的區域產生局部滑動,最終擴展到整個接觸面引起整體滑動。這也可以解釋摩擦副整體的摩擦特性與接觸面內單個節點的摩擦特性之間的差異。
(5)黏滑振動的頻率與系統的固有頻率有密切聯系,且發生黏滑振動的瞬態振型也與該階模態振型相似,因此從振動控制的角度考慮,降低系統固有頻率處的傳遞率可以改善制動顫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