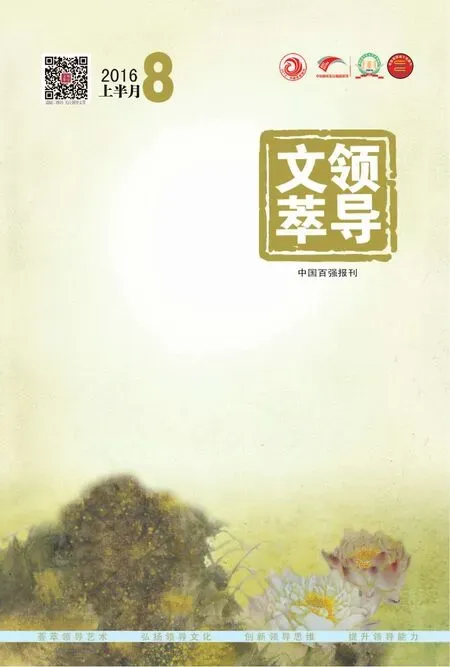《共產(chǎn)黨宣言》中文初版問(wèn)世記
黃顯功
五四運(yùn)動(dòng)前后,隨著馬克思、恩格斯著作譯文的不斷刊登,人們對(duì)馬克思主義的認(rèn)識(shí)也逐漸深化。此時(shí),這些譯文中的《共產(chǎn)黨宣言》的片斷文字和部分章節(jié),已無(wú)法滿足人們的閱讀需求與理論渴望。因此,陳獨(dú)秀認(rèn)為應(yīng)盡快把《共產(chǎn)黨宣言》全文翻譯出版,以適應(yīng)時(shí)代的召喚。
當(dāng)時(shí),擔(dān)任上海《星期評(píng)論》主編的戴季陶也曾計(jì)劃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并在《星期評(píng)論》上連載。《民國(guó)日?qǐng)?bào)》主筆邵力子得知此事后,極力支持,向戴季陶舉薦了陳望道。陳獨(dú)秀當(dāng)時(shí)正在上海主編《新青年》,知道邵力子推薦的陳望道精通英文和日文,同時(shí)具備馬克思主義常識(shí),又是新文化的倡導(dǎo)者之一,也極表贊同。于是,戴季陶向陳望道提供了《共產(chǎn)黨宣言》的日譯本,陳獨(dú)秀請(qǐng)李大釗從北京大學(xué)圖書館借出《共產(chǎn)黨宣言》的英譯本,一起供陳望道作為翻譯的底本。
陳望道,原名參一,字任重。1891年1月18日生于浙江義烏縣分水塘村一戶農(nóng)家。6歲讀于鄉(xiāng)村私塾,后考入省立金華中學(xué)讀書。1915年赴日留學(xué),先后在東京早稻田大學(xué)法科、東洋大學(xué)文科、中央大學(xué)法科學(xué)習(xí),畢業(yè)于中央大學(xué)法科,獲法學(xué)士學(xué)位。1919年6月回國(guó)后,經(jīng)《教育潮》主編沈仲九介紹,擔(dān)任浙江第一師范學(xué)校國(guó)文教師。在校期間積極倡導(dǎo)新文化,因“一師風(fēng)潮”而被迫離開(kāi)浙江第一師范學(xué)校。1919年冬,陳望道回到故鄉(xiāng)分水塘村,在偏僻的柴屋里冒著嚴(yán)寒集中精力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到1920年4月,陳望道譯完了《共產(chǎn)黨宣言》,此時(shí),他接到了《星期評(píng)論》編輯部邀他到滬任該刊編輯的電報(bào)。于是,陳望道帶上《共產(chǎn)黨宣言》譯稿來(lái)到上海,將譯文和日文版、英文版的《共產(chǎn)黨宣言》交給李漢俊,請(qǐng)他校閱,再轉(zhuǎn)請(qǐng)陳獨(dú)秀審定。陳獨(dú)秀對(duì)此譯稿非常滿意,將文稿交給戴季陶準(zhǔn)備在《星期評(píng)論》上連載。不料,該刊因“言論問(wèn)題”遭到查封。
當(dāng)時(shí)陳獨(dú)秀在滬正主編《新青年》雜志,編輯部只有他一人獨(dú)挑編務(wù),于是就請(qǐng)陳望道前來(lái)協(xié)助參與雜志的編輯,與陳獨(dú)秀同住于環(huán)龍路。此時(shí),共產(chǎn)國(guó)際東方局派俄國(guó)人維經(jīng)斯基作為代表來(lái)華,聯(lián)系中國(guó)的共產(chǎn)主義者,幫助建立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經(jīng)李大釗介紹,維經(jīng)斯基抵滬與陳獨(dú)秀見(jiàn)面,共商建黨之事。1920年8月,成立了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共有8名成員,他們是陳獨(dú)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tǒng)(時(shí)在日本)、楊明齋、李達(dá)。因此,陳望道是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陳獨(dú)秀在籌建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時(shí),深感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中譯本相當(dāng)缺乏。因此與維經(jīng)斯基商議,籌措經(jīng)費(fèi)印刷《共產(chǎn)黨宣言》譯稿。經(jīng)維經(jīng)斯基提供經(jīng)費(fèi),在辣斐德路(今復(fù)興中路)成裕里12號(hào)租了一間房子,建立了一家名為“又新印刷所”的小印刷廠,以上海社會(huì)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出版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產(chǎn)黨宣言》。1920年8月,初版的《共產(chǎn)黨宣言》首印1000冊(cè)。此書32開(kāi),封面以紅色印刷書名與馬克思肖像。這部中國(guó)出版的首個(gè)中文全譯本《共產(chǎn)黨宣言》第一次在我國(guó)印刷品上印上了馬克思肖像。此書一經(jīng)發(fā)行,很快售罄。同年9月又印了第二版,改正了首印本封面錯(cuò)印的書名《共黨產(chǎn)宣言》,書封上的書名和馬克思肖像也由紅色改為藍(lán)色。《共產(chǎn)黨宣言》在幾個(gè)月里重印了十幾次,出版一年不到,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在滬誕生。
陳道望譯本《共產(chǎn)黨宣言》為豎排平裝本,以五號(hào)鉛字印刷,內(nèi)文共56頁(yè),每頁(yè)11行,每行36字,每頁(yè)標(biāo)“共產(chǎn)黨宣言”眉題,文中部分專用名詞后注有英文供參照。封面標(biāo)注“社會(huì)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作者標(biāo)注為“馬格斯、安格斯合著”“陳望道譯”。本書正文之后的版權(quán)頁(yè)的出版項(xiàng)標(biāo)注是“印刷及發(fā)行者社會(huì)主義研究社”,出版時(shí)間是“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又標(biāo)“定價(jià)大洋一角”字樣。本書尺寸長(zhǎng)為18.1厘米,寬為12.2厘米。
陳望道所譯的《共產(chǎn)黨宣言》中文初版出版時(shí),雖然在形式上只是一本普通的小冊(cè)子,既沒(méi)有精美的裝幀,也沒(méi)有采用優(yōu)質(zhì)紙張,但是在歷史的洪流中,《共產(chǎn)黨宣言》中文版猶如一面光輝的旗幟指引了中國(guó)馬克思主義革命者披荊斬棘,勇往直前,開(kāi)創(chuàng)了中國(guó)社會(huì)的新天地。毛澤東在1936年接受美國(guó)記者斯諾采訪時(shí)說(shuō):“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duì)于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就是《共產(chǎn)黨宣言》《階級(jí)斗爭(zhēng)》和《社會(huì)主義史》。其他一些中國(guó)革命的領(lǐng)導(dǎo)人也都提到《共產(chǎn)黨宣言》對(duì)自己的影響。
(摘自《中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