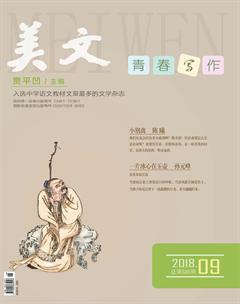老橋
汪鈺
故鄉(xiāng)的小城有一座老橋。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我卻很久以來都不知其名號與修造年代,只知道打我記事起,人們便是以“老橋”“老大橋”來稱呼它。其實,老橋在初建伊始也未嘗就一定有一個響當(dāng)當(dāng)?shù)拿枺驗樗坪醪o那個必要。直到建國后十來年,小城才終于有了它的第二座橋。
然而,我卻總是執(zhí)拗地以為,老橋在建成之初還是須有個名分的,就好像接在老橋一端的老街,街上或大或小的鋪面,總會把各家的字號寫成燙金的木匾,高高地懸于門楣之上一樣。曾經(jīng)乃本城“獨此一家”的中藥鋪,行草寫就的“同德仁”店名,比別家的木匾更為勁健,想來若非一時名家,是不能立就的。
直至近日,讀郁達(dá)夫的《屯溪夜泊》,并刻意搜羅了一些資料,方才明了老橋初建于明嘉靖年間,號為“鎮(zhèn)海橋”。大略時人冀此以名去鎮(zhèn)住怒濤,護(hù)佑行船的旅客與船家,恐怕還有兩岸時時為山洪所苦的居民。不過顯而易見,這“鎮(zhèn)海橋”之名至今也并不昭彰。
當(dāng)然,我斷斷不敢覺無此必要而去責(zé)備古人,但仍不免可惜當(dāng)初工程告竣之際,不曾有人提議依著舊例,利用多余的石板,鐫上橋名及修建緣起、捐資士紳的姓名雅號,并大明嘉靖某某年造的尾款,然后立于橋頭。設(shè)若時人覺得一座普普通通的石橋,實在不是什么可在后世子孫面前稱許夸耀的偉業(yè)豐功,便省去了這許多麻煩,也未可知。
濱水的城市多半是會有一條濱江的小道,小道臨水的一側(cè),還常植一行垂柳,故鄉(xiāng)的小城自然不能免俗。于是,我每喜在春夏的傍晚,來這濱江小路上閑逛,看一個個“夕陽中的新娘”。一株株柳樹總是將素約的腰身極盡能事地俯下,一任細(xì)弱的柳絲在粼粼的波光里遺下淺淺的吻痕。
小道的一側(cè)便是老橋的北端。以我的經(jīng)驗看來,在柳蔭里遠(yuǎn)眺老橋,是再好不過的。當(dāng)此際,平日并不顯山露水的老橋亦有它十二分的姿色。披了殘霞織就的緞面,那留諸水面的倒影蕩漾出熠熠的紅光,雖是徐娘半老,卻仍風(fēng)韻猶存。
若是肯稍稍走動幾步,略略近前,立在橋上細(xì)細(xì)端詳,則又是另一番韻致。上了年頭的青石板再是堅硬,經(jīng)不住春風(fēng)秋雨經(jīng)年的刻蝕,也不免要生出裂隙。裂隙里竄出一綹綹青碧,間或在江風(fēng)中搖曳,有規(guī)律地抽打著滿是綠苔的護(hù)欄,敲出許是數(shù)百年也未曾稍有更動的旋律。這時候,老橋上似乎總會走過那么幾位老者,鶴發(fā)雞皮,執(zhí)一根與他們脊背一樣微有些佝僂的手杖,緩緩地走進(jìn)熔金的暮色里,將身后的影子拖得頎長。我總以為,老橋的黃昏是屬于他們的,而我連同匆匆而過的行人至多不過是無謂的看客。只有軟底的布鞋踏在凹凸起伏的青石板上,才能踩出百年的滄桑。似乎在這里,“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這一句壓卷之作中的名句找到了它最好的注釋。
臨走的時候,半個月亮遠(yuǎn)遠(yuǎn)地從春江盡頭悄悄地爬上柳梢,將模糊的影子投在面前的青石板上。這時,最宜大張雙臂,攬起滿懷的江風(fēng),吟一首“獨立小橋風(fēng)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后”,或在俯仰之間,望盡雙懸的嬋娟,誦一句“江畔何年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老橋的北端,稍稍西向,便是華山。這華山不過百十來米,當(dāng)然比不得西岳的雄姿險絕,不過登高極目,亦可以將小城一覽無余。順著江水緩緩東下,左手邊一溜,幾乎都是晚清民國時期的舊式宅院。
在這些舊式宅院里,住著一個女孩兒。
這舊式的宅子很高,雖大多不過兩層,但層高竟往往可達(dá)五米左右,主體結(jié)構(gòu)系舊時青磚所砌,屋梁樓梯等處亦用了些木材。不知是層高還是建筑材料的緣故,抑或兼而有之,較之別的居所,倒是冬暖夏涼,宜居得多。古宅的前面大多有一方不大的庭院,不足兩丈見方,里面或植一株桃樹,或種幾盆幽蘭,花開之際,馨香繞梁,沁入肝脾,縱是上好的香料也絕難與之匹敵。宅子臨河,掘不多深,即可見清冽的活水,因而幾乎每個小院皆置有一口壓井,供自家吃用。井水跟老宅一樣,冬暖夏涼,雖然自來水早已通了十來年,可那吱扭吱扭的壓井聲仍不絕于耳。
女孩兒就在小院里長大,在一年一度的桃花香里,在一次一次的轆轤聲中,長成一個標(biāo)致的姑娘。高挑的身材,黧黑的皮膚,齊腰的長發(fā),淡淡的眉毛下一對活泛水靈的眸子,天生一副好模樣。
她做了我三年的同窗。
她每日穿著有些褪色的衣衫,背著磨去了紋飾的書包,騎一輛落了些漆皮的單車,穿行在青苔覆面的老橋上。那時,我以為老橋可能不單屬于斜陽里的老者,也是屬于她的。
不知從何時起,她的后面開始多了一個“跟班”。
她的背影,只有在老橋上才最好看。
江南的小城多雨,否則便不能叫做“煙雨江南”了。老橋也常常靜臥在疏疏的雨簾里,享受著純乎天然的淋浴。這時,她若騎一輛單車,劃破蒙蒙的雨霧,橋面上或深或淺的凹槽瞬時即會開出絢美的水花,足可羞煞墻頭檐底的春風(fēng)桃李,然而只一秒,便又重遁于無形,不曾在古舊的石板上遺下一絲唇印。細(xì)密雨絲的有時也會濕卻她的鬢角,梳在耳后的一綹發(fā)絲斜掛下來,更添了十二分的青澀與可人。纖長的睫毛上倘若懸了兩顆鮫珠,斷不會輸與昭陽殿里含情凝涕的那一樹帶雨梨花。
每到晚上,幽微的月光在坑凹的橋面勾勒起纖長的倩影,亦在如黛的綠云里撒下溫軟的流光。她偶一回眸,我即如觸電一般轉(zhuǎn)過頭去,佯裝“在橋上看風(fēng)景”。而這驚鴻似的一瞥,注定將會裝飾我當(dāng)晚斑斕的夢。是的,“在這般蜜也似得夤夜,教我如何不想她”。
凡是美夢,注定是做不多久的。久了,頎長的倩影便不再入夢來看我了。
每次回家,總還是會從橋上過,看一看裊娜的疏柳,拍一拍溫潤的石欄。然而離開時,總不免要帶走一夜的悵然。
學(xué)校這邊也有更為古老,且更著名的橋。數(shù)年間,雖屢屢見邀,我卻始終不曾踏足,只是常常會念叨陸務(wù)觀的兩句詩,“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