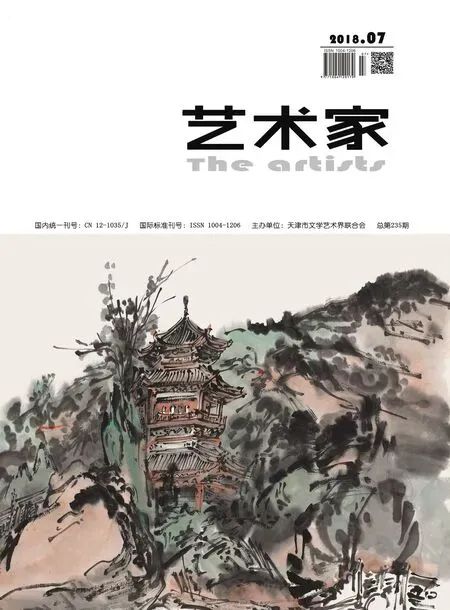現實主義文化內蘊
——論陳凱歌電影人文精神的哲學表達
□王 瑩 中國傳媒大學
一、情感符號及人性困境的深度剖析
陳凱歌早年經歷的社會變遷、政治熏染以及藝術氛圍為他日后的電影基調埋下了伏筆。他早期作品凸顯了鮮明的歷史元素和社會批判性,通過畫面語言、劇情結構以及象征手法的運用表達對于時代的憂患和歷史的反思,情感的符號式表達以及對人性困境的深度挖掘形成其電影獨有的人文情懷與藝術特色。對于陳凱歌來說,電影不僅僅能表現生活,還能將自己的思想與評判融入其中。陳凱歌有著深厚的文化內涵和藝術修養,其電影中總能看到寓意深刻的象征手法,他習慣將對歷史和生活的見解通過史詩的格局表現出來[1]。比如《黃土地》中特殊的畫面構圖,大氣而有深意,象征著被壓抑的人性和無奈。影片中的黃土地一望無際,地形起起伏伏,貧瘠且沉重,這種畫面既顯示了一個民族的堅韌與頑強,又從側面映襯了人們的保守與閉塞。在內容表達上,《黃土地》中有一段表現婚禮的場景,陳凱歌將婚禮作為情感訴求的表達符號,借此體現黃土地人封閉、守舊、落后的特性,也由此暗示了女主人公“翠巧”難以擺脫的悲慘命運。婚禮上村民眼中流露出的麻木與呆滯折射了現代社會進程與根深蒂固的國民性之間的矛盾。由于黃土高原沒有魚,象征自由靈動的“活魚”在婚宴中以被澆汁的“木魚”代替,表現出當地農民思想及心理層面的禁錮封閉等特點。這里的象征手法運用得十分巧妙,陳凱歌通過宴席上的一道菜充分體現了生活在這片黃土地上村民的愚昧和他們對于生活的麻木。他們也許知道這樣的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但卻沒有能力反抗或者說不想反抗,寧愿作為一個被動的屈從者繼續過著一成不變的生活。
在陳凱歌的另一部作品《邊走邊唱》中則通過符號化的情感表達體現了一則與命運有關的人生寓言。《邊走邊唱》是陳凱歌1991年根據史鐵生的小說《命若琴弦》改編的一部電影,影片借助兩個盲人的世界,通過寓言式的故事闡述了一個謊言中的真相。《邊走邊唱》反映出的人生哲理及早已注定的悲劇命運值得我們思考。老瞎子從他師傅口中得知一個可以治愈眼睛的藥方,不過要彈斷一千根琴弦才能取出藥方,不然無效,為此他封閉自己的精神和欲望,把彈琴視為自己的一切,認為什么事都不如“千弦斷,琴匣開”來得重要,他被村民奉為神神,人們經常找他排憂解難。他十分反對石頭和秀蘭之間的男女情愛,甚至一遍遍勸誡石頭將心思放在彈琴上。然而,當他終于彈夠琴弦打開藥盒,卻發現自己心心念念幾十年的藥方不過是一張白紙時,真相瞬時崩塌,所有的希望都化為這一刻的絕望。老人的心情難以平復,陳凱歌將鏡頭轉到老人師傅的墓碑上,手起錘落,墓碑被砸成兩半。他似夢似真,啼笑皆非的一生既可笑又悲涼,仿佛有道不盡的苦楚,訴不盡的哀傷。與老瞎子不同,石頭選擇的是一條截然相反的道路。石頭不在乎結果而更加注重過程,不會為了最后的結果去壓抑自己的本性。在老瞎子死后,村民想要奉石頭為新一代神神,但他拒絕了,他有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價值。影片的結尾出現的風箏鏡頭,也暗示石頭會走上和老瞎子完全不同的道路[2]。
《邊走邊唱》擴大了原著的立意,通過寓言式的故事情節探討了關于命運的人生哲理,對落后的國民性的反思與批判,這也是陳凱歌早期作品的一貫風格。
二、歷史與文化的沖突與反思
歷史背景與社會現實決定了電影創作的文化內涵與藝術風格,“文革”無疑成為第五代導演群體創作的不竭動力和思想源泉,同時也為他們帶來沉重的心理負擔。陳凱歌早年電影作品受到特殊歷史時期的影響,更多體現出對于社會現實的憂慮以及歷史與文化沖突背后帶來的人性的反思。陳凱歌秉承著反思歷史的文化自覺,創作了眾多反映社會現狀、凸顯憂患之感的影視佳作,同時也不斷反思著那段歷史以及整個民族的國民性,這些思考無疑都被他展現在了電影作品當中。與其他導演不同,陳凱歌總能以一種批判的眼光來審視當下人們的生存狀態和這背后所折射出的文化情結。
1993年陳凱歌為了適應經濟潮流,逐漸將電影與商業相結合。在經歷過幾次失敗后,他推出了迄今為止可謂最為經典的影片《霸王別姬》。這部云集眾多明星的電影講述了兩個戲曲演員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所經歷的愛恨冷暖,這中間摻雜了愛情、親情、同門之情甚至還有難以言明的同性之情。這部融合了眾多商業元素的電影,陳凱歌并沒有讓它淪為一部徹徹底底的娛樂片,而是延續了他一貫對歷史、文化以及人性的反思。整部電影以程蝶衣和段小樓的舞臺生涯及命運為主線,深刻反思了歷史和傳統文化,體現了“人生如戲”的真正含義。在歷史的洪流中人們是那么的渺小,片中人物的命運被時代驅使著,個人的興衰也折射出社會的變遷。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場景和場次都是按照戲劇的規范來籌劃的,寬敞的四合院、胡同里冰糖葫蘆的叫賣聲、戲班子等等這些場景都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與內涵,演員的臺詞、表演都有意向戲劇化的方向發展,這些設置都增加了影片的戲劇韻味與深意,也同影片所圍繞的關鍵戲曲表演相對應。程蝶衣和段小樓是戲劇的表演者同時也生活在“人生的戲”中,人生不同于舞臺,沒有設計好的劇本臺詞,所有人物的命運都不能掌控。陳凱歌通過兩人的人生軌跡表現了京劇文化和京劇人的生活,戲班對于小孩子的嚴格訓練和不近人情的懲罰,小石頭因為屢次說錯“我本是女嬌娥”的戲詞被師傅用煙袋燙嘴、小癲子因為渴望出名又怕被師傅責罰而上吊自殺等,這些場景都表現了臺上光鮮的表演者背地里的辛酸,也從側面傾訴了對中國歷史文化以及人生命運的思考。
三、欲說還休的哲學思考與美學意象

陳凱歌的電影始終帶有一種深厚的文化底蘊與哲學思考,對傳統文化元素的使用及角色命運的剖析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與此同時,對東方美學和歷史文化的敬畏與探索是陳凱歌電影的重要內涵,東方美學以民族傳統文化和審美意識為積淀,通過“情于景”“虛與實”“意與境”的美學構造將深刻的哲理寓于藝術作品當中,以期得到“心領神會”的審美效果。被稱為“學者導演”的陳凱歌非常重視對中國傳統美學元素的運用,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清晰感受到濃重的東方色彩和美學意蘊。例如,《妖貓傳》中陳凱歌最大限度地還原了唐朝時期的建筑樣式、景致特點,在色彩、服飾的設計上也極大凸顯了中國傳統元素的文化內涵。此外,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與白居易的《長恨歌》貫穿影片始終,主人公白居易對詩歌創作的精益求精也凸顯了古代文人對于文學與藝術造詣的極致追求。影片以白居易和空海的人物行動為線索,通過二人探尋楊貴妃的死亡之謎,一步步揭示出隱藏在表象背后耐人尋味的反差與沖擊。陳凱歌在影片中打破傳統線性敘事手法,通過不斷穿插、閃回,引領觀眾走進他所構造的“極樂之宴”,并逐漸體悟到他所表達的蘊含在魔幻外衣下的現實主義的批判思維[3]。
在內容創作上,電影雖以唐玄宗和楊玉環的愛情故事為依托,但其想要表達的內涵恰恰在于虛幻背后的殘酷現實。影片中通過幻術營造出的種種意象都被陳凱歌賦予了豐富的內涵表達。“三千寵愛于一身”的楊玉環被視為大唐昌盛的象征,她享受著極度的贊美與榮耀,而這所有的愛戴與稱贊卻又如幻象般虛無,這也是幻術在影片中出現多次的寓意,所謂極樂不過是華麗虛偽的假象。大唐昌盛,楊貴妃代表了無上榮耀,大唐滅亡,她也淪落為罪魁禍首。在臨危關頭,那些說愛她的人全部選擇袖手旁觀,沒有一個人肯為她的死承擔責任。從另一方面來看,唐朝自以為的榮耀又何嘗不是如夢似幻的假象,極樂之宴是大唐危機來臨前最后的警鐘。陳凱歌通過隱喻的手法,將唐朝歌舞升平的虛假繁榮描繪得淋漓盡致,與之后的落魄景象形成鮮明對比,透過虛實相生的情節描繪以及層層遞進的人物內涵,將自身的哲學思考隱晦地傳達給觀眾。
結 語
金丹元先生在《電影美學導論》中指出彰顯民族尊嚴,標榜時代印記是中國電影美學的文化內涵。與注重形式而忽視內在的導演不同,陳凱歌電影創作時刻秉持著對歷史的關注,對社會的批判,對世人的警示,對自我的反思。他堅持把中國傳統文化與東方美學元素運用到作品當中,凸顯人文精神在作品精髓中的核心價值,表達一種對人性意義的關懷以及最深層的哲學思考。可以說,陳凱歌是一位充滿憂患意識的藝術家,他的電影不是為了故事而故事,而是將深刻的人文情懷與批判精神貫穿其中,創作出一部部高質量的時代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