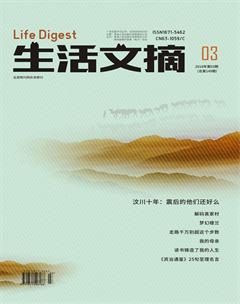舊扶風
劉新科
扶風縣位于陜西省中西部,全縣總人口約四十二萬,民風淳樸,是西周王朝的發祥地,也是秦漢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一。
扶風人過去居住以瓦房為主,房子多為“一邊蓋” ,純磚木結構的甚少,一般都是土墻土屋,造型具有地方特色,古樸大方。
房子里邊有火炕,火炕用柴火焙燒,冬天的夜晚躺在上面特暖和、極舒服。過去,上了年紀的人冬天睡覺不鋪褥子,俗稱“溜光席。”
過去,上了年紀的人很少穿襪子,光腳坐在炕上,煙鍋(旱煙袋)叼在嘴里,慢慢吸吮,品味的就是那“日出勞作,日落休憩”的平凡歲月。
已婚女人俗稱“屋里人”,做飯,喂豬,抱娃,收雞蛋。灶房一般的鍋臺和火炕連在一起,燒鍋的時候火炕也就熱了,冬季,坐在炕上吃飯,隔著鍋臺就把飯碗接給男人的手里,親切、熱火。燒鍋的燃料來自于莊稼收獲之后的秸稈,整個飯菜可口、環保。
吃完飯,掌柜的(男主人)坐在炕上吸上幾袋旱煙,悠然自得,俗話說:“飯后一鍋煙,勝似活神仙。”女人家則洗鍋、洗碗,開始喂豬、喂牛。
冬日里燒炕、燒鍋的主要燃料來自于莊稼的秸稈,男人就去田間地頭收拾柴草。
要使火炕一次燒了能耐到天亮,關鍵取決于燃燒過后的溫度保持,這主要得力于灰燼覆蓋的“煨底”。這“煨底”,就是秋、冬季草木枯黃之后的腐殖質,拿上很老了的竹掃把,將其掃在一起,捎帶一些細土,培在還未燃燒盡的火上,可以耐一個漫長的冬夜。
過去的扶風莊稼人辛苦,無論多大歲數,只要還能動彈就要自食其力的勞作,拉上架子車給自己弄些燒炕的柴火,冬季有熱炕,說啥也不換。
舊時,少有自來水,吃水要在自家院里打井、用轆轤費力去攪,吃水艱難。解決的辦法就是打井、打窖。打井,井水就是地下水;打窖,就是收集雨季的水,是雨水。打窖、打井都是鄰里幫忙,也不掙錢,只要有飯吃、有酒喝,足矣。
過去的扶風莊稼人冬天、雨天、晚上九點前,主要的業余生活就是諞閑傳、說評書。諞閑傳就是閑聊的意思,幾個人湊在一起,一壺“陜青茶”就足以聊上大半天,天南海北,東拉西扯,無所不談。說評書即稍有文化的莊稼人評說“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隋唐演義”、“岳飛傳”之類。小孩們常常聽得入神,真可謂“廢寢忘食”。
由于燒炕和燒鍋所用的燃料很多,所以家家戶戶就有了柴垛子,夏季收獲的麥草也用來喂牲口。
過去的扶風莊稼人最重的活兒莫過于 “踏胡基”、“踏墻”。
胡基也就是我們書面語所說的“土坯,”過去蓋房所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就是土坯,所蓋的房子也叫“土坯房。”這種活兒既是力氣活,也是技術活。過去,扶風農村有人以此為業,走村串戶,給人“踏胡基”掙錢。
“踏墻”即是“打墻”也。扶風有句諺語:“打墻的板子上下翻。”現在的意思是不要瞧不起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人可是做幾節子活的啊!所以不要把話說絕,把事做絕。可在實際生活中,“踏墻”,即是為了自家“小院子”的完整和安全。墻在鄉下有院墻和房墻之分。一般要將土用水泡濕,圈板或者椽子填土,用石槌子打擊夯實即可。
過去的扶風農村人最幸福的時刻莫過于殺豬,多在距離春節很近的臘月二十三殺豬,一是為年關吃肉做準備,二是要祭奠灶神。親親鄰里都來幫忙,將豬先捅死放血,然后燒一大鍋開水澆燙,剔除豬毛,煮肉熬湯,弄得全村子香味四溢。
年關近了,各種有關吃喝的準備工作就要到位。扶風人的口味偏“酸、辣”,所以用牲口拉碾子鍘調料或人工推碾子碾辣子,將干辣子角碾成辣子面,以備春節何平時吃用,就是人們經常要做的一件家務活。而要碾辣子就要將剛剛收獲的新鮮紅辣椒用繩子串起來,掛在房前屋后的樹上陰干,這樣才能碾成辣子面。
過去的棉花緊缺,百姓穿衣常常是個大問題。所以過去穿衣服就是將衣服穿得干凈、整潔就行了,“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因而,縫補衣服就是扶風農村婦女的基本活計了。
扶風的農村婦女心靈手巧,能扎花,會剪紙,總是把簡陋的農舍收拾得漂漂亮亮;把家里自產的糧食拾掇得干干凈凈,農婦一般使用的是簸箕,簸箕一閃一閃,塵土就飛走了。
夏收、秋收,常常是過去農村最繁忙的季節——又要收、又要種。一家人常晚上忙著剝玉米,俗稱“爆玉米。”就是將玉米棒上的玉米粒一粒一粒剝下來,準備磨面。剝不完的玉米棒要掛在架上,這一活兒叫架玉米。作用使之風干。
啊!遠古的扶風,淳樸的鄉民,但愿你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高歌猛進,永遠淳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