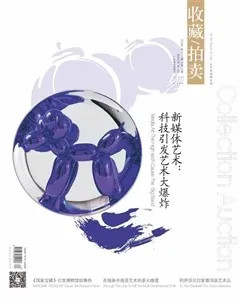尋找影像藝術的未來形態
雨葭



從攝影與電影的發明,到電視技術的出現,再到數字與互聯網技術對影像的轉化與激發,今天各種類型、不同層面的影像無處不在,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生活世界與觀念世界,以至于我們已完全可以把當代社會叫作“影像的社會”。面對這個前所未有的社會新形態,當媒介進入轉型階段,我們也試圖尋找影像藝術的未來形態。
2017年12月中旬,“復相·疊影——廣州影像三年展2017”在廣東美術館展出,將攝影和影像放在個非反映論的維度上,強調影像自身的獨立,并強調不同影像媒介之間的復合性與跨越性。展覽邀請了來自中國、日本、新加坡、法國、西班牙、瑞士、巴西、阿根廷、秘魯、美國等國家和地區58位藝術家的作品參展,從中可以窺當下藝術家在影像領域的探索面貌。展期至2018年3月8日。
前世今生:從攝影到影像
這個占據了廣東美術館全部12個展廳的大展,是從觀眾自己的眼睛開始的。
1號廳一進門右手邊有個小小的臺子,里面有個u形鏡,這樣觀眾俯視這件裝置作品時,左眼看到的是自己的右眼,而右眼看到的是自己的左眼,藝術家蔣竹韻用最簡潔的視覺技術和觀眾開了個小小的玩笑。而在展覽中,許多作品都顯示出對技術與媒介本身的欣然嘗試。
“廣州影像三年展”是有前緣的,它的前身是歷經三屆跨越六年的“廣州國際攝影雙年展”,曾經是廣東美術館除“廣州當代藝術三年展”外另一個重要的學術品牌,也是國內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國際性攝影雙年展之一,但由于種種原因,自2009年后,該項目度停止。廣東美術館于2017年重啟這一項目,并將“廣州國際攝影雙年展”正式更名為“廣州影像三年展”,最為核心的變化就是將“攝影”改為了“影像”。
廣東美術館重新開啟了對攝影,或者更廣泛地說,是對影像作為一種復合媒介其自身的獨立性以及與不同媒介之間所產生的跨越性思考。于是,如伺梳理靜態攝影與其他影像媒介之間彼此碰撞和交融所帶來的跨學科實驗,就成為了我們關注和研究的一個新方向。
本屆廣州影像三年展“復相·疊影”正是基于這樣的立場而形成。
策展人鮑棟在展覽新聞發布會中對這一主題進行了闡釋。在他看來:“‘復相在哲學層面上提示了一種多重的、共時的存在,一種非中心主義的與去本質主義的世界,旨在將攝影和影像放在一個非反映論的維度上,強調影像自身的獨立性并平行于現實,甚至生產著不同的現實;‘疊影則強調著不同影像媒介之間的復合性與跨越性,鼓勵我們去面對今天各種紛繁的攝影與影像的實踐,更為開放、包容地把握攝影這個傳統概念,并且把攝影與其他影像藝術之間的關系作為一個新的討論空間。”
換言之,從“攝影”向“影像”的過渡,預示著從原來的“社會人文的攝影”延伸為更具包容性和學科性的“視覺研究的影像”。
廣東美術館館長王紹強表示:“本次展覽一邊是對過去的梳理和回顧,一邊是對當下的關注及對未來的探索,我們將在動態、變化和發展中去建構中國當代影像藝術發展的歷史鏈條。我們希望這次展覽能夠給予觀眾嶄新的觀看體驗,并向社會提供廣泛而全面的素材資源,引發公眾對于影像藝術的關注,進一步推動中國當代影像藝術的實踐與研究。”
全球范圍的“影像”再議
本次展覽分主題展和特別展兩個部分。三位策展人中,亞歷杭德羅·卡斯特羅特、鮑棟、曾翰各自代表國際化、全國化和地方化,構成了兼具國際和本土的“鐵三角”。另外,三人背景剛好互補,“曾翰對本地珠三角的攝影史作了很好的梳理和研究,這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們要找一個這樣的人很難得。而亞歷杭德羅是觀察國際攝影的發展動態,特別是南美洲一些發展;鮑棟是獨立策展人,思潮相對比較新,也策劃過不同的攝影的展覽和當代藝術的展覽。”王紹強說道。
主題展分別就照相機、照相館、暗房、鏡像、仿象、類像、畫框與畫冊、自然與生命等母題展開對傳統攝影與圖像傳播、消費的反思;與此同時,當媒介進入轉型階段,試圖尋找影像藝術的未來形態,并在全球范圍內勾勒出影像藝術的可視化圖譜。
作為照相術最早傳入中國的城市,廣州地區從清以降的攝影發展定程度上可以作為中國在攝影藝術發展的完整典型案例。在廣東美術館的三樓,是此次影像三年展的特別展“鏡像粵影”,由國內策展人曾翰策劃,這是一種“回歸”的嘗試。展覽從粵港澳地區攝影史研究和對全球化歷史的平行關系的思考出發,通過15位/組藝術家的作品,討論攝影與歷史、攝影與社會、攝影與我們所處時代的關系,跨越一百多年的影像創作歷程,這部分展出了清末阿芳(1839-1890)原版蛋白照片;約翰湯姆遜(1837-1921)19世紀末來華拍攝的“中國和中國人的影像”;何藩(1933-2016)1950-1960年代所拍攝具有獨特幾何美學以及東方古典唯美意境的“新都市攝影”等。
策展人鮑棟認為:“在今天討論影像藝術,最重要的不是討論作品,而是需要把焦點從作為生產鏈末端結果的作品上移開,進入整個生產—傳播一消費的運作機制中去,進入藝術實踐對這種生產方式中各個環節的認識與回應中去。這種問題意識的轉變,帶來的不僅是方法論的調整,更重要的是討論場域的擴大,從而能夠真正地面對‘影像社會的議題。”
(編輯/雷煥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