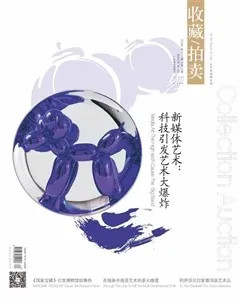袁付國:藝術家就是要不斷創造新語言
李冬莉



中國不乏眾多偏居一隅、名滿地方的名家能人。他們在當地的藝術圈、收藏圈里,有著明星一樣的光芒;他們的作品往往一畫難求,還沒完成就被提前預定了。身在河北邢臺的袁付國便是如此。但他卻遠遠不滿于此,年近60走上當代水墨之路,大膽而心無旁騖地做著自己的探索。袁付國說:繪畫是什么我不關心,人是什么,宇宙又是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表達的。
對于袁付國來說,在三十歲之前,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變成一個畫家。畢竟,一開始連喜歡畫畫對于他來說都是有些奢侈的。
小時候對于畫畫的認識,來自看小人書,有錢了就買小人書看,喜歡得不得了。自己也跟著畫幾筆。但母親很不喜歡他畫畫,也堅決不讓他畫畫。那時候父母還受老思想的影響,斷定畫畫未來肯定是吃不飽的。母親曾說過最狠的話是:“你要是再敢畫畫,就把你的手打斷。”初中畢業后,袁付國像每一個年輕人一樣進入社會參加工作,當時也沒想過有一天自己能成為一個畫家和藝術家。
或者他是一個天生要畫畫的人,不管過程中的路如何走,終點卻注定了要落在畫筆上。工作后,他一步步做到了一家國有企業的裝飾公司經理,裝飾公司畫效果圖,他對手下人畫得不滿意,自己沒學過,但一上手就能畫得好。有一年去廣州出差路過一個畫廊,在20世紀90年代,畫廊里的一張水墨畫賣2000塊錢,當時他非常吃驚,覺得怎么這么貴。畫面的畫風他自認也能畫得出來,也可以畫。后來回到邢臺,袁付國就跟領導申請,說自己想畫畫。以前的老領導都很愛才,說想畫就畫吧。這成了他走上繪畫之路的開端。
而這一開始就再也沒能停下來。一開始他的畫傳統寫實,尤其是牡丹很有名,一畫難求。后來竹子、小魚、小鳥這些傳統樣式都很受追捧。雖然他是從傳統中開始的,但作為一個半路出家的野路子,他并不在乎別人的看法和說法。也不計較名利,類似改換風格會不會不受歡迎之類的都不在他考慮范疇,畫到一定程度,他就再也不愿意畫這些了。“有人說,老袁,給我畫張芍藥吧。我就說不會畫了。其實就是不想重復,想不斷找到內心里的新可能。我是半路出家,沒有負擔,怎么變怎么改都可以。一成不變的是畫家,而藝術家應該是一個探索自己的內心和世界的關系的過程,需要不斷提供新的視野和角度的可能性。我的個性里也不喜歡重復。”
學習規范是為了擺脫規范
2006年,袁付國在北京待了一段時間,看了很多展覽。看得多了,發現都不是自己想要的。后來就不再看畫展,也不再看評論。“中國文人畫學古人,但古人出門就是山,寫生就是眼前的風景變成畫。我們不是古人,現在的人出門就是坐飛機乘高鐵,視野不一樣。西方的藝術家通過美術館的訓練,有自己的傳統,人家的傳統也不是我們的傳統,但藝術的境界卻是相同的。我要做的就是‘出了山門打師傅——找到自己。會畫畫的并不都是藝術家。”
之后,袁付國開始畫佛像,也畫得很好,喜歡的人也非常多。這些都是他繪畫探索的一個過程,也是他希望從古人和宗教那里得到養分的過程。但這些都不是他追求的終點。甚至走到現在的抽象畫,創作當代水墨,將丙烯顏料融入彩墨中,進行一種全新藝術語言的嘗試,都是不斷演變而來的,也不是終點。
“我學規范的目的是為了擺脫規范,而不是變成規范。”
袁付國的作品經歷過幾次大的風格變化,在走向當代水墨的嘗試之前,佛像系列和花鳥系列在他的收藏群體里一畫難求。他的作品如他的人一樣,有著不同于當時年齡的反差感,年輕的時候特別強調作品的古意和典雅,而年近60之后走上當代水墨之路,大膽得如同毛頭小子,全然不在乎是不是能被市場接受,能被過去的老藏家認可。
“只懂滿足市場需求的是設計師,工藝師。藝術家就是要不斷超越,創造新的語言。”他對這個話題有著自己清醒的認識。
有認識是一回事,真正改變是另外一回事。畢竟,拋掉過去的若干年積累的,不顧后果一往無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中國有著龐大的水墨畫收藏市場,尤其是地方性的收藏市場。這是多年審美積累的特色,也可以說是局限。說到市場層面,袁付國的不同之處則在于,他很在乎“懂他”作品這件事。話不投機的想要買作品的客人談都不要談,這樣的性格拒絕了部分投機客也收獲了很多真情實意的朋友。從作品的層面,讓他也有這種自信。除了國內和當地,在海外特別是美國市場,他的作品也擁有眾多擁躉。
在過去繪畫古意風格作品的時候,他也喜歡像古人一樣到處走走看看,讓自己立于自然和當下的場景中。他說,一個藝術家筆下畫出的東西,是心里的,而心里的又來源自眼睛和感受。好的藝術家都是情感表達的高手。沒有這種能力,很難畫出好的作品。藝術之難不僅在于它相比較一般的專業性更強,更在于,它是一種人類深層次精神性的孤獨,無可逃脫,并且很難從教學和他人的成功案例中獲得安慰。
做藝術家就是不斷否定自己的過程
無論是傳統的水墨畫家還是當代油畫畫家,能夠像袁付國一樣,完全半道出家,甚至自身因為當年父輩的歷史原因,只上到了初中便輟學進入社會,唯一正式的訓練來自于1999年的天津首屆中國畫高研班短訓,卻又能在藝術之路上走得如此深遠的,堪稱絕版。
從半路出家,完全靠著自己對藝術的熱愛和天賦,不斷跟自己死磕,不斷否定自己,到進入寫實、寫意,再到如今抽象畫的當代水墨之境,袁付國不斷超越著自己。他在北京短暫的停留后,很快就回到了故鄉邢臺。作為邢臺地區的名人,他很少見客,只是關起門來專心作畫。經常畫得多,毀掉的也多。不滿意了毀,不喜歡了毀;今天喜歡,明天不喜歡了,依舊毀。他說,做藝術家就是不斷否定自己的過程。
取得一些小成就很容易,難的是推翻過去的成就不斷挑戰自己的新可能。尤其是到一定年紀之后得到市場認可的藝術家,從這一點,越發顯得袁付國的難得、可貴。他似乎決定了藝術之路上要給自己找不痛快的,不斷嘗試著當代水墨的縱深邊界。中國的水墨畫很難突破,光材料本身就有諸多限制,不像油畫和丙烯的變化、層次這么多。
當代水墨是中國傳統水墨藝術與西方現代藝術觀念雜交的一個當代藝術品種。在保留中國傳統筆、墨、紙等的基礎上,大量運用西方現代藝術創作中的一些方法和觀念進行創作,和傳統中國畫已有相當大的距離,和傳統筆墨的概念也有很大區別,在形式上的追求大于傳統筆墨的內涵,甚至有南轅北轍的感覺。
這種強烈的反差和實驗性,對于無論在什么位階上進行創作的藝術家都是不容易的。尤其是身處邢臺這樣的小城市,這里并不具備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創新氛圍,那種很多可能都被支持和鼓勵,仿佛只要你敢想敢做,世界自然會給你條路去走的寬松環境。而在小城市里成名雖容易,約定俗成的傳統力量也更強。這也是為何很多年輕人要走向大城市的原因。
從2016年開始,袁付國仿佛不受任何壓力影響似的,也不管之前那些喜歡他作品的收藏家懂還是不懂,只是心無旁騖地按照自己的節奏創作全新的水墨作品。不知道他背景的人,會以為這是一個對西方藝術史有著深入了解的年輕藝術家,用色大膽,筆墨隨性。每一處細節都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對于這一點,他想得很通透,“想要從事藝術之路,想要獲得成功,就不能只想著怎么畫,為什么這樣畫。而是先要改變意識,忘掉自己,不斷接受新的觀念,社會上各種變化和新的理念。”
他說,抽象水墨畫的嘗試,并不僅僅是繪畫,而是想表現的人對宇宙的再認識,是一個藝術家應該有的思想。“2004年,我開始在水墨里加入丙烯,當時也是要找各種可能性。我的作品都是宣紙、丙烯、墨的綜合媒材。有時候,你不把自己限制在某一種類型和狀態里,世界反倒寬了”。
藝術是宇宙觀的表達
因為在當地很有名,很多年輕人找他來取經、學畫。袁付國跟他們都說,你們跟著我學不了技法,只能學做人。藝術是教不了的。“現在中國的藝術教育有一個問題,尤其在水墨畫的教育上,就是兒童畫的教材和成年人的教材大體相同。但繪畫不是群眾運動,不能一擁而上。如果只講怎么畫,找本書照著畫就行了,但藝術創作需要的是自己去感受生命的靈性。語言無法解釋,也不能通過數字來理解。”
“對于我來說,繪畫是什么我不關心,人是什么,宇宙又是什么,才是我真正要表達的。繪畫只是我表達的一種方式和方法。會畫畫的并不都是藝術家。只有藝術家才能創造出表達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方法。”這也才是藝術家和藝術創作者的區別,前者看重方法論和價值觀的一致性,而后者更強調方法論的簡單呈現。
“想要從事藝術之路,想要獲得成功,就不能只想著怎么畫,為什么這樣畫。而是先要改變意識,忘掉自己,不斷接受新的觀念,世界上的各種變化和新的理念。”
當代水墨的改造非常之難,中國的水墨畫本身就很難突破,光材料本身就有諸多限制,不像油畫和丙烯的變化這么多。對于袁付國來說,有時候一張畫的顏色調出來特別漂亮,想再調一張,調不出來了,全靠當時的感悟。
傳統水墨作品中,沒有純粹的黑,靠墨的深淺來表現不同意境。而袁付國的作品里,黑就是黑,再用其他的顏色來破黑,所有顏色的分量都是平等的。充分利用丙烯和彩墨的肌理效果,在東西結合的藝術中,產生新的跨界語言。
袁付國認為,恰恰是這種難和挑戰,讓他覺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思的事,因為這種有意思,讓他的心態一直年輕著。(編輯/李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