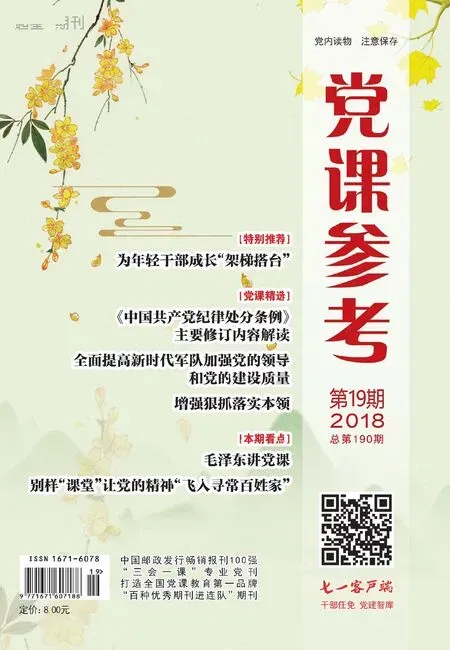瑞典怎樣有效防治腐敗
〉〉〉〉〉王鵬 賽明明

瑞典是北歐最大的國家,也是權力監督體制較為完善、行政效能較高的國家之一。近年來,瑞典官員貪污率低于十萬分之一。
完善高效的反腐敗法律體系
瑞典的反腐敗法律體系完備縝密,為有效防治腐敗提供了法律保障。從20世紀初開始,瑞典就按照預防與懲治相結合的原則,陸續制定了一系列反腐敗法律,包括《行政法》《反行賄受賄法》《審計法》等,對政府部門和公務員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作出了明確具體的規定。《反行賄受賄法》將賄賂犯罪的量刑起點額定得很低,規定收受價值超過200瑞典克朗(按現有匯率,約合人民幣150元)的禮物就可被視為腐敗。1977年,瑞典又修改了刑法關于受賄罪的規定,將犯罪主體由公務員擴展到企業職員。1999年,瑞典再次對該條款作出修改,使犯罪主體擴展到歐盟委員會成員、歐洲議會成員和歐盟法庭的法官。2012年,瑞典在立法中增加了“對資金管理不善或者過于濫用資金罪”,加大瑞典跨國企業海外反腐力度。與此同時,瑞典堅持嚴格執法,有效避免了腐敗問題上的“破窗效應”。比如,1995年10月,時任瑞典副首相薩林因為使用公務信用卡購買了價值幾十克朗的巧克力食品,被迫辭職。由此可見,瑞典對官員腐敗行為的容忍度極低。
獨立公正的權力制約和監督制度
瑞典實施了很多權力制約和監督制度,實現了全面監督、全民監督。其中,比較特別的是社會監督制度。瑞典的民眾和媒體都有很強的監督意識。在他們看來,反腐敗不但是專門機關的責任,而且是全社會都應該關注的事。如果一個官員的生活水平高出收入水平,很快就會有人舉報,隨后就會有監察官和稅務官調查。同時,瑞典民眾還通過參與工會等社團組織發揮監督作用。這些組織代表會員的利益,一旦發現政府部門和公務員有不作為或腐敗行為,就會向議會監察專員投訴,或者告之媒體。為了防止惡意舉報,瑞典相關法規明確,凡有惡意舉報者,一經發現就將給予其“最低信用級別”。而被列為這個信用級別的人,今后若想在銀行貸款、找到理想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
高度透明的政務公開制度
透明與公開是瑞典政府行政的一條主要原則。根據這項原則,政府或公共機構的書面公務資料、公函、財務報告等,只要不屬于國家機密,都必須向公眾和媒體開放。政府研究工作、法院開庭審判,公眾如果有興趣,可以隨時旁聽。目前,瑞典民眾有權查閱任何一個政府部門的文件(涉及國家安全的除外)。為限制政府對政務公開信息的自由裁量權,瑞典還專門制定了《保密法》,極為詳細地列舉了哪些信息屬于國家機密,這就避免了相關部門以國家安全為由,故意向公眾隱瞞非涉密信息。
較為完備的社會福利制度
瑞典是高福利、高稅收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公務員以權謀私和貪污受賄的主觀動因。一方面,“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政策、完備的社會福利和保險制度,保障了公務員的基本生活。瑞典財政預算的四成多用于社會福利事業,地方政府的比例更高。在瑞典,無論男女、老幼、有無工作,無論是否對瑞典有所貢獻,均享受基本統一的社會福利,包括國民基本年金、國民健康保險、社會救助、失業保險、兒童補助、子女撫養貸款、老年福利、房租補貼、帶薪假期、免費教育等。另一方面,重稅使國民失去追逐財富的動力。為維持高福利支出的財政需要,瑞典實行了高稅收制度,個人所得稅負平均達到38%,整體稅負達到50%,是“世界上稅負最高的國家”。“高稅收”和“高福利”,實際上是把“收入均等化”作為第一戰略目標。社會福利開支的增長意味著由國家或社會“包”下來的消費項目增多,包括公務員在內的民眾,缺少“發財”的誘因和動機。
誠實守信的廉潔從政文化
瑞典歷史文化傳統悠久,重視道德教育和社會道德體系的建立,崇尚公平正義和誠實守信,成為防治腐敗的重要支點。瑞典中學普遍開設法律道德課,注意培養孩子的社會正義感和民主法治意識,使孩子從小就養成遵紀守法、純樸誠實、行為規矩、重諾守信的好習慣。瑞典《教育法》中,在價值觀部分提出“學校工作人員鼓勵對學生價值觀的尊重”。2005—2014年被定為“可持續發展教育的十年”,通過教育提高國民文化水平、法律意識。可以說,公平正義和誠實守信的價值觀已經深入骨髓,成為瑞典國民自覺遵守的社會準則和行為規范。國民重視誠實的品質,同時,政府重視誠信體系建設。瑞典的征信系統全國聯網,個人如果有不良行為,就會被作為污點如實記錄下來,并在求學、就業、晉升時產生影響。公務員一旦涉腐,不僅個人將付出慘痛代價,家庭和家族都將蒙羞。所以,瑞典人從小都以有不良記錄為恥。這種視公正和誠信為生命的文化氛圍,推動了瑞典整個國家的道德建設,也造就了一支廉潔奉公、不搞特權的公務員隊伍。
(摘編自《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