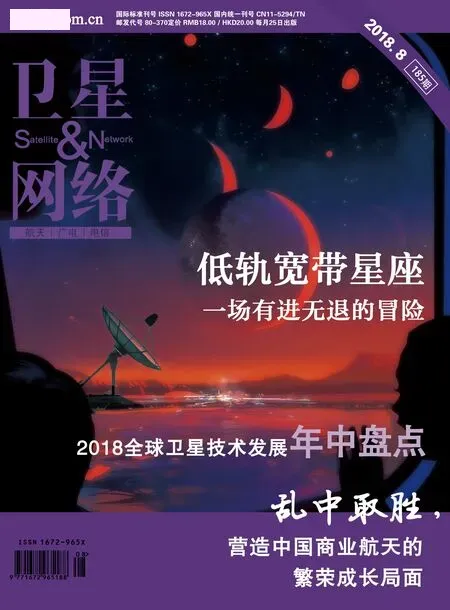對(duì)話雨菲:開(kāi)創(chuàng)航天產(chǎn)業(yè)新模式正當(dāng)其時(shí)


本月,《中國(guó)航天報(bào)》記者采訪了航天加工程技術(shù)研究院常務(wù)副院長(zhǎng)劉雨菲。采訪內(nèi)容以《開(kāi)創(chuàng)航天產(chǎn)業(yè)新模式正當(dāng)其時(shí)》一文,刊登于《中國(guó)航天報(bào)》2018年8月17日《觀點(diǎn)》欄目。本刊特將當(dāng)時(shí)的完整采訪記錄整理成文,呈獻(xiàn)給讀者。
Q:您看好今天的中國(guó)商業(yè)航天嗎?假以時(shí)日,會(huì)不會(huì)像互聯(lián)網(wǎng)一樣,出現(xiàn)國(guó)際級(jí)的企業(yè)和領(lǐng)軍人物呢?
A:首先,我們所談的商業(yè)航天,是特指現(xiàn)在的民營(yíng)商業(yè)航天。按現(xiàn)有思路發(fā)展下去,中國(guó)的商業(yè)航天或許會(huì)有一定的經(jīng)濟(jì)規(guī)模,但很難有體系性的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
我之所以敢于下這個(gè)結(jié)論,是出于商業(yè)航天本身的屬性。航天事業(yè)本身就是以顛覆傳統(tǒng)為傳統(tǒng)的,這一點(diǎn)與互聯(lián)網(wǎng)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如果商業(yè)航天的企業(yè)和從業(yè)者不打算顛覆傳統(tǒng),而是追隨或者重復(fù)其他人,那么就談不上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
我們?cè)诤教飚a(chǎn)業(yè)中耕耘了20年。這是一個(gè)不缺乏精英的行業(yè),但是基礎(chǔ)工業(yè)的落后,以及過(guò)去奉行的多年不變的“趕超世界先進(jìn)水平”思維,讓整個(gè)行業(yè)在商業(yè)模式創(chuàng)新上缺乏創(chuàng)新性和積極性。哪怕近幾年商業(yè)航天概念興起,這個(gè)問(wèn)題也沒(méi)有顯著改觀。相當(dāng)多商業(yè)航天企業(yè)負(fù)責(zé)人大談“中國(guó)的馬斯克”就是典型表現(xiàn)。中國(guó)是中國(guó),美國(guó)是美國(guó),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方向和道路不可能一樣。我們聽(tīng)過(guò)哪個(gè)成功的互聯(lián)網(wǎng)領(lǐng)袖自稱要做“中國(guó)的貝索斯”、“中國(guó)的拉里·佩奇”嗎?為什么沒(méi)有人自稱要做“商業(yè)航天的馬化騰”?
總體來(lái)說(shuō),整個(gè)商業(yè)航天界,有一大部分企業(yè)都是在試圖重復(fù)國(guó)有航天企業(yè)的歷程,為自己建立衛(wèi)星、火箭的研制生產(chǎn)能力;一小部分航天應(yīng)用企業(yè)有著一定的創(chuàng)新意識(shí),很多想法和實(shí)踐也很有價(jià)值,但是對(duì)整個(gè)產(chǎn)業(yè)很難起到顛覆的作用;還有少數(shù)企業(yè)在渾水摸魚(yú),利用“商業(yè)航天”這個(gè)題材弄錢、弄地皮。
至于國(guó)有航天企業(yè),兩大航天集團(tuán)剛剛改制,其實(shí)質(zhì)性的內(nèi)部改革還在逐步推進(jìn)之中,尚且還沒(méi)有發(fā)生可以稱為顛覆的事情。要想改變國(guó)有企業(yè)的運(yùn)行模式機(jī)關(guān)化、高管任免政治化、營(yíng)銷模式僵化等問(wèn)題,還有很長(zhǎng)的路要走。一些有志于航天的其他軍工集團(tuán)公司,他們雖然擁有比較強(qiáng)的經(jīng)濟(jì)實(shí)力,但目前也處在技術(shù)上的摸索階段,還談不上商業(yè)模式。
如果按照現(xiàn)有的模式發(fā)展下去,或許個(gè)別企業(yè)可以成長(zhǎng)為能夠盈利的、具有一定細(xì)分市場(chǎng)占有率的成功者。實(shí)際上,已經(jīng)有一些企業(yè)的營(yíng)業(yè)收入加起來(lái),會(huì)是一個(gè)可觀的數(shù)字。不過(guò),這里恐怕還不會(huì)出現(xiàn)BAT那樣的巨頭,也不會(huì)出現(xiàn)華為那樣具有國(guó)際影響力的行業(yè)性領(lǐng)軍企業(yè)。
“菲”說(shuō)不可
· 航天產(chǎn)業(yè)在商業(yè)模式創(chuàng)新上缺乏創(chuàng)新性和積極性。相當(dāng)多商業(yè)航天企業(yè)負(fù)責(zé)人大談“中國(guó)的馬斯克”就是典型表現(xiàn)。我們聽(tīng)過(guò)哪個(gè)成功的互聯(lián)網(wǎng)領(lǐng)袖自稱要做“中國(guó)的貝索斯”、“中國(guó)的拉里·佩奇”嗎?為什么沒(méi)有人自稱要做“商業(yè)航天的馬化騰”?
· 要開(kāi)創(chuàng)商業(yè)航天,首先要開(kāi)創(chuàng)對(duì)行業(yè)的認(rèn)識(shí),包括:對(duì)于新航天時(shí)代的認(rèn)識(shí)、對(duì)航天商業(yè)化和商業(yè)航天的認(rèn)識(shí)、對(duì)商業(yè)航天管理體制的認(rèn)識(shí)和建議、對(duì)軍民融合的認(rèn)識(shí)。
Q:那么,我們有沒(méi)有可能把中國(guó)的商業(yè)航天推向一條高速發(fā)展的軌道,像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業(yè)一樣起到顛覆性的推動(dòng)作用呢?
A:我們中文里有一個(gè)詞叫做“危機(jī)”,也就是所謂的機(jī)遇和挑戰(zhàn)并存。這個(gè)詞匯最近也得到了美國(guó)航天界的認(rèn)可,因?yàn)樵谟⒄Z(yǔ)中表示危險(xiǎn)的“Crisis”這個(gè)詞,并不包含機(jī)遇(Opportunity)的意思,而中文中的“危機(jī)”這個(gè)詞的內(nèi)涵更加豐富。對(duì)于我們的商業(yè)航天來(lái)說(shuō),不好的局面未必是壞事,只要應(yīng)對(duì)得當(dāng),完全可以成為開(kāi)創(chuàng)商業(yè)航天的良好機(jī)會(huì)。
現(xiàn)在,同樣是機(jī)遇和挑戰(zhàn)并存的時(shí)刻。上文所討論的問(wèn)題,已經(jīng)是行業(yè)普遍認(rèn)識(shí)到的。這意味著大家都不滿意,所以就擁有了顛覆格局的原動(dòng)力。如果形成了某種能夠運(yùn)行下去的機(jī)制,要改革和顛覆,反而就很困難了。
要開(kāi)創(chuàng)商業(yè)航天,首先要開(kāi)創(chuàng)我們對(duì)行業(yè)的認(rèn)識(shí)。想明白了,才能堅(jiān)決行動(dòng)。這里提出四個(gè)方面的認(rèn)識(shí)問(wèn)題:對(duì)于新航天時(shí)代的認(rèn)識(shí)、對(duì)航天商業(yè)化和商業(yè)航天的認(rèn)識(shí)、對(duì)商業(yè)航天管理體制的認(rèn)識(shí)和建議、對(duì)軍民融合的認(rèn)識(shí)。
Q:您可以詳細(xì)解讀一下這四個(gè)認(rèn)識(shí)嗎?
A:有關(guān)這四個(gè)認(rèn)識(shí),我在過(guò)去的社論中已經(jīng)做了詳細(xì)的闡述。這里列舉一些核心的觀點(diǎn)。
我們?nèi)缃褚呀?jīng)來(lái)到了新航天時(shí)代的門檻上,這個(gè)時(shí)代完全可以和曾經(jīng)的大航天時(shí)代相提并論,其對(duì)人類文明進(jìn)步的影響甚至更大。航天產(chǎn)業(yè)能否發(fā)展壯大,決定了中國(guó)人能否在太空開(kāi)發(fā)時(shí)代,在宇宙中取得應(yīng)有的地位。宇宙被王希季院士等老一輩科學(xué)家稱為“第五空間”。沒(méi)有強(qiáng)大的航天產(chǎn)業(yè)和強(qiáng)大的商業(yè)航天,就沒(méi)有進(jìn)軍太空這個(gè)人類活動(dòng)新領(lǐng)域的資源和能力,就不能順利、大規(guī)模地開(kāi)展空間資源開(kāi)發(fā)、外星資源開(kāi)發(fā)、星際移民等活動(dòng)。
對(duì)中國(guó)來(lái)說(shuō),航天商業(yè)化有了一定的物質(zhì)基礎(chǔ)。中國(guó)已經(jīng)擁有了多顆通信衛(wèi)星所組成的空間通信基礎(chǔ)設(shè)施,高分辨率對(duì)地觀測(cè)衛(wèi)星系統(tǒng)正在發(fā)射和運(yùn)行,北斗衛(wèi)星導(dǎo)航系統(tǒng)已經(jīng)初步形成了運(yùn)行能力。但商業(yè)航天卻有極大的缺口,無(wú)論在技術(shù)基礎(chǔ)、投資、人力資源、政策環(huán)境等方面都嚴(yán)重不足。因此在中國(guó)推動(dòng)商業(yè)航天的發(fā)展,將面臨更大的困難,意義也因此而更加重大。
對(duì)行業(yè)管理和宏觀經(jīng)濟(jì)調(diào)控部門來(lái)說(shuō),商業(yè)航天是新生事物,沒(méi)有歷史遺留下來(lái)的條條框框。而且中國(guó)行政部門對(duì)于體制機(jī)制改革的積極性、適應(yīng)性要比美國(guó)高得多。美國(guó)有關(guān)部門在商業(yè)航天立法及管制政策改革上的有益經(jīng)驗(yàn),或許在中國(guó)會(huì)帶來(lái)更大的成效。其中最重要的一條經(jīng)驗(yàn),或許是:不要把產(chǎn)業(yè)管得太死。管理部門要專注于保護(hù)誠(chéng)信企業(yè),驅(qū)逐借機(jī)炒作、純玩資本以及跑馬圈地變相行房地產(chǎn)之舉等的害群之馬。
對(duì)于企業(yè)來(lái)說(shuō),軍民融合是一場(chǎng)新的創(chuàng)業(yè),是企業(yè)走向永續(xù)經(jīng)營(yíng)的必由之路,需要大家從頭開(kāi)始。短期內(nèi),軍民融合將為軍工企業(yè)帶來(lái)更多市場(chǎng)機(jī)會(huì),讓軍工技術(shù)更多地在民用市場(chǎng)上發(fā)揮作用、形成經(jīng)濟(jì)效益。長(zhǎng)期來(lái)說(shuō),軍民融合發(fā)展可以讓軍工企業(yè)更加深入地植根于國(guó)民經(jīng)濟(jì)、更充分地參與社會(huì)發(fā)展,成為永續(xù)經(jīng)營(yíng)的事業(yè)和品牌。今后一段時(shí)間里,國(guó)有企業(yè)的改革將以更大的力度和更積極的態(tài)度推進(jìn)。主管經(jīng)濟(jì)工作的劉鶴副總理親自擔(dān)任國(guó)有企業(yè)改革領(lǐng)導(dǎo)小組組長(zhǎng),就為我們提示了這樣的前景。在國(guó)有企業(yè)改革中,軍工企業(yè)的改革以及軍民融合發(fā)展的推進(jìn),具有很大的示范意義,因?yàn)檐姽て髽I(yè)的體制是最傳統(tǒng)的。長(zhǎng)期以來(lái),因?yàn)樯婕皣?guó)家安全和國(guó)防安全,軍工企業(yè)的傳統(tǒng)體制一直沒(méi)有進(jìn)行深刻的改革。兩大航天集團(tuán)的情況最為典型。按照有關(guān)解讀,國(guó)企將成為新產(chǎn)業(yè)、新領(lǐng)域的開(kāi)拓者,要引領(lǐng)諸多中小企業(yè)和民營(yíng)企業(yè)進(jìn)入藍(lán)海。因此,從商業(yè)航天角度理解的軍民融合絕不是簡(jiǎn)單的軍品、民品并行開(kāi)發(fā),而是如何締造產(chǎn)業(yè),進(jìn)而壯大產(chǎn)業(yè)的問(wèn)題。我們現(xiàn)在所熟悉的一切體制機(jī)制可能都要經(jīng)歷一場(chǎng)革命。而且,在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的背景下,這場(chǎng)革命時(shí)不我待。
因此,可以看出,開(kāi)創(chuàng)商業(yè)航天不但是歷史的必然,今天也具備了歷史的緊迫性。
“菲”說(shuō)不可
· 這些認(rèn)識(shí)是我們這20多年來(lái)深耕行業(yè),聽(tīng)取各方面意見(jiàn)和思想,結(jié)合國(guó)內(nèi)外商業(yè)航天實(shí)踐,逐步分析和總結(jié)出來(lái)的。
· 實(shí)際上是要從頂層開(kāi)創(chuàng)整個(gè)商業(yè)航天,全心全意營(yíng)造產(chǎn)業(yè)生態(tài),宇宙人的生態(tài)基礎(chǔ),不是政府或者龍頭企業(yè),而是廣大的消費(fèi)者。
· 國(guó)內(nèi)外經(jīng)濟(jì)形勢(shì)變化和新政策的出臺(tái),催促著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向高端轉(zhuǎn)型,不進(jìn)則退。那么作為商業(yè)航天來(lái)說(shuō),我們的生意是在宇宙里做的,還有哪個(gè)行業(yè)比我們更“高”的嗎?
Q:今天的商業(yè)航天,是不是具有這樣的物質(zhì)基礎(chǔ)來(lái)開(kāi)創(chuàng)呢?
A:這是完全沒(méi)有問(wèn)題的。首先,經(jīng)過(guò)幾十年的努力和建設(shè),我們國(guó)家已經(jīng)擁有了完整的航天科研、試驗(yàn)、發(fā)射、測(cè)控基礎(chǔ)設(shè)施,這些都是國(guó)有資產(chǎn),通過(guò)立法和政策制定,可以建成一種合理的模式來(lái)向商業(yè)航天企業(yè)開(kāi)放。同樣需要開(kāi)放模式的還包括無(wú)線電頻率資源和空域使用資源。當(dāng)然,模式的建立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本著為行業(yè)發(fā)展的初心來(lái)營(yíng)造健康的政策環(huán)境,而不是為了某一個(gè)、某一類企業(yè)的利益服務(wù)。
同樣,我們也已經(jīng)具備了實(shí)施商業(yè)航天活動(dòng)的充分技術(shù)基礎(chǔ)。我們?cè)谛l(wèi)星、火箭、載人航天方面的科研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具體的應(yīng)用技術(shù)上也超過(guò)了相當(dāng)多的國(guó)家。現(xiàn)在的問(wèn)題是,很多核心技術(shù)屬于資產(chǎn),由國(guó)有企業(yè)掌握和使用。民營(yíng)企業(yè)在這種情況下有幾種選擇,首先是從國(guó)企獵頭,其次是投資自己開(kāi)發(fā),最后是從國(guó)外引進(jìn)。但是付出的時(shí)間代價(jià)都很大。
美國(guó)采用的是另外一種機(jī)制,那些拿不到足夠合同的老牌宇航企業(yè)被收購(gòu)或者破產(chǎn)了,技術(shù)人員重新被新興民營(yíng)航天企業(yè)雇傭,重新創(chuàng)業(yè)。這對(duì)我們來(lái)說(shuō)似乎還有很長(zhǎng)的路要走。反而,如果能夠建立一種國(guó)有企業(yè)和民營(yíng)企業(yè)之間合理的技術(shù)轉(zhuǎn)讓機(jī)制,當(dāng)然一方面要激發(fā)產(chǎn)業(yè)活力,另一方面不能損害國(guó)有資產(chǎn)和國(guó)有企業(yè)利益,也許是更適合的道路。

Q:那么,您具體打算從哪里著手,推動(dòng)商業(yè)航天的開(kāi)創(chuàng)呢?
A:應(yīng)該說(shuō),上面這些認(rèn)識(shí)并不是我一個(gè)人或者某幾個(gè)人的,是我們這20多年來(lái)深耕行業(yè),聽(tīng)取各方面意見(jiàn)和思想,結(jié)合國(guó)內(nèi)外商業(yè)航天實(shí)踐,逐步分析和總結(jié)出來(lái)的。在這個(gè)歷程中,我們不但形成了商業(yè)航天的思想,還認(rèn)識(shí)到,立刻著手打造新的商業(yè)航天模式,已經(jīng)刻不容緩。如果不立刻著手行動(dòng),一方面美國(guó)人會(huì)把我們?cè)铰湓竭h(yuǎn),另一方面,今天這些創(chuàng)業(yè)者的熱血也會(huì)慢慢冷卻下去。
所以,經(jīng)過(guò)三年多的調(diào)研和充分的梳理,包括商業(yè)模式的梳理、優(yōu)質(zhì)資源的梳理等,我們提出了宇宙人航空航天港這個(gè)項(xiàng)目。宇宙人的基本思維是與諸多企業(yè)共同探索和建立適合商業(yè)航天發(fā)展的環(huán)境。取得成功模式之后,再向更多地區(qū)擴(kuò)展。
我們必須要指出,宇宙人不是孵化器的概念,更不是各地產(chǎn)業(yè)園搶奪那些有限的優(yōu)質(zhì)企業(yè)資源的概念。我們就像森林、草原和大海,企業(yè)可以在這里誕生、成長(zhǎng)和壯大,可以在這里長(zhǎng)期生存下去,不但從產(chǎn)業(yè)生態(tài)中汲取養(yǎng)分,自身也成為產(chǎn)業(yè)生態(tài)的貢獻(xiàn)者。
所以說(shuō),我們實(shí)際上是要從頂層開(kāi)創(chuàng)整個(gè)商業(yè)航天,全心全意營(yíng)造產(chǎn)業(yè)生態(tài),而不再糾結(jié)于產(chǎn)業(yè)鏈如何打造。產(chǎn)業(yè)鏈的概念是以供應(yīng)商為核心的,在消費(fèi)拉動(dòng)的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下已經(jīng)不再適用了。至少,對(duì)于嚴(yán)重缺乏消費(fèi)者基礎(chǔ)的商業(yè)航天來(lái)說(shuō),是不適用的。宇宙人的生態(tài)基礎(chǔ),不是政府或者龍頭企業(yè),而是廣大的消費(fèi)者。
為此,我們?cè)O(shè)計(jì)了直接針對(duì)消費(fèi)者的系列服務(wù)。當(dāng)然其中的B2B部分為商務(wù)合作留有足夠的空間,這個(gè)空間會(huì)優(yōu)先為商業(yè)航天企業(yè)及其關(guān)聯(lián)產(chǎn)業(yè)提供如基礎(chǔ)設(shè)施、商業(yè)伙伴、投資、法律和政策咨詢、各方面的優(yōu)質(zhì)資源、專業(yè)營(yíng)銷服務(wù)、上市等多方面的支持,同時(shí),核心的是,我們會(huì)幫助這些企業(yè)完善如何服務(wù)于最終消費(fèi)者的商業(yè)模式,共同在宇宙人的環(huán)境下成長(zhǎng)、壯大。
最近一個(gè)時(shí)期的國(guó)內(nèi)外經(jīng)濟(jì)形勢(shì)變化和新政策的出臺(tái),再一次深刻地催促著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向高端轉(zhuǎn)型,不進(jìn)則退。那么作為商業(yè)航天來(lái)說(shuō),我們的生意是在宇宙里做的,還有哪個(gè)行業(yè)比我們更“高”的嗎?所以,開(kāi)創(chuàng)商業(yè)航天,為國(guó)民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升級(jí)起到帶動(dòng)作用,是行業(yè)的責(zé)任,也是宇宙人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