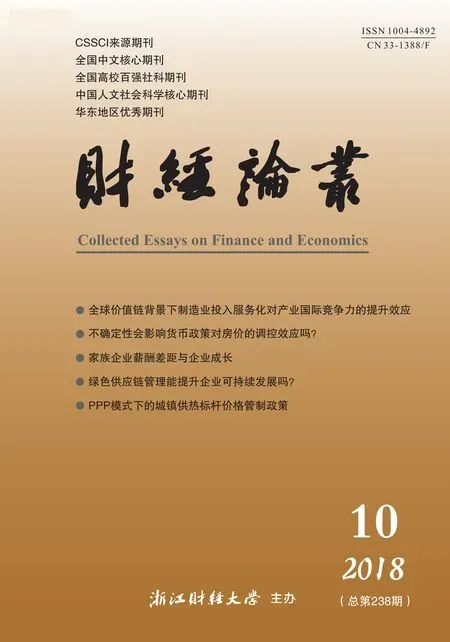貨幣政策透明度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DAG-SVAR模型
卜振興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總行資產管理部,北京 100033)
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定義,貨幣政策透明度指的是公眾能夠簡單、方便、及時、準確獲取貨幣當局關于政策目標、政策框架、政策決策等方面的信息。這個定義既包含了央行向公眾的信息披露,也包含了公眾對已披露信息的理解。隨著貨幣政策透明度逐漸成為各國貨幣當局政策操作的趨勢,貨幣政策透明度問題受到了政府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通過對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測度可以發現,不同國家和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政策透明度水平都是有明顯差異的。那么為什么各國貨幣政策透明度會存在差異?貨幣政策透明度又受哪些因素影響?回答上述問題,一方面有助于理解各國貨幣政策透明度差異的原因,另一方面也為貨幣政策透明度的調整提供了理論基礎。鑒于影響因素分析是貨幣政策透明度問題的核心之一,但目前國內這方面的研究還非常缺乏,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文獻回顧
Barro-Gordon (1983)[1]最早開始貨幣政策透明度的研究,隨著提升貨幣政策透明度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學術界的研究也不斷深入,研究內容不斷擴展。這些研究既包括對貨幣政策透明度概念的研究(IMF,1999[注]IMF Code of Good Practices on Transparency in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olicies。),也包括對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度量[2][3],既有對貨幣政策透明度理論和實踐基礎的分析[4][5],也有對貨幣政策透明度實踐操作的探討[6]。此外,還有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政策效果[7][8],并認為貨幣政策透明度在引導公眾預期,穩定市場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雖然關于貨幣政策透明度研究的領域非常廣泛,但是目前關于貨幣政策透明度影響因素的分析相對缺乏。從國外的研究來看,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Dincer和Eichengreen(2007)[9]對1998年~2005年全球100個國家和地區央行的透明度因素研究,他們把影響透明度的因素分為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其中經濟因素包括人均收入、歷史通脹水平、匯率制度、金融深化;政治因素包括法律法規、政治穩定、話語權和問責制、政府效率等,研究結果表明,人均收入是影響透明度水平最重要的因素,匯率制度彈性與透明度正相關,政治性變量中很多也與透明度相關,但是顯著性不高,而且政策獨立性與透明度的關系并不顯著。Crowe和Meade(2008)[10]基于40個國家(包括12個歐元區國家)2003年的數據,運用截面回歸模型分析了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影響因素后發現,匯率制度彈性、監管質量、話語權和問責制與貨幣政策透明度正相關,貨幣政策獨立性僅與貨幣政策透明度有微弱的相關關系,人均收入、開放度與透明度沒有顯著相關關系。Geraats(2009)[11]基于Dincer和Eichengreen (2007)的測算數據研究了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影響因素,發現通脹水平、人均GDP與貨幣政策透明度正相關。Dincer和Eichengreen(2010)[12]評價了100個國家和地區央行1998年~2006年貨幣政策透明度狀況后提出,經濟因素方面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匯率制度的彈性,政治方面法律法規、政治穩定話語權和問責、政府效率、政治民主化與政策透明度成正比。在彈性匯率制度下,開放度與透明度成正比,在固定匯率制度下,開放度與透明度正反比。Dincer和Eichengreen(2014)[13]評價了全球120個國家1998年~2010年的貨幣政策透明度狀況后發現,發達國家透明度水平高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遠離金融中心和實行專制政治體制的北非和中東地區透明度水平普遍較低。總結國外的研究可以看出,國外學者將影響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因素分為經濟性和政治性兩大類。經濟性因素中,經濟增長、通脹水平、金融深化和開放度等是影響透明度的重要因素。政治性因素中,法律法規、政治穩定、話語權和問責制、政府效率等是影響透明度的因素,但是政治性因素呈現出較高的相關性,并且很多變量對透明度的影響并不顯著。另外央行獨立性對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影響也不顯著。
從國內的研究來看,楊麗華(2008)[14]在分析了影響發達國家透明度的因素后認為,央行的獨立性和宏觀經濟的穩定性是影響貨幣政策透明度的主要因素。沈煊和張偉(2010)[15]以E-G指數為基礎分析了貨幣政策透明度的現狀和演變趨勢,認為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和宏觀經濟環境(開放度、匯率制度、央行聲譽)是影響透明度的主要因素。趙靜(2010)[16]運用面板數據分析方法,以加拿大、中國、日本、美國等18個國家的樣本為例,分析了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經濟增長、歷史通脹、政治穩定性、政府效率與貨幣政策透明度正相關,而金融深化、公眾話語權與透明度負相關。肖曼君和李穎(2013)[17]運用PVAR模型研究了貨幣政策透明度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通貨膨脹對透明度的影響并不顯著。王少林等(2014)[18]認為宏觀經濟表現會促使貨幣當局調整貨幣政策透明度,最終影響透明度水平。總結國內的研究可以發現,目前國內的因素分析主要停留在定性說明方面,宏觀經濟表現、開放度、通貨膨脹、政策獨立性等都是影響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因素。
綜上所述,目前國內外關于貨幣政策透明度影響因素的研究還較為缺乏,尤其是定量的研究。但是,影響因素的定量研究恰恰是貨幣政策透明度理論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有必要去分析和探討。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一是從一個嶄新的視角研究了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問題;二是運用有向無環圖方法研究變量之間的當期因果關系;三是在DAG模型基礎上構建結構向量,并運用SVAR模型分析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影響因素,結構模型的建立更加科學。本文是目前國內首次對貨幣政策透明度影響因素進行的專門定量研究,也是國內外第一次運用DAG和SVAR模型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的貨幣政策影響因素定量研究,豐富了貨幣政策透明度問題相關領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二、理論模型和數據說明
(一)理論模型
1.結構化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傳統的經濟計量方法是以簡單的經濟理論為基礎來描述變量之間的關系,實質是人為決定變量是內生還是外生,建立在這種主觀判斷基礎上的估計不夠準確。為了克服不足,Sims(1980)[19]提出了向量自回歸模型(簡稱VAR模型),并開創性地利用VAR模型對經濟變量的因果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Granger因果檢驗正是基于VAR模型來定義的。
VAR模型因其在參數回歸方面具有的優勢,目前被廣泛運用于計量分析中。但是該模型也存在缺陷,如模型的建立不以經濟理論為基礎,不分析回歸參數的經濟意義;對參數不施加零約束,模型待估參數過多;模型不包含任何當期變量,不能考察變量當期之間的關系等。基于此,Blanchard和Perotti (1999)[20]提出了一種結構化的向量自回歸模型(structural vector auto regression model,簡稱SVAR模型)。該模型基于一定的經濟理論,在VAR模型中加入具有單向因果關系的內生變量當期值,可以體現出變量之間當期的結構性關系,并且對待估參數進行了結構化約束,很好地解決了標準VAR模型存在的一些問題。
估計SVAR模型需要對模型的結構式施加約束,對擾動項的結構式進行正確的設定。目前研究中對結構化模型進行約束,一般是根據經濟理論進行直觀的判斷,但是這種方法帶有很強的主觀色彩,缺乏科學依據[21],因此研究方法亟待改進。有向無環圖(DAG)方法的出現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
2.有向無環圖(DAG)。DAG方法出現以前,研究變量之間因果關系比較常用的方法是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但是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存在以下問題:一是格蘭杰因果檢驗是檢驗統計上的時間先后順序,并不表示真正存在因果關系,具體還要依據模型和經濟理論進行解釋[22];二是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無法檢驗當期因果關系,只是檢驗滯后期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基于此, Pearl(1995)[23]和Hoover(2003)[24]等人提出了有向無環圖(directed acycline graph)方法,用于分析變量間的當期因果關系。楊子暉(2008)[25]認為DAG方法可以考察變量之間的當期因果關系,同時能夠避免VAR模型結構設定中的主觀因素,因此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趙勝民等(2011)[26]、范小云等(2013)[27]認為基于DAG的方差分解更能體現出經濟意義顯著性。DAG方法是通過分析擾動項無條件相關系數和偏相關系數(條件相關系數)之間的關系來確定變量之間的當期因果關系,檢驗過程如下:
步驟1:建立相關性關系的原假設,即假設變量之間存在著同期的因果關系。通過無方向的線將變量連接在一起,建立無向完全圖。
步驟2:運用PC算法對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篩選。首先通過回歸殘差的相關系數矩陣進行第一次篩選,如果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則刪掉變量之間的連線,說明變量之間不存在同期因果關系。其次運用回歸殘差的偏相關系數進行第二次篩選,如果相關關系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則刪掉。以此類推,直至進行第N-2階偏相關系數顯著性檢驗。在整體相關性檢驗中,經常使用的是Fisher提出的Z統計檢驗量[28],該檢驗表達式如下所示:
(1)
其中,ρ(i,j|k)表示以k個變量為條件的變量i和變量j之間的總體相關系數,n表示樣本量。
步驟3:識別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方向。在無向完全圖中,如果經過刪邊后變量之間仍然保留連接線,則表明它們之間存在相關關系,并且變量之間是相鄰的,如X-Y。如果三個變量之間存在如下關系X-Y-Z,且以Y為條件的X與Z偏相關系數為0,則說明變量Y是變量X與變量Z的隔離集。即ρ(X,Z|Y)=0。給出以上定義以后,我們有如下推論:當無向完全圖為X-Y-Z,X與Y相鄰,Y與Z相鄰,但是X與Z不相鄰,如果Y不是X與Z隔離集,那么三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方向為X→Y←Z;當無向完全圖為X-Y-Z,X與Y相鄰,Y與Z相鄰,但是X與Z不相鄰,如果已知X→Y,那么Y與Z的同期因果關系為Y→Z[29][30]。
步驟4:結果解釋。通過建立原假設,并運用PC算法刪邊和定向,最終我們可以得到變量間因果關系的有向無環圖。總結起來,變量之間一共存在以下幾種情況:

(2)
步驟5:過度識別檢驗。在進行有向無環圖DAG的分析后,我們需要運用Sims(1986)[31]提出的似然比檢驗方法,對DAG的分析結果進行檢驗。檢驗方法如下:
(3)

與以往通過經驗判斷決定SVAR模型結構式的約束不同,有向無環圖基于擾動項的相關系數和偏相關系數的檢驗,避免了經驗分析的主觀性,確保了SVAR模型后續研究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二)指標選取
根據已有研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和數據可得性,本文建立如下的理論假設,并通過后文的實證分析予以驗證。
H1: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貨幣政策透明度水平越高。
經濟增長通過兩個渠道對貨幣政策透明度產生影響。一方面,對央行而言,經濟水平越高,央行對通脹目標賦予的權重會越大,央行會更加主動的與公眾交流溝通,引導公眾預期,提升政策透明度;另一方面,對公眾而言,經濟水平越高,公眾對政策信息的需求也越高,這將進一步提升透明度水平。
H2:歷史通脹水平越高,貨幣政策透明度水平越高。
提升貨幣政策透明度有助于錨定公眾預期,對降低通脹水平和通脹波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歷史通脹水平越高,央行越有激勵去提升貨幣政策透明度水平。
H3:金融深化水平與貨幣政策透明度密切相關。
金融深化對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影響是正反兩方面的。金融深化水平的提升會引發央行對金融市場的關注,促使央行主動采取措施發布指引,引導金融市場預期。同時,金融深化也會加重央行金融監管的困難,金融市場對政策會產生過激反應,促使央行在信息披露時會采取較為謹慎的態度。
H4:開放度越高,貨幣政策透明度水平越高。
開放度水平越高,對外交流的程度和水平也越高。這種對外交流會促進我國的貨幣政策與世界各國貨幣政策的相互交流,并推動我國央行的貨幣政策融入世界貨幣政策發展的趨勢中。目前世界各國都在采取措施提升政策透明度,開放度的提升將有利于我國透明度水平的上升。
綜上,我們最終選擇經濟增長、通脹水平、金融深化和開放度作為影響貨幣政策透明度的主要參考變量[注]本文之所以沒有選擇政治性因素,一方面在于政治性因素的影響并不顯著,另一方面在于政治數據的公布主要是來源于美國、英國等統計機構,數據統計存在問題。如民主化指數來自于美國中央情報局政治不穩定工作小組的調查數據,數據顯示我國民主化指數從1977~2014年一直為-7,沒有任何變化,這顯然是嚴重不符合我國民主化進程實際的。經濟學人智庫也曾經給出了民主化的數據,但只公布了2006~2012年的數據,并且是以2年為一個周期。法律法規、政治穩定、話語權和問責制、政府效率等指標均來源于全球治理數據庫,目前公布數據跨度為1996~2014年,是以2年為一個周期。。其中,經濟增長變量選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變量(PCG),即GDP/總人口,并取對數;歷史通脹水平(PIL)變量選用滯后一期消費者價格指數,即CPI(-1);金融深化(TFD)選用貨幣供應占GDP的比重,即M2/GDP;開放度又稱對外貿易指數(ETI)選用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即進出口總額/GDP。
根據以上的理論分析與假設,本文構建如下模型,以檢驗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影響因素:
MPT=β0+β1PCG+β2PIL+β3TFD+β4ETI+μ
(4)
關于貨幣政策透明度測算,本文采取了與以往研究完全不同的方法。首先運用指標體系方法評價我國貨幣政策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其次運用市場反應方法測度市場反應的透明度,最后將兩種方法下測度的透明度狀況進行歸一化和標準化處理并加權求和,得到總的透明度指數。該方法一方面借鑒了已有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更符合IMF等關于貨幣政策透明度定義的兩層含義,計算結果更為合理。圖1給出了我國2000年第1季度至2016年第4季度的貨幣政策透明度狀況。
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的信息披露透明度水平在2001年~2002年之間出現較為明顯的上升,2002年~2005年緩慢上升,而2006年~2013年我國信息披露的貨幣政策透明度均沒有出現明顯變化,2016年后開始出現明顯上升。其中2001年~2002年、2014年左右的快速上升與我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信息公布通用系統和數據披露特殊標準密切相關。市場反應的透明度水平一直保持較高水平,并在2007年~2008年出現劇烈下滑,這與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密切相關。綜合指數充分反映了兩種透明度變化的信息。

圖1 貨幣政策透明度指數
(三)數據說明
本文采用2000年第1季度至2016年第4季度的季度數據,其中貨幣政策透明度指標數據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網站、CCER經濟金融數據庫并經作者計算整理而得。經濟增長、總人口、物價指數、貨幣供應(M2)數據來自Wind數據庫。另外,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民幣計價的月度進出口貿易總額數據是從2012年開始的,國家外匯管理局人民幣對美元的月度匯率數據是從2002年1月開始,因此,本文的進出口總額數據選取了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以美元計價的進出口總額數據,并通過匯率折算得出了我國2000年~2016年以人民幣計價的進出口總額數據,其中美元計價的進出口總額數據來自Wind數據庫,人民幣對美元數據來自美聯儲經濟研究局網站。

表1 指標變量一覽表

表2 變量統計描述
注:括號內為p值;變異系數=標準差/均值;J-B 統計量在 5%和 1%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分別為 5.99 和9.21。
三、實證檢驗和結果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在進行分析之前,首先必須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以確定數據的平穩性。本文采用常用的ADF單位根檢驗方法,同時考慮截距項、截距項和趨勢項、無截距項和趨勢項三種情況。通過對ADF檢驗結果的分析發現,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三個變量均為非平穩變量,對變量進行一階差分后,數據變為平穩變量。據此可知各變量均為一階單整I(1)過程。
(二)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
1.模型穩定性檢驗和最優滯后期。建立VAR模型首先要滿足平穩性的假定,平穩性要求特征方程的特征根均要位于單位圓以內。由穩定性檢驗可知原變量的單位根有一個位于單位圓之外,VAR模型不滿足穩定性的要求。差分后的特征根均位于單位圓內,表明差分后的模型滿足穩定性要求,可以進行脈沖響應、方差分解等后續的計算和分析。其次應確定滯后期k值。如果滯后期太少,誤差項的自相關會很嚴重,會導致參數的非一致性估計。但k值又不宜過大,k值過大會導致自由度減小,直接影響模型參數估計結果的有效性。本文采用了LR、FPE、AIC、SC、HQ等多種方法對最優滯后期進行了檢驗。綜合不同的信息準則檢驗結論,最終確定模型的最優滯后期為2期。
2.協整檢驗。在進行時間系列分析時,傳統上要求所用的時間序列必須是平穩的,即沒有隨機趨勢或確定趨勢,否則會產生“偽回歸”問題。但是現實中,宏觀經濟數據一般是不平穩的。面對這個問題,有兩種解決方法:一種是對非平穩變量進行差分,使差分后的數據滿足平穩性的要求,但是差分會讓我們失去總量的長期信息,而這些長期信息對分析問題來說又是必要的。另外一種方法就是運用協整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不在損失數據信息的情況下,考察非平穩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因此更有優勢。在協整分析之前首先要確定兩組非平穩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也即是否存在非平穩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協整檢驗的方法有很多,最典型的就是Engle-Granger檢驗和Johansen檢驗,其中Engle-Granger檢驗只能用于檢驗兩個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Johansen檢驗不僅在檢驗變量上沒有這種限制,而且可以同時求出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因此,本文在進行協整檢驗時采用Johansen檢驗方法,檢驗公式如下:
ΔYt=ΠYt-1+Γ1ΔYt-1+Γ2ΔYt2+…+Γk-1ΔYt-(k-1)+ΦDt+μt
(5)
其中,Y表示非平穩變量,Π、Γ、Φ表示系數,D表示截距項,u表示隨機擾動項。如果檢驗存在r個協整向量,即(N-r)個非協整向量或者(N-r)個單位根,可以表達為相應的(N-r)個特征值。協整個數的檢驗主要有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兩種方法,為了保證檢驗結果的穩健性和一致性,本文采取了這兩種檢驗方法。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檢驗均表明,政策透明度、經濟增長、歷史通脹水平、金融深化和經濟開放度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
3.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根據格蘭杰定理,如果若干個非平穩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則必然存在誤差修正模型。誤差修正模型可以在不損失變量信息的情況下對變量長期均衡關系進行量化分析。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是在解釋變量中含有協整約束的VAR模型,它適用于分析已知有協整關系的非平穩序列之間的關系。當有一個大范圍的短期動態波動時,VECM表達式會限制內生變量的長期行為收斂于它們的協整關系。因為一系列的部分短期調整可以修正長期均衡的偏離,所以協整項被稱為是誤差修正項。根據協整向量個數檢驗結果表明MPT、PCG、PIL、TFD和ETI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因此進入VECM模型的誤差修正項分別是:
ΠYt-1+αμ=αβTYt-1+αμ=

(6)
4.求擾動相關系數矩陣。通過對一階差分變量的誤差修正模型(VECM)估計,可以得到擾動項的無條件相關系數矩陣[注]限于篇幅,擾動項的偏相關系數這里不再報告。。

(7)
(三)有向無環圖
下面將以擾動項相關系數矩陣為基礎,運用有向無環圖(DAG)進行變量當期因果關系的分析。首先,我們建立無向完全圖(圖2),作為當期因果關系檢驗的原假設。然后運用TETRAD軟件進行當期因果關系的檢驗。由于本文使用的樣本數據是2000年第1季度至2016年第4季度的數據,數據跨度為68個周期,屬于小樣本估計(樣本觀察值小于200),小樣本估計結果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為了避免這一情況,通常的做法是提高小樣本估計下的顯著性水平,來改善DAG估計結果的有效性和合理性[32]。本文參考郭娜和李政(2013)[33]的研究,將顯著性水平設為0.2。同時,為了使估計結果更具有合理性,本文運用了Sims提出的似然比統計量檢驗方法,檢查結果顯示,在20%(甚至是5%)的顯著性水平下無法拒絕“過度約束為真”的原假設,DAG模型的估計結果是合理的。最終檢驗結果見圖3。
圖3表明:在20%的顯著性水平下存在著開放度(ETI)對歷史通脹水平(PIL)的當期單項因果關系,金融深化(TFD)存在著對經濟增長(PCG)的當期單項因果關系,金融深化(TFD)和經濟增長(PCG)存在著對政策透明度(MPT)的當期因果關系,而歷史通脹水平(PIL)和開放度(ETI)與政策透明度(MPT)之間的當期因果關系并不顯著。

圖2 無向完全圖

圖3 有向無環圖
(四)脈沖響應分析和預測方差分解
基于DAG分析,我們得出了各變量之間的當期因果關系,以此構建結構化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的約束矩陣,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進行分析。
1.脈沖響應。由于VAR模型的估計結果只具有一致性,但是對單個參數估計值的經濟解釋比較困難。要想對一個VAR模型做出分析,通常是觀察系統的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脈沖響應函數解釋了變量是如何對各種沖擊做出反應以及反應的程度。
如圖4所示,在一個單位的沖擊下,透明度對自身沖擊響應的初始值較高,從第1期上升到較高水平后快速衰減,到第8期沖擊響應基本消失;透明度對經濟增長的脈沖響應在第2期開始,之后緩慢衰減,至14期后基本維持在0.001的較低水平。而透明度對通脹水平在第三期才開始出現并在第7期后衰減,10期后的脈沖響應基本消失。透明度對金融深化的脈沖響應一直不顯著,并在14期后衰減至0.001的水平。透明度對開放度一個單位脈沖的響應第2期才會出現,之后緩慢衰減,并最終維持在0.001的水平上。

圖4 對各變量一個單位標準差的脈沖響應(基于DAG)
2.方差分解。方差分解反映未來預測誤差由不同信息沖擊影響的比例或百分比。為了更直觀地觀察預測方差分解情況,我們給出了基于有向無環圖的貨幣政策透明度預測方法分解圖。

圖5 基于有向無環圖的MPT預測方差分解圖
觀察圖5可以發現,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波動絕大部分可以由自身因素來解釋,1~4期快速下降后,基本穩定在60%~70%左右的水平,這說明貨幣政策透明度存在很大慣性。貨幣政策透明度作為一種制度性安排,其變動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除自身因素外,其他變量對政策透明度的影響都從第一期后出現不同程度的上升,但是上升幅度有所差別。以第10期為例,經濟增長可以解釋預測方差變動的12.05%,歷史通脹可以解釋7.22%,金融深化可以解釋0.59%,而開放度可以解釋16.98%。因此,除去自身慣性因素外,各變量對貨幣政策波動影響程度為:開放度>經濟增長>歷史通脹>金融深化。這說明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受外部影響較大,受內部影響較小;受實體經濟影響較大,受物價、金融等虛擬經濟影響因素較小。
除了對外開放因素,經濟增長在政策透明度風格轉換中也發揮了巨大作用。經濟增長和發展一方面激發了人們對政策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促進了信息溝通和交流。回顧和分析各國透明度建設的歷程,很多國家提升政策透明度的初衷就是為了穩定公眾預期,降低通貨膨脹。貨幣政策重要目標是維持物價穩定,因此,維持通脹水平保持在合理的區間,也就成為了政策透明度提升的內在動力。最后,金融深化同樣在透明度提升中扮演者著重要角色,正如已有研究所證實的那樣,透明度水平較低的國家主要集中于遠離金融中心的北非和阿拉伯國家。只有金融不斷的深化和發展,才能對宏觀監管和微觀監管提出更多要求,才能促進政策體制和政策風格的不斷變革和轉換。
(五)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基于有向無環圖(DAG)方法的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我們采用遞歸預測方差分解方法進行檢驗。具體做法是,以2000年第1季度至2009年第1季度為基期進行第一次方差分解,然后將研究樣本擴展至2000年第1季度至2009年第2季度,并做該樣本期內基于DAG模型的方差分解。以此類推,一直持續至2016年第4季度。共進行32次遞歸分析,并將不同樣本期方差分解第20期的分解結果進行綜合,得到遞歸方差分解圖(圖6)。

圖6 政策透明度MPT的遞歸預測方差分解
從圖6可以發現,在不同的樣本期內,政策透明度波動的60%左右可以由自身慣性解釋,說明自身慣性因素是導致政策透明度波動的主要因素。金融深化的影響因素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大約1%左右,說明金融深化對透明度波動的影響一直不明顯。除此之外,開放度、經濟增長和歷史通脹因素對透明度波動的影響基本維持在18%、15%和10%左右的水平。
穩健性檢驗結果表明,各變量波動影響因素的占比基本保持穩定,沒有出現明顯的波動,說明在不同樣本期下,估計具有較好的一致性,估計結果穩健。
四、結 語
本文運用有向無環圖(DAG)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研究了影響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因素,得出以下結論:第一,金融深化和經濟增長存在著對政策透明度的當期單項因果關系,也即金融深化和經濟增長導致了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提升,而歷史通脹水平和開放度與政策透明度間的當期因果關系并不顯著。第二,貨幣政策透明度對各變量沖擊的響應程度有所不同,其中受自身沖擊產生的反映程度最大,其次為經濟增長和開放度,歷史通脹水平的沖擊影響也較為顯著但是時滯相對較長,并且持續時間有限,透明度對金融深化沖擊的響應并不顯著,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表明透明度對金融深化的擾動并不敏感。第三,通過基于DAG模型的預測方差分解,我們發現貨幣政策透明度波動的絕大部分可以由自身因素來解釋,存在很大的慣性。除去自身慣性因素外,各變量對貨幣政策波動的影響程度從高至低依次為開放度、經濟增長、歷史通脹、金融深化,并且金融深化的影響一直非常小。這說明,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受外部影響較大,受內部影響較小;受實體經濟影響較大,受物價、金融等虛擬經濟因素影響較小。最后,遞歸預測方差分解也表明估計結果非常穩健,結論是非常可信的。
根據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一是繼續堅持對外開放的策略。在對外開放中不斷學習和借鑒,同時結合中國的實際,創新政策監管方式、增強政策監管能力,提升政策引導能力,進一步提高政策操作水平。二是繼續堅持發展經濟。經濟增長在透明度中的積極作用,一方面讓我們認識到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提升是有其客觀經濟基礎的,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所處的階段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中國在經濟發展中遭遇的問題和困難,最終靠發展來解決,只有經濟增長才能帶來透明度水平的持續提升和優化。三是關注貨幣政策核心目標。維持物價穩定是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這也是歷來主要國家央行的共識,即使近年來經濟危機的爆發引發了各國央行對經濟增長、金融穩定等目標的關注,但是物價穩定作為貨幣政策核心目標的地位并未受到削弱,貨幣當局應堅守穩定物價的核心目標不動搖。四是有計劃推進金融深化,使其保持在合理水平。金融深化對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影響作用相比其他變量小,因此通過金融深化影響透明度的效果不明顯。政府應逐步放松對金融的干預,引導資金更多地投入到實體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