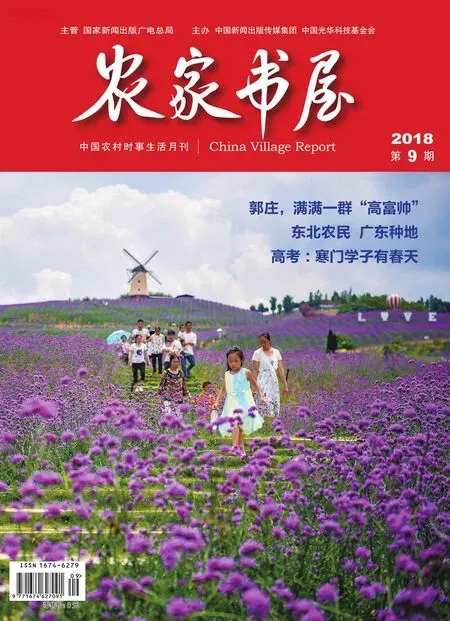久遠(yuǎn)的飯市
□
冀南漳河北岸,有一個(gè)叫水魚崗的小村莊。說它小,全村只有百十戶人家,人口不到六百,在當(dāng)時(shí)全公社21個(gè)村莊中,它的人口最少,這就是我的家鄉(xiāng)。
我們的村莊雖面臨漳河,但是由于地勢高,河里的水引不上來。水魚崗既沒有水,更沒有魚,名不副實(shí)。崗,倒是實(shí)實(shí)在在有。土地處于崗坡上,人們靠天吃飯,十年九旱。在全公社中,數(shù)它最窮。
上個(gè)世紀(jì)60年代,在這樣自然條件惡劣的農(nóng)村,填飽肚子是人們的首要事情。在我的記憶中,村里小麥年年種,但很少有豐收的年景。經(jīng)常有外村人笑話我們:“水魚崗的麥子長到脖子高。”然后再來一句“腳脖子”。麥子矮得不能用鐮刀割,只能蹲在地上用手薅,連麥種都打不回來。
一年就指望秋天這一季。田地里種的大都是耐旱作物。玉米是極少種植的。紅薯成了最大眾的作物。它不僅耐旱,而且高產(chǎn)。五斤紅薯算一斤糧,對農(nóng)民也最劃算。即便如此,人們也難填飽肚子。于是,出現(xiàn)了這么一種現(xiàn)象,別的村,年年給國家交公糧,我們村三年兩頭吃國家的返銷糧。老人們常說:“還是共產(chǎn)黨好,社會(huì)主義好。要擱過去,遇到災(zāi)荒年,餓不死也得逃荒要飯去。”
那個(gè)年代,吃的不好,也常常吃不飽。紅薯,成了水魚崗人的主要食物。不僅煮紅薯、蒸紅薯、烤紅薯,還把紅薯擦成片、曬成干兒、碾成面。嬸子、大娘、奶奶們充分發(fā)揮女人的想象力,變著法地做出許多花樣來:紅薯面窩頭、紅薯面餅子,紅薯面饸絡(luò),等等。現(xiàn)在當(dāng)作佳肴極少能吃到的東西,當(dāng)時(shí)是我們的家常便飯。
村小人少,一條胡同也就幾戶人家。和我家做鄰居的就三四戶人家。戶少人不少,那時(shí)還不興計(jì)劃生育,每家多的六七個(gè)孩子,少的三四個(gè)。一到飯點(diǎn),大人、小孩都端著飯碗走出大門,或蹲或坐,擠滿大半條胡同,大家邊吃邊聊,熱鬧親切,如同一家人,村里人稱它為“飯市”。

那時(shí)候人們都很窮,早晚飯基本是沒有炒菜的。簡單點(diǎn)的,在稀飯里撒些鹽,放把青菜葉。條件好些的,腌點(diǎn)蘿卜咸菜,吃飯時(shí)切上一小塊,左手拇指、食指和中指端著碗,無名指和小指夾著咸菜,右手拿著筷子和窩頭。十個(gè)手指動(dòng)作協(xié)調(diào),從沒見過有誰將窩頭或咸菜掉下來的。
飯市最熱鬧的時(shí)候,是鄰村一位五十多歲盲人的到來。他靠一根盲杖走五六里崎嶇不平的崗坡路,并且能一步不差地走到我家門口,坐到門口南邊一塊很大很平滑的河卵石上。憑聲音他能準(zhǔn)確地喊出我們每個(gè)人的名字。來時(shí),他肩膀上總是背著一個(gè)長長的布袋子,中間開口部分搭在肩上,兩頭可以裝東西,我們稱之為褡褳子。他坐在石頭上,把木魚安放好,將敲木魚的繩子套在腳上,拿出一把老舊弦子,只見他調(diào)調(diào)弦,嗽一下嗓子,就邊拉邊敲邊唱起來,他的個(gè)人“演唱會(huì)”就算開始了。
說實(shí)話,除了木魚聲清脆之外,他拉的弦子比拉鋸好聽不到哪里,他唱的不算難聽也說不上好聽。盡管如此,聽到他的演唱,村里的大人小孩還是紛紛端著飯碗圍攏過來,吃飯、聊天、聽唱都不耽誤。他唱完一段,會(huì)有人主動(dòng)給他端來稀飯、咸菜和窩頭。他走的時(shí)候,每家都會(huì)送給他一兩個(gè)窩頭。他將這些窩頭裝進(jìn)褡褳子里,作為下頓飯的吃食。
“飯市”已是久遠(yuǎn)的過去了。如今,水魚崗人不再為吃飽飯發(fā)愁,村里人的生活也逐漸富裕起來。然而,現(xiàn)代化的快節(jié)奏也給人們帶來了很多壓力,大家忙碌著,過去村里飯市的那種場景再也不見了,同時(shí)有些不該丟掉的東西,似乎也漸漸地遠(yuǎn)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