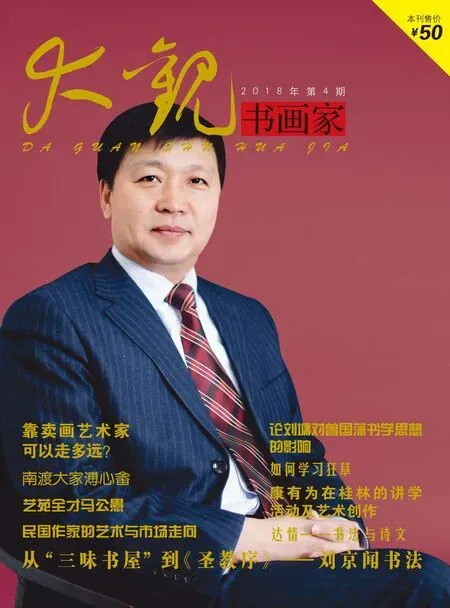自書自畫自題詩
——略論金農與文人畫的定型
張眠溪
因文為用,相須而成。
中國美術史上的文人畫主要指宋、元、明、清時代以文人士大夫為主體的業余或半業余繪畫,詩、書、畫的合一是其關鍵。在文人畫史上,金農是一個重要人物。關于這一點,已有不少的研究者注意到了,本文略微調整一下研究角度,直接圍繞“詩、書、畫”關系的變動來討論金農與文人畫定型的關系。上海博物館藏金農《山水人物冊》,其六題跋云:“回汀曲渚暖生煙,風柳風蒲綠漲天,我是釣師人識否,白鷗前導在春船。此予在二十年前泛蕭家湖之作,今追想昔游風景漫畫小幅并錄前詩,曲江外史記。”這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金農七十三歲時追記二十年前所游蕭家湖風景。“漫畫小幅并錄前詩”“曲江外史記”是比較典型的題跋格式和語言。同一年金農還創作了另外兩件風格相似的作品,故宮博物院藏金農《人物山水冊》,其九題跋云:“回汀曲渚暖生煙,風柳風蒲綠漲天,我是釣師人識否,白鷗前導在春船。曲江外史畫詩書。”沈陽故宮博物院藏金農《雜畫冊》中有題跋云:“回汀曲渚暖生煙,風柳風蒲綠漲天,我是釣師人識否,白鷗前導在春船。曲江外史畫詩書。”我們知道,出于市場的需求,一題多作在金農及“揚州八怪”中是常見的現象,這三件作品就屬于這種情況。值得注意的是,金農在后兩件作品的題跋中使用了“畫詩書”聯署的作法。
“畫詩書”聯署也出現在金農的其他作品中,略舉數例。上海博物館藏《梅花冊》,其五題跋云:“驛路梅花影倒垂,離情別緒寄相思。故人近日全疏我,折一枝兒寄與誰?稽留山民畫詩書。”其十五題跋云:“一枝兩枝橫復斜,林下水邊香正奢。我亦騎驢孟夫子,滿頭風雪為梅花。稽留山民畫詩書。”《梅花冊》作于乾隆丁丑年(1757),金農七十一歲。廣西博物館藏《雜畫冊》,其四題跋云:“松比人長覆石闌,人如松立影生寒。一只我有弄泉手,濺沫飛流獨飽看。稽留山民畫詩書。”《雜畫冊》作于乾隆二十四年,金農七十三歲。南京博物院藏《牽馬圖》,題跋云:“龍池三浴歲骎骎,空抱馳驅報主心。牽向朱門問高價,何人一顧值千金。七十五叟杭郡金農畫詩書。”這是已知最晚題跋中有“畫詩書”聯署的作品。此外,在金農的詩文集以及著錄作品中也可見到“畫詩書”的聯署,《冬心先生雜畫題記》云:“白板小橋通碧塘,無闌無檻鏡中央。野香留客晚還立,三十六鷗世界涼。曲江外史畫詩書。”《雜畫題記》是后人根據金農題跋所編文集,所收主要是金農在自己作品上的題跋。與其他詩文集不同的是,《雜畫題記》所錄為題跋原文,因此較多的保存了“畫詩書”聯署的資料。
概括而言,在金農的繪畫作品中,“畫詩書”聯署已經成為一種慣例。從題跋的格式來說,“畫詩書”聯署與“畫并題詩”“畫并記”等并無含義的上不同,但是從詩、書、畫的關系來說,它卻最直接地反映了文人畫關鍵因素的演變。“畫詩書”聯署在古代繪畫作品的題跋中不算常見,但是在金農的題跋中卻并不少見,這就引起了筆者的注意。

金農作品
“畫詩書”聯署可以追溯到元代,上海博物館藏柯九思《墨竹圖》,題跋云:“熙寧己酉湖州筆,清事遺蹤二百年。人說丹丘柯道者,獨能揮翰繼其傳。非幻道者丹丘柯九思敬仲畫詩書。”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畫詩書”在繪畫題跋當中的第一次聯署。除了柯九思以外,其他元代畫家很少采用這種聯署方式。再向上可以追溯到宋代,故宮博物院藏宋徽宗《祥龍石圖》,題跋云:“祥龍石者,立于環碧池之南,芳洲橋之西,相對則勝瀛也。其勢騰涌,若虬龍出,為瑞應之狀。奇容巧態,莫能具絕妙而言之也。乃親繪縑素,聊以四韻紀之。彼美蜿蜒勢若龍。挺然為瑞獨稱雄。云凝好色來相借。水潤清輝更不同。常帶瞑煙疑振鬣。每乘宵雨恐凌空。故憑彩筆親模寫。融結功深未易窮。御制御畫并書。”這里的“御制”指皇帝所作之詩,“御制御畫并書”顯然就是“詩、畫并書”的意思。雖然從文字上看還不完善,但是將它看作“詩書畫”聯署的源頭是沒有問題的。
由此可見,在美術史上存在一條從宋徽宗到金農的“詩書畫”聯署的線索。“詩書畫”聯署線索所牽涉的畫家人數雖然不多,但是它直接反映了詩、書、畫關系的變動。作為文人畫的關鍵,任何有關詩、書、畫融合的材料都應該得到重視。遺憾的是,這一線索往往為研究者所忽略,這固然有文獻整理的問題,但更重要的還是對作品的重視不足,畢竟它們之中的相當一部分仍流傳于世。所謂“詩書畫”合一,從形式上看是詩歌、書法、繪畫三種藝術形式并列于同一載體,就內容而言則需要三者的充分融合。唐代有鄭虔詩、書、畫三絕的故事,也有盧鴻繪《草堂十志圖》并題詩的記載。事實上,在鄭虔、盧鴻之前的時代,傳世作品和文獻中就已經出現了詩、書、畫并列的形式。應該看到,唐以前這種詩、書、畫的并列已經具有審美的價值,但它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人畫。詩、書、畫融合包括詩書、詩畫和書畫關系三個方面,以下略為說明。首先來看詩書關系。一方面,文字需要書寫才能實現其價值,漢代許慎所說“著于竹帛謂之書”即是此意。另一方面,書法的成立也需要內容的支撐,正如孫過庭所說“造次之際,稽古斯在”,張懷瓘“因文為用,相須而成”可以基本概括詩書關系。其次來看詩畫關系。從題材和技巧來說,詩歌和繪畫本身往往就具有畫境和詩情,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正是就此而言。蘇軾在《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一詩中提出了“詩畫一律”的觀點,從此將詩情與畫境聯系起來。最后來看書畫關系。從繪畫的角度來說,要在畫法中體現書法的筆法,這就是畫法通書法。張彥遠雖然提出了書畫“同法”的看法,但與畫法通書法并非一事。真正產生影響的是趙孟所提出的“書畫本來同”的觀點。從書法的角度來說,要讓書法成為整體畫面的一部分,這就是書法畫面化。總之,只有做到了詩書、詩畫與書畫三種關系的完全融合,文人畫的定型始告完成。
以上主要是從理論上對詩、書、畫的關系加以說明,下面來看實踐的情況。詩書融合首先是通過書法的理論和實踐來實現的,從這一點來說,與繪畫關系不大。但是,當詩書融合以題跋的方式與繪畫產生關聯就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繪畫的形態。就詩畫關系而言,要在實踐上將兩者結合起來,就必須在畫面上題詩,陸機所說“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畫”有助于我們對兩者關系的理解。詩畫關系的這種結合已不只是兩者的并列,而是詩情與畫境的深入溝通,這就與鄭虔、盧鴻的詩書畫區別開來了。宋徽宗是詩畫關系在創作上的有力推動者,他的“御制御畫并書”就是“詩畫一律”的實踐。從他對詩、畫、書的排列來看,顯然強調的是詩畫關系。就書畫關系而言,宋徽宗的“御制御畫并書”并不涉及書畫的融合,到了元代,趙孟才從理論和創作上實現了畫法通書法。柯九思則全面繼承了趙孟的衣缽并創造性地使用了“畫詩書”聯署。與宋徽宗相比,柯九思對詩、書、畫的順序進行了調整,畫、詩、書的排列表明他已經將詩書統一于繪畫之下。如果說宋徽宗的“御制御畫并書”邁出了文人畫形態演進的關鍵一步,那么柯九思的“畫詩書”則標志著文人畫形態的基本確立。需要指出的是,在趙孟、柯九思以及明人的手中,雖然實現了畫法通書法的目標,但是書法畫面化仍未最后完成。事實上,唐代繪畫已很重視書法與畫面的關系,這一點甚至在更早的漢晉繪畫中也顯露端倪。從某種程度來說,宋人將名姓隱藏在枝干、石隙中的做法也是重視書法與畫面關系的體現。總體而言,明代以前畫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畫法通書法上,無論從認識還是實踐來說,書法本身還沒有完全成為畫面構圖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來說,文人畫的定型還沒有完成。
書畫畫面化是文人畫定型的最后一步,金農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雖然傳世的材料不多,但是從中還是可以看出金農對書法畫面化的認識,故宮博物院藏金農致羅聘札云:“二佛像古雅莫匹,真絕藝也。但主像所余紙無多,題記字大小不稱耳。面相須發極畫莊嚴,奇樹忍草,令我嘆賞不置。墨竹紙,明日同墨汁一齊送來,重為我畫,當覓佳物奉酬也。”羅聘為金農代筆已成為研究者的共識,不必多論,值得注意的是,金農雖然對于羅聘所畫佛像“嘆賞不置”,但是仍然要求其“重為我畫”,原因是佛像占據畫面空間過大,從而導致“余紙”與“題記字大小不稱”。故宮博物院藏另一件金農致羅聘札云:“朱竹設色須鮮華而有古趣才妙,多留空處以便題記,復作一篇。”對于這件作品,金農也提出了重畫的要求,從“多留空處以便題記”可以看出,重畫的原因正與佛像相同。這兩條材料都表明金農特別重視書法與畫面構圖的關系,為了達到書法與畫面的和諧甚至不惜毀棄佳作。當然,金農對書法畫面化的重視主要體現在他的創作中。無論什么題材的作品,金農都有大小長短不一的題跋,并且這些題跋與繪畫主體之間形成一種促進的關系。在某些作品中,題跋甚至具有統領畫面的作用。方薰《山靜居畫論》指出“畫可有不款題者,唯冬心畫不可無題”,準確地概括了金農在書法畫面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