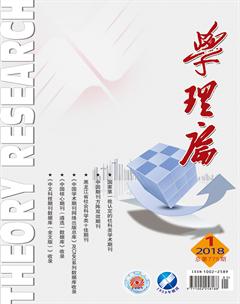文化—環境范式的自覺螺旋
吳捷 劉建濤
摘 要:迄今為止,人類共經歷了三種不同的環境文化范式:農業文化——人與自然基本和諧的環境范式;工業文化——人與自然基本不和諧的環境范式;生態文化——人與自然新的和諧的環境范式。其中,工業文化環境范式具有極大不可持續性,造成了全球性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生態文化則實現了對工業文化的超越,建立了適應自然的生態文化——環境范式,追求以人為核心的人與自然的和諧,從而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關鍵詞:農業文化——環境范式;工業文化——環境范式;生態文化——環境范式;自覺螺旋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8)01-0177-03
范式是指一種理論的構架,一種用于解釋生活與世界的思維中的觀念形式。文化——環境范式體現了文化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強調看待環境問題或者文化問題時,要將二者結合起來,從整體上把握和理解。在農耕時代,人對自然是一種單純的依賴;工業時代,人對自然則變成了野蠻的掠奪。現代生態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環境范式。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1]。人及文化與環境不是相互對立的,他們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環境促使帶有特色的文化產生,文化則促使環境不斷變化。環境和文化之間的關系,表明人是環境的一部分,并沒有站在環境之外。“在脆弱的環境之上很難建立起健康的文化。自然和文化的命運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2]。可見,環境問題與人類文化的確有著內在的關聯。某一地區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從表面上看,好似只是人為的緣故,但是深究其背后的原因,可以發現環境的破壞和該地的文化背景有很深的關系。隨著經濟的發展,人類形成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他們認為就應當對自然資源大肆利用。面對這樣的狀況,單純地發布法令已經很難從根本改善生態環境被破壞的局面。所以,環境問題也從側面反映出人類本身所具有的問題,而且這種問題不是某地特有的現象,而是整個人類社會普遍的問題。正如國家環保部副部長潘岳也指出:“中國環境問題的形成十分復雜,但從根源上看,還是思想文化問題。因為思想文化決定了社會制度、戰略目標、經濟模式、技術形態的選擇設定”[3]。從文化角度來探尋環境問題的本質,生態破壞只是文化危機所披的外衣,即原有環境塑造的文化—環境范式無法修復或調整自身以適應變化了的環境,從而導致了環境的惡化。對此,我們必須深刻反思,要想從根本解決環境破壞的問題,必須首先解決文化危機。
一、傳統農業文化——人與自然基本和諧的環境范式
農業時代大概包括最初的原始農業、中期的傳統農業以及現今的現代農業三個階段。現代農業大量使用農藥、化肥等農用化學品,使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傳統農業基本屬生態農業。傳統農業看似簡單落后,卻是一種以農耕為主要生存方式的文明,也是人類從被動適應自然開始向改造自然的轉變時期。傳統農業時期,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和改造能力還較低,物質條件還比較貧乏,人類依賴自然,維持著基本的生存需求,在傳統農業生產中,農民同土地、同大自然保持著直接的接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種秋收……任何的生產都必須嚴格按照自然的變化來進行。因此,這個時期的人類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建設人與自然之間的友好關系,并且對自然擁有無上的崇拜感,例如對神明的祭祀。傳統農業時期人與自然產生了一種整體性,我國古代“天人合一”的理念就源自于這種整體性。因此,傳統農業塑造的農業文化——環境范式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人高度依賴自然的發展模式,雖然可持續性較高,但易受自然環境影響,發展性低。盡管如此,隨著鐵器時代的到來人類生產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同時對自然的改造能力加強、依賴度降低,人類為了獲取更多的生產資料開始大規模的開墾土地,砍伐樹木。這時,人與自然的關系開始出現了局部的對抗,有些地區產生的后果相當嚴重。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樣:“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但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地方竟因此而成為不毛之地”[4]。但從大尺度的時空看,農業社會的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還相對處在統一和平衡的時代,呈現出人與自然基本和諧的文化環境范式。
二、近代工業文化——人與自然基本不和諧的環境范式
工業文明時代人類逐漸擺脫了對自然的依賴,開始根據自己的需要去改造自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雖然工業文明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且由它塑造的工業文化——環境范式相對于農業文化——環境范式來說,發展性較高,但可持續性較低。因此,工業革命以來短短的200多年間,就爆發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和環境危機,激化了人與自然的矛盾,破壞了人類生存的環境根基。工業文化——環境范式的不可持續性主要表現在其所蘊含的自然文化觀、人類中心主義價值文化觀、發展文化觀所具有的反環境的性質。
工業文明所塑造的自然文化觀具有二元論的性質,它把人視為萬物的主宰,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觀點貶得一文不值。在整個工業文化中,自然始終處在被利用的位置,只能單純為人類提供物質積累。這種偏激的理論使人類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尷尬境地:人類利用自然來創造財富的能力越來越高,帶來的卻是環境的破壞,如倫敦煙霧事件,5天時間就有5 000多人死于非命。在工業文化中,自然被同質化和否定化地建構,不僅給整個地球帶來了無法恢復的生態破壞,同時使人類的心靈產生了嚴重的扭曲——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價值文化觀在西方很多地方都能找到它的理論根據。現代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文化觀發端于西方,成熟于工業文明時期,本質上把人看成一切存在和價值的中心,已內化為現代社會發展模式的深層理念,構成了現代工業文明與現代人生活方式的信念支柱。澳大利亞著名環保主義者約翰·錫德認為“人類中心主義就是人類沙文主義。與性別主義類似,人是生物的君王、一切價值的來源、一切事物的尺度,這一觀念,深深根植于我們的文化和意識之中”[5]。在人與自然的價值關系中,是否具有價值,則完全取決于是否具有理性。人因為具有理性而具有內在價值,自然不具理性,則毫無內在價值可言。在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中,人類是萬物的主宰,人對自然擁有絕對的控制權,自然只是為人類提供物質積累的工具和手段,霸道地將自然被驅趕出了倫理王國。并且人類中心主義價值文化觀對人類的世界觀產生了嚴重的誤導,對人類在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上所產生的偏執性進行了絕對的美化,客觀上助長了人類對大自然不計后果的控制與掠奪,并讓人類對逃避其在生產生活中所造成的嚴重后果的負值效應所應承擔的責任提供了理論依據,而這些失誤又反過來進一步膨脹了人對自然征服的傲慢,進一步加重了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正因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文化觀在價值關系中拒斥自然,在倫理關系中排斥自然,在實踐關系中危害自然,所以遭到國內外學者的批判。海德格爾于1946年秋寫下了《論人類中心論的信》,向人類中心主義價值文化觀發起了挑戰。認為西方傳統的文化都是建立在人類中心論的價值文化觀基礎之上,而且在當代,這種形而上學人類中心論的價值文化觀已經發展到危及世界和人的存在的境地了。總之,在這種價值觀的指導下,人在向自然進攻、征服自然的同時,發展了經濟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實行一種反自然的社會——經濟——消費生活。
三、當代生態文化——人與自然新的和諧環境范式
思想上的片面必然導致認識的錯誤,文化上的缺失必然造成行為的短視。工業文化——環境范式所蘊含的自然文化觀、人類中心主義價值文化觀及發展文化觀的反生態性導致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相互排斥與相互否認,對地球生態系統造成了嚴重的傷害,致使全球生態環境指數不斷下降,生態足跡指數日趨攀升,生態赤字日益擴大,甚至威脅到了人的生存。
這迫使思維著的理性對工業文明的文化基礎進行深層次的反思,迫使人類修復或調適工業文化對環境的不適應,創造新的文化來與環境協調并濟、和諧共進,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生態文化應運而生。生態文化是人類建設生態文明的先進文化,是和諧的環境文化,它是以諧適人與自然為圭臬,以適度消費為原則,以協調性發展為過程,以可持續發展為目的,以和諧理念與環境意識為基本特征的文化范式。以生態理性和生態規律為支撐的生態文化——環境范式,把農業文化——環境范式的可持續性原則與工業文化——環境范式的發展性原則有機地結合了起來,適應了對文化變革的需求,對工業文化價值觀念進行了生態化的重塑,進而實現了對工業文化——環境范式的自覺螺旋,從而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生態自然文化觀打破了工業文明時期自然文化觀的二元論的理論偏執,把人與自然視為相互含有的不可分割的親情機體,主張建立在生態規律基礎上的以人為中心的和諧整體,這一和諧整體不是自然的復歸,而是按照人的類本質的發展規律建立的人化自然的螺旋攀升。在實踐上主張遵循自然的規律并用這樣的規律去作用萬物以利其生存,以成其生生不息之生機。生態化自然文化觀在價值論上實現了對以往人類中心主義價值文化觀的批判性逆轉,注重環境正義與環境的可持續性,注重自然規律、自然因素及生態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價值與影響,視人為自然內在價值的展現。否定了人統治、控制自然的價值取向,把自然納入了道德的規范,用生態化的道德價值規范調控人的思想與行為,認為文明不僅是物質的進步、器物的昌盛,更是德性的成長,主張用道德文化統帥物質文明。這種自然文化觀、價值文化觀運用到社會發展的層面上,豐富了社會發展的內涵,拋棄了把社會發展視為單純的經濟增長的觀點,擯棄了偏離國情的高消耗、高環境影響的發展模式,確立了人與自然互利共生的低消耗、低污染、高環保的發展模式及可持續的發展理念。總之,生態文化——環境范式實現了人的文化系統、精神世界的生態化,目的就是要把環境從人類的過度干預中解放出來,努力實現一種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又可促進環境保護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局面,以實現人類社會在自然環境承載范圍內的永續發展。以此為基礎,江澤民同志指出:“破壞資源環境就是破壞生產力,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能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6]。并且黨的十六大提出把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四大目標之一。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了以人為本、全民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把統籌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黨的十七大又進一步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努力形成一種以“以人為本” “和諧” “可持續發展”為重點的新的發展理念。十九大更加明確指出:要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生態文化——環境范式的核心理念,體現了黨對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所以,我們需使這些友好環境的新理念掌握大眾,依靠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逐步解決我國的環境問題,從文化的深度推進綠色中國的進程,以實現黨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的偉大歷史任務。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39.
[2][美]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環境倫理學:大自然的價值以及人對大自然的義務[M].楊進通,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310.
[3]潘岳.和諧社會與環境友好型社會[J].環境保護,2006(7):14.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
[5]John Seed“Anthropocentrism”,in Devall&Sessions;,Deep Ec-ology pp 243-246.
[6]江澤民.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