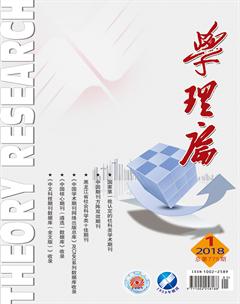傳統與現代轉型
崔凌 梁慶峰
摘 要:啟蒙運動中,英法對待傳統文化迥異的態度對兩國的現代轉型產生了重要影響。英國現代轉型遭遇的阻力較小,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英國啟蒙運動充分繼承并利用了本國道德哲學傳統,以之整合了新興的理性精神和傳統的宗教信仰,并從中發展出了之后成為現代英國經濟和政治制度基石的英國式自由主義傳統;而法國啟蒙運動和大革命以對傳統的反叛開始,卻以無意識的回歸告終,其過程的曲折性從反面顯示出傳統在社會轉型和新文化塑造中不可抗拒的強大力量。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傳統文化的復興和重塑,英法啟蒙運動比較研究對中國現代轉型及傳統文化復興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
關鍵詞:啟蒙運動;傳統文化復興;現代轉型
中圖分類號:G0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8)01-0183-02
“啟蒙運動”開啟了成為整個人類發展目標和生活典范的現代性。長期以來,對啟蒙運動的研究往往更注重整體性,而忽視了各國歷史處境和傳統文化對其現代化轉化的重要作用。本文將聚焦英國和法國,分析兩國啟蒙運動對待傳統迥異的態度及其結果,以揭示傳統在現代轉型中的作用和意義。
一、英法啟蒙運動比較研究
由于歷史處境的不同,英法兩國啟蒙運動對傳統表現出迥異的態度。審慎的英國人堅守并發展了本國的道德哲學傳統,以此協同了新興理性精神和傳統宗教信仰之間的關系,同時催生出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和平等。激進的法國人試圖徹底顛覆以基督教為代表的舊制度,按照理性的原則重建一個全新的世界,但卻事與愿違地陷入一系列深刻矛盾中。
(一)英國啟蒙運動
在啟蒙運動之前,英國已經經歷了光榮革命和宗教改革。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和較為寬容的宗教氛圍使英國文人對本國社會總體比較滿意,他們并不試圖以顛覆性的方式來重新認識和改造世界,也不敵視包括基督教在內的歷史傳統,表現出明顯的樂觀主義態度和溫和的改良主義性情。出于社會改良的目的,同時也基于本國的道德哲學傳統,英國將“美德”置于啟蒙運動的中心,專注于社會倫理的探索和實踐。
英國的道德哲學傳統將美德起源歸于人性中的“道德感”,這是一種人天生固有的對他人產生的“同感”。正如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開篇所論述的那樣,“人,不管被認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人性中顯然還有一些原理,促使他關心他人的命運……”[1]2基于相同的情感基礎和相似的是非判斷,道德感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情感和倫理。個人的痛苦和快樂也與之相連,惡行導致痛苦,美德產生快樂,這樣個人利益也就和普遍的社會利益聯系起來了。
在英國,新興的理性沒有被推崇到至尊地位,傳統的宗教也沒有受到敵視,因此理性和宗教之間沒有產生像在法國那樣激烈的沖突,相反,二者以自然神論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共同成為道德的同盟。理性提供真與假、對與錯的普遍原則,而宗教則通過上帝來強化這些原則。英國啟蒙運動的領軍人物,包括休謨、斯密和吉本,即便對基督教存有懷疑,也絕不否其重要的道德和社會作用。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論述了宗教信仰如何驅使人們遵守自然的義務感,“對于那些似乎深懷宗教情操的人,人類通常會比較信任他們的誠實正直。”[1]206吉本則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贊美由個人美德支撐信仰的早期基督教徒[2]。即使是最具懷疑精神的休謨,也至多是一個不可知論者,而絕非無神論者。他在《英國史》中主張,在每一個文明社會,都應該有基督教秩序和宗教的公共機構[3]。在法國走向無神論極端的時候,英國“狂熱的”衛理公會卻蓬勃發展。衛理公會宗教性極強,又缺乏理性色彩,常常被視為“反啟蒙”力量,但實際上它卻十分符合英國啟蒙運動的精神內核——他們推崇宗教寬容和自由,極為重視道德教誨,大力推廣慈善和人道主義事業。衛理公會在溝通世俗和宗教、公共和個人之間發揮了積極的社會作用。正是這種宗教、理性和道德的相互協調和互通實現了基督教的現代化轉化,使基督教從權威教條過渡到理性宗教,最終落腳于道德實踐[4]。
英國人對自由的追求同樣基于他們對人性的樂觀,他們相信尊重人類社會的自由發展是促進其進步的最好方式。英國人的樂觀主義并非理想主義,他們對人性利己主義的認識絕不亞于“道德感”,但他們相信自由的體系可以使利己主義有助于普遍利益。勞動者在這個自由體系中工作,雖然是出于對個人利益的追求,但同時也滿足了社會各方的利益。這就是亞當·斯密《國富論》中那只“看不見的手”,它協同了個人利益和普遍的社會利益,無意識地推動了社會進步和福利。這就形成了英國式自由主義傳統:相信漸進式的改良,相信社會發展的自發秩序;保護人的自然權利,控制政府對自然秩序的人為干預,以保障個人和市場的自由。
在英國啟蒙運動中,人性勝于理性,這就引出了一種平等主義的觀點:人性是所有人所共有的自然天性,即使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斯密在《國富論》中把“普遍利益”推及到了“國家”的概念,認為國家的財富并非是衡量其力量的指標,而是組成這個國家的人民[5]。斯密的觀點是劃時代的,它打破了對窮人的傳統偏見,即認為應當讓底層階級保持貧困,只有這樣他們才會為了溫飽而勤奮工作。對底層階級的同情和善意,使人們開始關注窮人的苦難境遇,催生了大量的民間慈善組織,也使英國成為第一個、也是長期以來唯一一個擁有國家貧困救濟體系的國家。
英國啟蒙運動,從哲學理念到社會實踐,都基于并進一步發展了其道德哲學傳統,以此整合了新興的理性和傳統的宗教,使二者作為道德同盟從屬于道德哲學。“道德感”從個人情感出發,形成普遍的“社會美德”,從而聯結、平衡并協調了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因而,英國人一方面珍視個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重視社會的普遍利益;既追求財富的增長,又關注窮人的苦難。英國啟蒙運動的時代被稱為“仁愛的時代”,雖然沒有法國啟蒙運動“理性的時代”那么雄心壯志、波瀾壯闊,但顯得更為務實和人性,更符合英國冷靜而審慎的性格和傳統,同時也更利于完成英國現代化轉化過程中物質改善和道德提升的歷史任務。
(二)法國啟蒙運動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中以本國知識分子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來解釋英法啟蒙運動的差異:在英國,作為政策理論家的知識分子和政府管理者是相互合作的關系,一方提出新的理論,另一方根據實際經驗修正這些理論或限定它們的范圍;在法國,這兩者是完全分離的,法國哲人很難對管理者的實際政策產生影響,因而他們一方在理論上提出好的政策而不考慮實際的應用,另一方則根據需要而不是理論實施必要的措施[6]139-148。這種在政治上缺乏影響力的地位反而使法國哲人不受現實的約束,更加大膽而自由地思考和推廣抽象的理論原則,但另一方面這些理論在遭遇現實問題時往往又容易陷入深刻的矛盾中。
如果說英國啟蒙運動是一場漸進的社會改良運動,那么法國啟蒙運動則是一場渴望改天換地的革命運動,它立志要建立一個全新的理想世界,這個理想世界的最高準則就是理性。宗教作為舊傳統的代表,理性的對立面,成為法國啟蒙運動的頭號敵人,遭到了哲人們最嚴酷無情的批判。哲人們希望通過啟蒙運動,解放被基督教束縛、處于蒙昧狀態下的民眾的崇高理想,但矛盾的是他們又時常流露出對普通民眾的不信任,認為他們“太白癡—野蠻—太可憐,而且太忙”,而不能被啟蒙,普通人需要一位“上帝、造物主、統治者、優勝者、報復者”來對他們進行約束,“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有必要造出一個來。”[7]這種對待基督教和理性矛盾的態度,正是法國啟蒙運動理論原則和現實傳統分離的結果。理論上,哲人們堅信打破宗教迷信、樹立理性權威能使這個時代的人變得更聰明、更高尚、更幸福;但現實中,他們卻發現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擁有或愿意接受理性權威,而基督教傳統更是深深扎根于普通民眾之中。法國哲人對基督教傳統的犀利批判固然給人一種暢快淋漓之感,但他們無視基督教一千年來對歐洲文明的奠基和塑造作用,也無視法國民間對基督教的情感和精神需求,使得他們的批判顯得膚淺且非理性。這種過于急切的反傳統態度也使他們對自身反思不足,最終在本質上法國人終究沒有沖破崇拜權威的傳統,不過是以理性的新權威替代了宗教的舊權威。
對于這種過于“高貴”而不具有普遍性的理性的偏愛,還導致了哲人們對自由的矛盾態度在觀念上向往自由,卻在制度上偏愛專制。許多法國哲人都曾遭遇過審查、監禁和流亡避難,因此他們普遍渴望自由的宗教和政治氛圍。然而在政治和社會實踐中,哲人們卻表達出對“開明專制”和“普遍意志”的偏愛和崇尚,認為睿智開明的君主是普遍意志的代表,必須保障其基于理性的道德和政治權威。托克維爾在總結大革命時曾明確表明對開明專制的支持:“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并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6]2在法國,自由僅被限于市場。法國人矛盾地認定一個有力的政府、擁有絕對權利的君主,即開明專制,是確立經濟自由環境的必要保障。
這場意欲改天換地的思想和社會革命運動,卻最終沒有脫離法國對某種一手遮天權威力量崇尚的傳統。于是他們一邊奮力打破宗教權威,一邊又建立起理性權威;一邊渴望著自由民主,一邊又以專制來保障自由。“……他們在不知不覺中繼承了舊制度的大部分思想、觀念與習慣……他們利用舊制度的磚石建造了新社會的大廈,盡管他們并不是要故意如此。”[6]5在付出沉重代價之后,法國人意識到徹底的摧毀和重建非但不是捷徑,反而是死胡同。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既贊美了法國人的革命激情和理想,又深刻反思了他們天馬行空的理想主義。這種脫離實際的理想雖然廢除了法國人痛恨的舊制度,卻使他們錯失了對舊制度進行深刻而緩慢的改良的機會,到頭來反而使他們在潛藏的未經改良的舊制度的影響下逐漸偏離了起初的目標。無論目標和理想是多么正確和高尚,無視傳統、意欲與歷史割斷仍是一種簡單粗暴且往往事與愿違的變革方式,法國啟蒙運動和大革命正揭示了理論理想與現實傳統之間這種不可分割的聯系。
二、英法啟蒙運動對中國現代化轉化的啟示
近代以來,對啟蒙的渴求,使眾多中國人痛心疾首地看到了自己傳統文化的弊端,近代西方國家的成功轉型和迅速崛起更是為中國啟蒙者提供了奉行西學的理據。一時間,西學盛行,傳統文化受到巨大沖擊。這種極端的方式斷送了啟蒙精神轉化為中華民族內在價值的可能性,因為沒有充分的本土價值作為消化這套外來資源的基礎,這導致了中國啟蒙運動屢屢受挫,西方政治、經濟和文化模式在中國的實驗問題重重。
對西方不同國家啟蒙運動的對比研究,對中國啟蒙運動和現代化轉化有著非常有價值的借鑒作用。首先,英法啟蒙運動的差異性研究打破了對啟蒙和現代化的模式化認識,使對當下處境的探索更加符合本國實際的現代化路徑。其次,英法兩國的啟蒙運動和現代化道路極具代表性,一個是在沿襲傳統的基礎上所進行的漸進式的改革,另一個是在打破傳統的基礎上所進行的突進式的革命。雖然兩種模式都在本國特定的歷史處境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和意義,但就啟蒙運動和傳統文化的關系這一方面而言,英國啟蒙運動和現代化轉型所遭遇的阻力較小,連續性強,發展較為順利,這與英國充分繼承和利用傳統文化資源密切相關。而法國啟蒙運動和大革命以對傳統的敵視和叛逆開始,卻以無意識的回歸告終,其過程的反復和曲折則從反面顯示出傳統在社會轉型和新文化塑造中不可抗拒的強大力量。第三,英國啟蒙運動對傳統的利用和發展為儒學的現代轉型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鑒的范例。英國并沒有將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相反,傳統成為了實現現代轉化的必要資源。英國的道德哲學傳統不僅整合了新興的理性精神和傳統的宗教信仰,更從中發展出了之后成為現代英國經濟和政治制度基石的英國式自由主義傳統。當代中國的歷史處境和啟蒙時期的英國有著幾分相似,都有著豐富的道德哲學傳統,都在經歷了一系列改革后處在一個比較穩定且寬容的社會環境中。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如何整合現代精神和傳統價值,如何利用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從中發展出新的現代傳統,從而實現“中國式”而非“西方中心主義”的啟蒙和現代化,將是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參考文獻:
[1][英]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M].謝宗林,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
[2][英]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M].席代岳,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380-383.
[3][英]大衛·休謨.英國史III[M].劉仲敬,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2:134-135.
[4]崔凌.基督教在西方現代轉型中的解構和重構[J].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55-59.
[5][英]亞當·斯密.國富論[M].謝祖鈞,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8.
[6][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M].陳瑋,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
[7][美]格特魯德·西梅爾法布.現代性之路:英法美啟蒙運動之比較[M].齊安儒,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