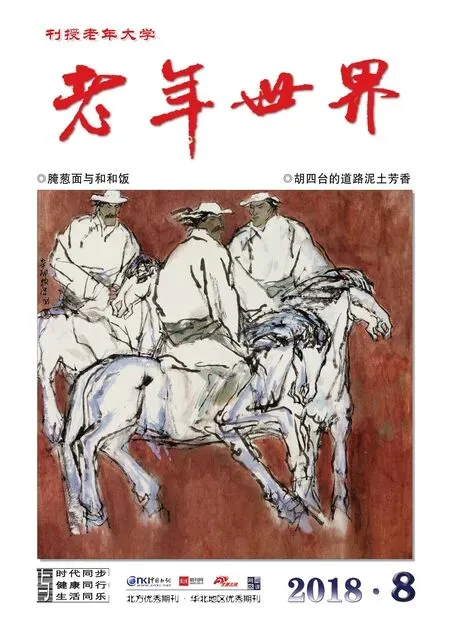延安憶往
云照光
民族學院
1941年春,國民黨發動了皖南事變,掀起了反共高潮,形勢非常緊張,邊區財政經濟也更加困難。在這個時候,黨付出人力物力,把陜北公學和中央黨校的包括7個民族的數百名學生合編在一起,成立了陜公附屬的民族部。整個夏天,我們都在清泉旁邊的巖石下上課,學員不斷地增加著。為了適應抗日形勢的迅速發展,更加具體地體現黨的民族政策,培養各民族抗戰和建國的骨干,中央作出了使人無比興奮的決定:成立各少數民族的最高學府——民族學院。這個消息,很快在教職學員中傳開了,大家的那股高興勁兒,簡直無法形容。1941年9月18日,是一個風和日暖的好日子,就在這一天,各民族子弟向往的民族學院正式誕生了。毛主席和許多中央首長送來了賀詞,祝賀這所新的學府的誕生。兄弟學校也派來了代表,送來賀信、賀詞,和我們共同歡度這個快樂的日子。成立一所真正的、各民族人民的學院,是中國有史以來沒有過的事,是少數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頭號大喜事,誰能不盡情地歡慶呢?我們由五十五隊變成民族部,又變成了民族學院,是由小到大、突飛猛進地發展著。除了各民族人民的救星中國共產黨,任何一個朝代,任何一個政黨,是絕對辦不到的。況且,那時是在抗日戰爭緊張的年頭,是在艱苦困難的環境里,不惜用最大的努力,修建校舍,添置教學設備,配備堅強的領導干部和教職員,使各民族的子弟們團聚在一起,在溫暖的大家庭里學習、生活,這確實是偉大的創舉。我們都以無可比擬的感激心情,來歡慶這個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各民族的代表,不斷擁到主席臺,向中央、向學院首長表達自己的心情和決心。到處敲鑼打鼓扭秧歌,到處張貼標語和墻報。晚間舉行了慶祝晚會,各族青年演唱了自己民族的歌曲,演出了自己編排的話劇和秧歌劇。就在這一天,我們全校數百人,用激昂而又洪亮的聲音,第一次唱出了我們的院歌:

民族學院舊址(資料圖)
我們是各民族的優秀子孫,
我們是中國真正的主人。
漢、滿、蒙、回、藏、苗、彝,
親密地團結在一起。
今天是各民族學習的伙伴,
明天是革命戰斗的先鋒。
同志們,讓我們攜起手來,
高舉起民族革命旗幟,
邁步走向平等、幸福、各民族團結的新中國!
慶祝晚會一直進行到深夜結束,但大家激動的心情,卻久久不能平靜。
我們學院,在延安文化中心的文化溝,和西北文藝工作團、西北青年劇院、文化俱樂部是鄰居。北邊翻過山就是中央黨校,對面是規模龐大的中央圖書館。南邊有能容納近2000人的八路軍大禮堂,醫療上有比較正規的八路軍醫院,溝口有當時延安最大的運動場。往前走,就到了清澈似鏡的延河邊。四面的山頭上,長滿野草,還有一片片紅紅綠綠的酸棗林,真是一個優美而又熱鬧的環境。來自四面八方的7個民族的青年,在這個舒適的環境里緊張地學習著。院長由中央負責同志兼任,云澤(烏蘭夫)同志是學院的教育處長。我們的課程有漢語文、數學、地理、歷史、時事政策、政治理論、生理衛生、新文字以及不定期的民族問題的報告。最使人感動的是,雖然延安條件很差,但是黨盡量設法從別的機關、從前方調來一些教員,擔任各民族的文字教學工作。因為苗族沒有文字,西北局還專門組織研創苗文。為了尊重各民族的風俗習慣,特別為回族學生另立了食堂,每逢吃肉,都要由阿訇親自屠宰。在那樣困難的情況下,還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供回族學生做禮拜,使伊斯蘭教信徒像在自己家里一樣,無拘無束地生活著、學習著。少數民族學生的身體健壯,按一般伙食標準不夠吃,邊區政府特意每月多撥糧食,作為補助。圖書館、體育場、俱樂部、課堂等各方面的設備,也比別的學校好。黨對少數民族的關懷,真是無微不至啊!

1942年秋天,在中央大禮堂召開了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會,這是一個東方各族人民團結的大會、戰斗的大會。幾十個民族的代表,都聚集一堂,一致聲討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并提出:東方各民族人民團結起來,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各民族的解放事業奮斗到底。在會上聽到了各被壓迫民族的血淚控訴,也聽到了各民族反抗侵略者可歌可泣的戰斗事跡,使我們這些少數民族的青年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國際主義教育。這個大會,增強了我們爭取勝利的信心。大會的最后一天,毛主席也來了。正當蒙古族代表的講話剛結束,突然全場起立,掌聲雷動。我坐在過道的旁邊,也跟著大家站起來,隨著大家的眼光向后看去。一個高大魁梧的身影,已經匆匆地從我的旁邊走過去。我喜出望外,把頭伸過去,用盡所有的力氣鼓掌。這時,毛主席已經走上主席臺了,接著就開始了講話,聲音是那樣清脆洪亮。毛主席號召各民族親密團結起來,打倒一切法西斯侵略者,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下,發揚高度的國際主義精神,進行轟轟烈烈的反法西斯運動。毛主席的講話,給了我們更大的溫暖和鼓舞。
通過系統的學習,經過幾次政治運動,我們在政治上大大地進步了,各民族的大批優秀青年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后,大批的同學畢業了。有的到敵占區進行艱苦的地下工作,大部分到了抗日的最前線,投入了轟轟烈烈的戰斗。在和敵人的斗爭中,體現了忠于黨、忠于民族解放事業的堅定信念。像關起義、朱玉珊、趙青山、云晨光、圖布新、云貴生、巴增秀、李世昌、金玉、楊秀清、秦子華、雷明利等許多優秀的黨員,就是在艱苦的戰斗中犧牲的,表現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有的同學在對敵斗爭中犧牲了,有的成了模范和英雄。各族青年,沒有辜負黨和母校的希望,投身了轟轟烈烈的事業,忠心耿耿地盡了自己的責任。
母校啊,你培養了多少少數民族的干部!你把我們從無知引到革命的道路上來,你給了我們無窮的力量、無限的智慧和革命斗爭的知識,你教給了我們如何做一個真正的革命戰士。這偉大的功績,歸功于黨,歸功于我們敬愛的母校。母校,你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里!
燒木炭
延安所有的機關學校,都住在窯洞里。人們都說窯洞是冬暖夏涼的神仙洞。不過到了冬天,也并不見得暖和,因為沒有像樣的行李,床上只鋪著幾塊薄門板,洞里又潮又濕,還是怪冷的。過冬怎么辦呢?買炭,一個錢也沒有,做飯還是同學們上山打回來的木柴。就是有了炭,也很難找到一個火爐子。最簡便的辦法就是到深山里燒木炭。陜北有許多原始森林,只要出勞動力,不用花幾個錢,就能燒出木炭來。況且,這木炭實在是寶貝,它既不用火爐,也不冒煙,只要在地下圍幾塊土坯,見火就著,一夜都不熄滅。1940年冬天,我們自己組織起來去山里燒木炭。當時因為我年齡太小,做了“火頭軍”的助手,擔水燒火。1943年民族學院和延安大學合并了,好幾千人的過冬問題,是個大事情,學校首長和校黨總支把任務交給了我們這支已經經過燒炭考驗的生產大軍。出發前,周揚副校長、宋侃夫總支書記給我們做了動員。
從橋兒溝出發,走了20多里地,就拐進一個小溝。走不多遠,就看見滿山滿溝一片綠,到處是原始森林,山溝、山坡到處都是野花、野草,還有許多野生果樹。我們的生產地點是瓦房,其實并沒有幾片瓦。養蜂的人家倒挺多,都住在窯洞里。因為我們都是燒木炭的老手,用不著什么訓練,第二天就動手勞動了。
出發的時候,我就下定決心,這次再不干“火頭軍”了。但事與愿違,生產隊長偏偏分配我當“火頭軍”,有什么辦法?只好接受了。我和隊部住在一間快要倒塌了的窯洞里,每天收工回來,我就磨蹭,要求干點別樣的事。可能是讓我說得有點心軟了,不久,隊部決定把我正式升為燒木炭工人。但重要的活還是不讓我干,我只好滿山跑,割苧條,捆木炭包。我們的小組長是彝族同志,是個大胖子,我們小組5個人經常在一起,分開就很危險,因為不時會碰到豹子、碰到成群的野豬和各種可怕的野獸。
腰粗的大樹,被我們幾斧子就砍倒了,再鋸成好幾節,粗細搭配開,放到一個土窯洞里,用土埋上,只留一個通風孔和煙筒。說起來,燒木炭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每道工序都有技術。白天黑夜都要留神放哨,稍不注意,一窯炭就化成灰了。只要看到煙筒冒青煙,就堵好通風孔,過幾天取出來,木頭已經變成木炭了。取木炭的時候,因為是高溫,脫光衣服進去一分鐘就滿頭大汗,呼吸都很困難。我們有幾個得了感冒的人,進去取了一趟木炭,病也給治好了。砍大樹的人都是彪形大漢,分布在四處的山上。你站在溝底聽吧,這里哼嗨,那里哈呀,有的唱著,有的叫喊著,手起斧落,噼啪亂響,大樹嚓的一聲便倒下來了。你看吧,砍樹手站在那里,滿頭大汗,滿手血泡,掏出毛巾,擦上幾把汗,又開始征服第二棵大樹了。一直把一片樹林砍成光禿子,這一窯木炭的材料才算準備完了。
勞動雖然累,但那是快樂的累。收工回來,大家蹦蹦跳跳,有的還趕著排劇。不久,一垛一垛的木炭就用騾子、毛驢、大車運回學校了。
有一天正要開飯,隊長王鐸同志拿出一封學校給我們的慰問信,密密麻麻寫了一大張。當他念完最后一句話的時候,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動,但是誰也沒有鼓掌,有幾個人感動得流出了眼淚。劉金(云世英)同志實在忍不住了,站起來激動地說:“我們用什么行動來報答這種關懷?請隊長轉告全校黨員,告訴全校師生,我們一定要超額完成任務,保證全校過冬!”誰能不同意呢!學校不但在慰問信的字里行間表現了階級的愛、同志的關懷,還用全校黨員繳納的黨費,給我們買了5只羊,隨慰問信一起送來了。要知道,那時一個黨員能交多少黨費呢?有的同志盡量節省,只能交幾分錢。是的,這是黨、這是全校對我們的慰問和支援,我們不但要保證勝利而歸,而且要用勞動的熱情,投入到整風學習中去,投入到今后的一切工作中去。
學習武裝了我們這些少數民族青年的頭腦,勞動鍛煉了我們這些少數民族青年的意志。我們不僅有了工人階級的立場觀點,還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學習了階級斗爭的知識,也學習了生產斗爭的知識。我們在黨的直接關懷、教育下,一天天成長起來。
延安是我再生的第二故鄉,是我長大成人的地方,她有多少事情值得我們回憶和懷念啊!延安,當我憶起往事,又看到現在,怎么能不感激你,怎么能不向往你!啊,延安,我多么想再回到你的身旁,看看你現在的千變萬化呀!
選自《延水情深》
云照光,蒙古族,內蒙古土默特左旗人。1929年10月出生,1939年7月參加革命,1945年5月入伍并加入中國共產黨。1966年9月轉業,歷任內蒙古自治區文聯主席,文教委副書記、副主任。“文革”后歷任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局黨組書記、局長,文聯黨組書記、主席,宣傳部副部長、黨委顧問、文明辦副主任,自治區第五、第六屆政協副主席,文聯名譽主席、關工委副主任。全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級文學創作,著有《云照光電影劇本集》《云照光文集》《云照光攝影集》等,主持編輯了《土默特文化》《圣地之魂》《一代英豪》叢書。現任延安大學校友總會名譽會長、內蒙古校友會會長,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理事、內蒙古延安精神研究會會長,內蒙古大學校友總會名譽會長。2003年12月離職休養,享受正省級醫療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