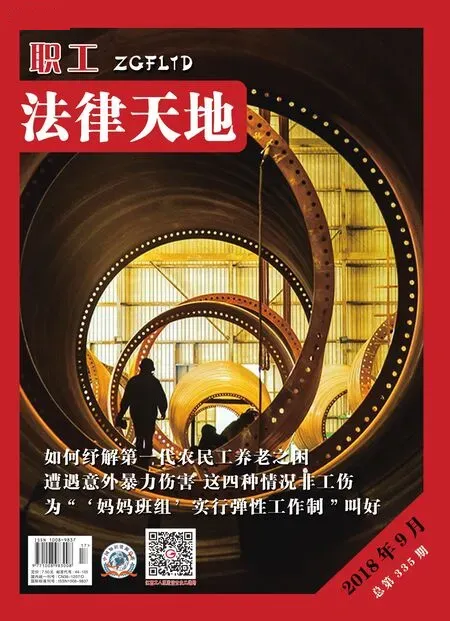如何紓解第一代農民工養老之困
□宗 禾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大量勞動力密集型企業落戶在我國沿海地區,那里也成了最早一批外來務工人員的聚集地。自那以后,或始于維持生計的初衷,或懷揣著發家致富的愿景,一批批的農民背井離鄉,進入工廠,走進城市,把青春歲月留在那里。經濟學家在總結中國經濟騰飛的原因時,都特別強調“勞動力紅利”因素。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用勤勞的雙手,撐起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片藍天。
如今,我國第一代農民工都年事漸高,不少人已年過花甲,在拼體力的勞務競爭中他們不再具優勢,這個群體已到思考人生歸宿的節點,面臨著“去”與“留”的抉擇。
面臨“裸老”命運的第一代農民工
隨著第一代農民工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養老保險的遺留問題已經顯現,并且將在未來數年內集中顯現。
近年來,深圳市社保部門被農民工群體接二連三地告上法庭。“旁聽席第一排的,你們分別叫什么名字,是哪一方的?”龍崗區法院小小的審判庭里坐滿了人。庭審未開始,法官便逐個詢問旁聽者的姓名與立場。在奇怪的開場白下,所有人都伸出右手,指向了原告席。循著人們的目光,可以看到一個穿著暗褐色短袖、身板單薄的女人,偶爾回應法官的問話,聲音低得聽不見。這一切讓她在嚴肅的法庭上顯得毫無存在感,雖然她身后有一支強大的“后援團”。她叫蘇貴琴,是最早起訴社保部門的農民工之一。她在一家工廠里打了10年工,老板沒有給她交過一分錢的養老保險。社保部門說,根據現行政策,只能補繳兩年之內的保險。“憑什么只能補繳兩年?”蘇貴琴將社保局告上了法庭。這支“后援團”來自深圳的各個工廠。與其說關注著蘇案,不如說他們關注著與養老保險補繳有關的一切。是否能成功補繳,關系到他們后半輩子的衣食冷暖。而在法庭之外,還有散落在深圳乃至全國各個工廠里的老工人,他們或是訴求無門,或是認了命,無可奈何地回到農村。
他們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跟隨打工大潮南下深圳。同時,他們也是逆潮而動的一批人:在同一家廠里一干就是十幾二十年,工作的穩定性讓他們看起來與城鎮職工無異。但在退休的節骨眼上,他們卻因為沒有繳滿足夠年限的養老保險,可能面臨“裸老”的命運。
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我國農民工群體的老齡比例連年攀升。目前,在農民工聚集的廣東深圳,異地來深勞務工參加養老保險的比例雖然達到八成以上。然而,大多數農民工的參保年份在2008年之后。這意味著近年退休的農民工里,將有一批人因不滿15年繳費年限而無法領取養老金。
一份民間調研報告顯示,六成以上的農民工不了解領取養老金的條件,也不知道補繳政策。而對每天在流水線上干活的農民工來說,“沒有途徑去了解”成為最主要的原因。許多人到快退休時開始關注養老保險,才發現這扇門早已關上了。
幾多憂愁幾多無奈
在深圳,李秀梅第一次知道農民工也可以“退休”,是2011年12月。
從那時開始,李秀梅留了個心眼,每年廠里都有三五人退休,絕大多數人的養老保險沒達到《社會保險法》規定的“累計繳費滿15年”,因此也沒法“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于是,他們中的大多數,選擇了退保。
到目前為止,李秀梅所在的“千人大廠”里,大伙唯一知道的“成功退休案例”,是一位湖南籍的男主管。但他也不是順風順水的,他退休時養老保險繳夠了10年,在老家又有一點人情關系,于是轉回老家某單位“掛靠”繼續繳費,如今已快滿15年,馬上能領到養老金了。年紀大了,每個月還能有一兩千元,在老家農村,是招人羨慕的。
這個“案例”在廠里廣為流傳,畢竟,五十來歲的“老人”越來越多。根據調查報告顯示,近些年退休或正考慮退休的農民工,已超過5000萬人。
李秀梅也是其中一員,前幾個月,她滿50歲了。

某種程度上,她代表了第一代農民工的退休尷尬。她發現,自己雖然從上世紀90年代就來到深圳工作,但直到2004年起廠里才給她買了“當年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養老保險,如今已繳12年零4個月;麻煩的是,她想補繳2004年之前的養老保險,或者延長繳納期限,補齊15年的期限,可究竟怎么做?對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她來說,實在是一件難以操辦的事。
如今五六十歲的農民工群體中,養老保險繳滿15年的并不多。畢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民工的普遍觀念是“干一天算一天”,根本就不會去奢望什么養老保險。
比如肖葉青,若不是10年前工廠老是“無故”給她放假導致掙不到錢,她也許至今都接觸不到“養老保險”這個詞。當年她和工友們集體去問老板“放假的原因”,原來是為了應付“上頭檢查”,沒有繳納社保的員工不能到車間去。她似懂非懂,但她知道,與每月放假減少的收入相比,自己繳納一點社保不算什么,于是肖葉青才有了買社保的契機。
想不到,等到她2014年退休,問題又來了。她從2006年繳起,尚不滿8年,更不用說15年了!如今,工廠也倒閉了。對已經52歲、文化程度不高的肖葉青來說,進退兩難。
上世紀九十年代就能有意識繳納養老保險的農民工少之又少,所以到了退休年齡能拿到退休金的第一代農民工可謂鳳毛麟角。
早在2003年,深圳就有了第一位退休農民工,他叫郭錦釗,從1987年在某賓館做保安和客服人員,整整干了16年。幸運的是,賓館一直給他按時繳納養老保險,2003年退休時他每月能領到養老金700多元。當年曾被媒體廣泛報道,郭錦釗自己都沒想到“能像城里人一樣拿退休金養老”!實際上,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早在1982年就開始試行勞動合同制職工養老保險制度,1987年開始在臨時工中推行養老保險退休基金統籌,郭錦釗是第一批。
深圳市社保部門曾在2007年首次通報,220名農民工享受深圳養老保險待遇。到2010年,這個數字是320人,人均養老金為1500元。但是,這個數字與當下數千萬正要退休的農民工群體相比,實在太少。
不過,我國在養老保險統籌上,一直在進步。以農民工數量較多的深圳為例,1989年,深圳被確定為全國社會保險制度綜合改革試點地區,后來借鑒了新加坡經驗,1992年在國內率先創建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并能與統籌賬戶相結合;1995年深圳頒布規定,允許外來農民工離開時可以退保……

2010年,國家出臺《社會保險法》,其中第十六條規定:“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個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繳費至滿十五年,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也可以轉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按照國務院規定享受相應的養老保險待遇。”肖葉青一直珍藏著當年從宣傳攤位上拿來的這份文件,在第十六條下,重重地畫了黑線。
據深圳社保中心統計,2008年該市近500萬人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但當年退保的人數多達83萬人;而東莞2007年就有超過60萬人次辦理了退保手續,一天最多時退保金達30多萬元。“那時大家都在問,可不可以不買,而且很多人都認為交了以后就退不了了。”很多農民工這么說,許多人都是到快退休時開始關注養老保險。
而對肖葉青來說,工廠的倒閉,使她補繳養老保險的希望也落空了。已經交了7年半的養老保險依然放在社保局,尷尬的是,這筆錢不知如何處理好。由于城鄉養老保險轉移接續的操作問題尚未解決,無法轉回老家;由于深圳市出臺的相關規定,補繳社保只有兩年的追溯期,所以她目前也補繳不了。她打起了官司,希望能通過法律手段,為自己爭取養老金。
深圳市的有關規定雖然允許企業與工人協商補繳,但兩年的追溯期與“按日加收萬分之五的滯納金額”大大增加了工人們與企業協議補繳的難度,一名工人粗算了一下,10年的補繳金額為3萬元,而滯納金則高達10萬元。
事實上,即使工人與企業達成補繳協議,目前來看,他們依然無法實現養老夙愿。因為農民工養老不僅是一個群體的問題,更是一個體系性的課題,是一項涉及面廣的綜合性改革。
多管齊下破解農民工養老困局
由于收入低、故土難離等原因,第一代農民工中的絕大多數不會在城市頤養天年,而是會選擇葉落歸根,回到農村。隨著第一代農民工整體步入老年,養老問題必須擺上議程。這一特殊群體的“超齡”打工生活、背后的辛酸以及即將到來的養老困局,應該進入我們的視野。
時評員凌國華在光明網撰文指出,在社會養老金存在較大缺口等整體形勢至今仍不甚樂觀的情況下,農民工養老可以說更是難上加難。這不單單體現在農民工養老工作的面大線長,更因為城鄉二元化等歷史遺留和現實困境的加劇,故使得農民工養老一直停留在“養兒防老”的“自給自足”層面上。體制內外存在兩套截然不同的養老體系,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工自然無法獲得體制內的“垂青”,而鑒于農民工只是暫時離鄉的打工者,他們的最終身份仍舊是農民,這也就使得他們的養老困局仍舊桎梏在城鄉二元化所帶來的制度迷思當中。
改革開放40年了,第一代農民工群體收獲了辛酸、歧視以及并不豐厚的收入之后,他們的身體逐漸佝僂,勞動力市場的激烈競爭使得他們不再有任何競爭力,“沒有活干”是他們不能改變的趨勢,更大的困境則在于,已經整體步入老年的他們,能否“頤養天年”,又該如何“頤養天年”?傳統社會的斷裂使得“養兒防老”的模式已經難以滿足日漸增長的養老需求,而體制造成的裂縫短時間內難以彌縫。如此看來,橫亙在農民工面前的養老困局,顯然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問題。

對于第一代農民工來講,不論是“超齡”的堅守還是被迫的返鄉,都無法抹去改革開放大背景下的時代變奏色彩。這些年過半百甚至已屆花甲的農民工,不論是仍堅守工地出賣殘存的體力,還是回鄉依附離開已久的土地,顯然都無法回避養老難題。而40年巨變導致的經濟結構、家庭結構以及傳統觀念的嬗變,都在或多或少侵蝕著鄉村“養兒防老”的社會保障模式。不錯,40年中農村也在發展,但卻是城鄉二元化體制下的不平衡發展。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城鄉間的鴻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這對于包括養老在內的農村公共保障無疑是個嚴峻的挑戰。
不論是從區域經濟均衡發展來講,還是從農村、農民、農業等“三農”問題的重要性來講,發展都不能畸輕畸重,不能搞體制歧視,更不能讓本就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群體(包括農民工)為發展墊底。“三農”問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包括農民工群體在內的農村養老問題又是其中不能忽視的重要問題。從社會資源配置、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講,包括養老在內的農村公共服務也應該有一個明顯的提升。從“三農”的層次上說,中國夢應該也包括興農夢,應該讓農村更公平地享受到改革發展的紅利。
包括農民工養老在內的農村養老困局亟待“破題”。農村養老應該而且可以多元化,公共部門、社會以及個人都應該是農村養老的主體。在制度設計上,可以借鑒新農村合作醫療的模式,政府補貼一部分,個人承擔一部分,同時要鼓勵企業等社會組織發揮應有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包括農民工養老在內的農村養老問題,更應該放到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大背景下綜合考慮,新型城鎮化過程要探索農村養老的新模式,將農村養老納入土地流轉、農村社區建設等過程中,這樣不僅免除了農民的后顧之憂,更有利于提升土地流轉、新農村建設以及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質量,從而在更大程度上釋放制度紅利。
“第一代農民工”年輕時為國家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如今他們老了,卻陷入老無所養的尷尬境地,政府對他們進行政策扶持,助他們解決老有所養的問題,這是值得期待的。
紓解第一代農民工養老之困,需要更多制度反哺,讓背井離鄉建設城市的勞動者在退休時享有基本的保障。第一代農民工的境遇,實際上是農民工群體權益保障不力的現實投射。因此從根本上而言,解決的落點還是要放到農民工權益保障的基礎上來,實現權利的平等,讓勞動者共享發展成果,包括第一代農民工在內的所有勞動者,才能更有尊嚴、更加體面。破解第一代農民工養老困境意義深遠,不僅能切實解決這些人面臨的現實困難,還可以為新生代農民工今后養老探索出一條制度性路子來。從現實看,農民工養老問題主要聚焦在兩個方面:一是收入問題,社保能否覆蓋到每名農民工,到了和城里人一樣的退休年齡,養老金能否支撐他們的生活開支?二是看病問題,醫保能否解決農民工看不起病,重大疾病會不會導致他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

不論是收入問題還是看病問題,反映的都是農民工養老的制度性缺失。目前,政府層面已經形成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大多從宏觀層面出發,對農民工自身的特點考慮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導致制定的政策難以達到預期效果。比如,規定參保只有累計繳費滿15年才可領取退休金,但農民工從事的多數是體力活,多數是靈活就業,鮮有單位會這么長時間雇傭他們;又比如,農民工流動性大,養老保險關系“轉移難”卻一直得不到徹底解決,省際之間缺乏有效協調機制,從而造成“參保——退保——再參保——再退保”的惡性循環,等等。
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曾動情地說:“從社會公平角度講,也不應該讓上億的人口把青春獻給城市,把養老負擔甩給農村。”破解農民工“城市無法養老、農村無力養老”,不僅需要制度層面的改進,更需要健全的法律規范作保障。當務之急是加快農民工養老保險立法,或采取“進城養老”立法模式,把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的適用范圍;或采取“返鄉養老”立法模式,把農民工納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適用范圍;還可以采取專門的立法模式,針對進城農民工制定專門的養老保險法律。但不管采取哪種立法模式,都必須明確政府、企業和農民工的權利義務,讓農民工養老得到法律的保護,讓違法行為得到應有的制裁。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民工養老“幾面都靠,每面都靠不住”的現狀。(據光明網《大眾日報》《上觀新聞》《小康》《農家書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