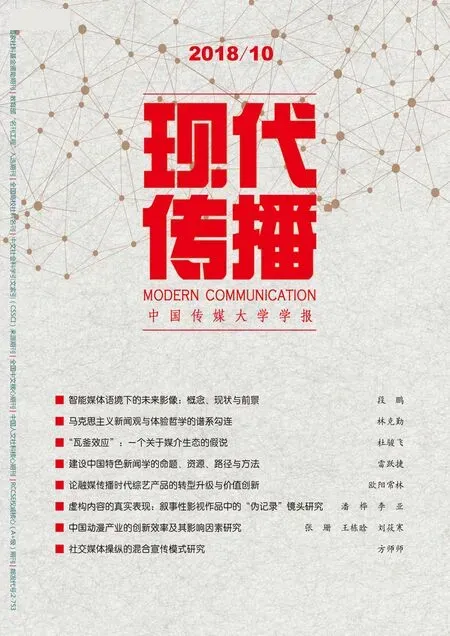“瓦釜效應”:一個關于媒介生態的假說
■ 杜駿飛
關于“瓦釜效應”的觀點,最初作為一篇媒介文化批評,發表于《南方周末》,后經學術期刊《新聞記者》摘編轉載。由此,這個概念進入研究視野。①
“瓦釜效應”現已逐漸成為文化、社會、媒介批評中的常見詞,用以指代新聞市場上形形色色的“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在百度上搜索“瓦釜效應”,有3680個返回;在中國知網,正文中涉及“瓦釜效應”一詞的學術論文也有14篇之多。作為概念的提出者,我樂見它的理論應用;但同時,有感于討論者對“瓦釜效應”的闡發時有分歧,故此,我愿借本文作一個理論性的回應。
一、檸檬市場與瓦釜效應
“瓦釜”一詞,典出《楚辭·卜居》:“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屈原以這些同類意涵的排比,來批判是非顛倒、真偽混淆、輕重倒置的時代政治。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字面含義是指:黃銅鑄的鐘被砸爛拋棄,泥制的鍋卻被敲得很響。兩千多年來,“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已經成為一個成語,在漢語里,人們是以它來比喻:有價值之物被棄置不用,而無價值之物卻登堂入室。
在本題中,我以“瓦釜效應”來闡釋一種逆向的社會文化機制的原理,批評價值觀顛倒的新聞流通。“瓦釜效應”的基本現象是:“在我們今天的大眾傳媒上,更有意義的新聞角色大多默默無聞,更無意義或更有負面意義的新聞角色則易于煊赫一時。黃鐘奈何毀棄,瓦釜居然雷鳴。其間,有‘黃鐘’的原因,有‘瓦釜’的原因,更多的則基于傳媒的時代之病。”①
作為一個理論假設,“瓦釜效應”旨在解釋媒介文化的“崇低”和“向下”何以可能,以及媒介場域中諸主體的合謀是如何實現的。其要義,可表述如下:傳媒與其新聞社群之間,在一定的媒介生態環境下,能夠形成鼓勵低文化價值的新聞市場機制,并通過彼此循環影響,逐漸產生“劣幣驅逐良幣”式的文化后果,導致高價值新聞只能得到傳媒資源與注意力資源的低配置,而低價值新聞卻可以得到傳媒資源與注意力資源的高配置。
在這里,我們從傳統新聞學的視角,定義富有新聞價值、旨趣純正、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新聞為高價值新聞;反之,定義缺乏新聞價值、旨趣低俗、迎合人性弱點的新聞為低價值新聞。自然,我們也可以仿照下文中經濟學對貨幣成色所做的命名,將高價值新聞稱為貴新聞(undebase news),將低價值新聞稱為賤新聞(debased news)。按理,新聞的貴賤,不取決于市場價格,而取決于其內在價值。但事實上,在一個價值理性倒置的新聞市場上,貴新聞反而賣不出好價格,賤新聞的價格倒可能扶搖直上。這是因為,在“劣幣驅逐良幣”的生態下,社會易于忽視新聞的公共產品價值和內在文化效用。我們以“黃鐘”“瓦釜”這樣的修辭,代指新聞報道在社會進步、文化操守維度上的兩極,原因也正在于此。
“劣幣驅逐良幣” (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是經濟界一個古已有之的現象:在鑄幣流通時代,在銀和金同為本位貨幣的情況下,一國要為金幣和銀幣之間規定價值比率,并按照這一比率無限制地自由買賣金銀,金幣和銀幣可以同時流通。由于金和銀本身的價值是變動的,這種金屬貨幣本身價值的變動與兩者兌換比率相對保持不變的規則,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使復本位制無法實現。貴金屬含量較高的“貴錢”(undebase money)漸漸為人們所貯存離開流通市場,使得貴金屬含量較低的“賤錢”(debased money)充斥市場,這一后果無疑是具有諷刺性且違背經濟直覺的,但是,它卻又往往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這一現象最早被英國的財政大臣格雷欣(1533—1603)所發現,故也稱之為“格雷欣法則” (Gresham's Law)。
千百年來,人們早已發現,“格雷欣法則”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現象。事實上,在很多領域,人類群體行為都曾演化至“劣幣驅逐良幣”的后果。例如,乘地鐵時,排隊者總是競爭不過不守次序的人,于是,為了爭得座位或搶得時間,遵守秩序排隊上車的人越來越少。再例如,在一個道德失范的單位里,不擇手段的人,總是更有機會攀升到管理層,安分守己而有道德感的人,則往往沉淪于底層,久而久之,正人君子開始逃離這個社群。同樣,在國際政治、街角社會里,也均有同類過程與后果發生。
形形色色的例證,雖然都暗合“格雷欣法則”所描述的現象,但是在不同領域,“劣幣驅逐良幣”的行動邏輯、約束條件、例外規則,顯然還是不同的。因此,在廣闊的社會科學界,“格雷欣法則”并不是一個可通約的理論,而是一系列屬性不同、但形式近似的社會現象。
在經濟領域中,對這一現象的典范的理論闡釋,來自美國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阿克洛夫(G.A.Akerlof),1970年,他發表的具有開創性意義的論文《檸檬市場:質化的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The Market for 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以二手車市場為范例,推證了“不對稱信息理論”(asymmetrical information theory)對市場運作的影響,并因此而獲得了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不對稱信息理論”指出,在二手車市場,當事人的信息不對稱,是“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存在的基礎,因為,如果交易雙方對貨幣的成色或者真偽都十分了解,劣幣持有者就很難將手中的劣幣用出去;或者,即使能用出去,也只能按照劣幣的“實際”而非“法定”價值與對方進行交易。
同樣是針對“劣幣驅逐良幣”,二手車的“檸檬市場”與新聞的“瓦釜效應”,都是一個基于現象的歸納。從理論來看,“不對稱信息理論”對經濟行為有良好的解釋力,但是,用“二手車市場”所發現的經濟學思想框架,還無法分析擠公車、單位政治中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畢竟,政治、社會現象比單純的買賣行為具有更多的分析變量。“不對稱信息理論”也顯然并不能充分解釋,在一個宏觀的媒介文化場域里,為何會出現新聞內容上“劣幣驅逐良幣”的長期化市場后果。如前所述,在新聞市場中,受到大量內、外因素的影響,“劣幣驅逐良幣”的行動邏輯、約束條件、例外規則,都更為復雜;文化市場的社會心理,也和純粹的經濟行為迥然不同。
以上,正是我們要以“瓦釜效應”來闡釋媒介的反文化景觀的主要原因。簡言之,我對這一理論假設抱有這樣的期待:通過一系列不斷深入的求證,以及不斷開放的集體討論,或許能逐步建構起一些獨特的理論模式,對媒介文化景觀中“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這類逆向選擇機制做出宏觀解釋。
二、媒介生態的循環影響鏈
如果不是在中國文化環境里,我們大概很難說清楚“瓦釜”這個詞匯的文化寓意,以及對“瓦釜效應”字面上的闡釋。但如果我們以說明其內在機制的“循環影響鏈”(circular causal chain)來刻畫其理論模式,則可能會清晰得多。
稱之為“循環影響鏈”,是因為在“瓦釜效應”的社會行動邏輯里,存在著一個多主體“共謀”的機制;如下文所述,塑造這種機制的不同主體也在交互影響,形成一個封閉的循環結構。顯然,這種閉環特性足以建構和維持一個媒介生態,進而形成特定時期的媒介文化景觀。
關于媒介生態(media ecology),以下知識是讀者耳熟能詳的:麥克盧漢在《媒介即訊息:效果一覽》(The Media is the Massage:An Inventory of Effects,1967)一書中,提出媒介生態的概念,以環境作為特定的比喻,來闡釋媒介對文化的生態式影響。不久后,波茲曼(Neil Postman)在其演講中進一步闡釋了媒介生態,并將媒介生態學定義為“媒介作為環境的研究”(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
媒介生態論對于世人理解媒介的宏觀結構至關重要。任何大眾媒體的新聞傳播,不僅僅受市場法則的牽引,還總是受制于特定的制度、政策、法律、歷史和文化范式,以及它們所構成的系統。這種控制并非是時刻顯著的,而更接近于布里德(Warren Breed )在《新聞編輯部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一文中所描述的,是一種潛在的宏觀控制。按照布里德的控制學觀點,任何處于特定社會環境中的傳播媒介,都擔負著社會控制的職能;這類控制往往是一種潛移默化、不易察覺的過程,用一個形象化的詞來概括,可以叫“潛網”。此外,“潛網”對社會、媒體的控制,最終會落實到新聞人身上,新的從業者也最終會變得與老記者一樣循規蹈矩,將自己逐漸融入其中。②
自然,除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控制之網外,媒介自身的技術、市場、商業理念和新聞產品管理,也是媒介生態的組成部分。并且,它們的存在,是媒介權力的主要來源,也是“瓦釜效應”的循環影響鏈上的第一環。事實上,所謂媒介外部因素的控制本身,可以視為媒介權力所激發的反權力;畢竟,在媒介生態的核心地帶——媒介權力中,存在著媒介對國家意識形態、社會大眾思想的塑造之能。
而社會大眾,也并非只是被動的受眾,也是決定市場和資本的力量。社會大眾是媒介生存的市場基石,也對影響媒介的政策環境、資源環境和競爭環境構成間接影響。在談到媒介生態環境時,無論是麥克盧漢還是波茲曼,他們的主要關注點,還是媒介技術對人類文化的影響,并由此闡發技術導向的媒介環境如何塑造了人類生存狀態。但是,如果我們從相反的視角看,一個特定社會的受眾人群,其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和社會組織方式,不也在以文化消費市場潮流決定著資本的立場,進而決定著媒介的理念和趨勢嗎?
媒介確是在建構著社會,但社會也在更有效地建構著媒介。正如有什么樣的公眾就有什么樣的政府,有什么樣的受眾也就有什么樣的媒體。從傳統的學術觀念看,技術、媒介與社會(在這里,是受眾與市場)是媒介生態中三個同等重要的元素,而據我看來,在媒介文化這一具體化的生態系統中,如果將政治視為強有力的外部力量,同時,也將社會史的屬性作為一個文化發生學意義上的歷史性背景,那么媒體、市場、資本、技術、政策和社會傳統,即是媒介文化生態的六個核心要素。

圖1 媒介生態:六要素的結構網模型
如圖1,媒介生態的核心六要素形成了一個“結構網”模型,要素之間也均有相互影響的動力關聯。而在這些核心要素中,有哪一個要素是決定性的呢?我認為,一個決定性的要素,應該是 “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存在的制度性基礎,它通常以媒介政策和媒介管制的方式存在,它也是 “循環影響鏈”得以不被中斷的主因。
張五常曾質疑,“劣幣驅逐良幣”在邏輯上是錯誤的:“在有優、劣金幣的情況下,購物而要付出金幣的當然想使用劣幣。問題是,賣物而收幣的人可不是傻瓜,怎會不見劣幣而敬而遠之?賣物者是愿意收劣幣的,但物品的價格必定要提高,借以補償劣幣之所不值;另一方面,以良幣購物,價格就較便宜。”③張五常的觀點自然是有價值的,不過,“劣幣驅逐良幣”這個“錯誤邏輯”,卻是時常可見的史實;而糾正這個倒錯的事實,則需要時間里的衍變、交易成本的降低:例如,在唐朝時,唐肅宗鑄造“乾元重寶”,到最后開元通寶(良幣)和乾元通寶(劣幣)并存,是一個從信息不完全到信息完全的過程,人們對良幣和劣幣的認識過程也是一個交易費用從很高到逐步降低的過程。開始時也許人們會被欺騙,不能區分劣幣,但是“你不能在所有的時間里欺騙所有的人”,人們最終能夠識破騙局,用劣幣支付價格必定提高。④我們可以想見,在傳媒文化生態中,“瓦釜效應”的運行也絕不可能天長地久,但問題是:需要多久?另外,在得到匡正之前,社會需要付出多少成本?
經濟史學圍繞這一問題的深入討論,給了我們進一步的啟發,崔慧永在討論劣幣驅逐良幣的根源時指出:“法的力量強加于流通,確立起本位幣兌換的固定‘標準’以扭曲金銀自身價值,是劣幣驅逐良幣的深層原因;法的力量由政治權力賦予,因而政治權力通過法對流通施加作用力是劣幣驅逐良幣的根本原因。”⑤
相應地,在新聞市場上,如果純粹按照流通價格來衡定新聞的價值,那么,功利主義的媚俗觀念一定會占據上風,畢竟大眾總是具有人性弱點,而往往,人性是經不住低俗、娛樂的誘導的。如果國家鼓勵新聞機構一概以商業價值(點擊率、發行量、收視率)來要求新聞生產,那么低價值新聞一定會在資本回報率競爭中勝出。事實上,“今日頭條”迎合大眾的新聞算法邏輯能取得空前成功,“內涵段子”之類產品的紅極一時,均得益于商業邏輯對信息服務業(延及新聞業、視聽市場)的宰制;類似于中央電視臺《讀書時間》等一批文化類欄目之死,以及諸多文化精英類媒體的衰亡,在很大程度上,也直接來自這一不良制度框架帶來的致命競爭。
過度的、一概的商業化,還只是新聞市場“瓦釜效應”的起點。在循環影響鏈開始形成后,原本可以阻止其“螺旋化”發展的文化階層,也就是可以批評和抵制低價值新聞產品的人群,無法獲得掌控言論的舞臺和制定文化標準的權力——這有點類似于在前述的“檸檬市場”上,當事人被有意剝奪了信息對稱的機會;與此同時,被視為高價值新聞產品的內容與主題,也不斷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壓制,于是,在幾無競爭的環境下,劣幣驅逐良幣的慣性,終得以長期保持,且愈演愈烈,這才是循環影響鏈能夠循環的關鍵。
因此,作為一個強外部性的行業,一個或一系列的外部因素(如政治、法律、制度及社會事件),才是循環影響鏈的承托之物,也是新聞“瓦釜市場”上的決定性力量;外部因素對社會及媒體的重商業、輕文化、去時政的“潛網”式規制,也是新聞市場上“劣幣驅逐良幣”現象長期存在的制度性基礎。
如果“瓦釜效應”有其內在的“循環影響鏈”,那么,媒體、市場、資本、技術、政策和社會傳統就是這個閉環系統的關鍵聯接點,它們的交互影響,輻射出一系列施加影響的鏈條;它們相互作用,締造了屬于“瓦釜”文化的媒介新聞社群,催生了媒介自身的觀念變異,也制造了眾多以招徠顧客和擊中人性弱點為能事的新聞產品。如果說,新聞業墮入趨利避害的商業邏輯,是“瓦釜效應”的“起因”,政策、制度和社會傳統等強外部性因素是“瓦釜效應”的“主因”,那么,媒體、市場、資本、技術、政策和社會傳統的共謀,就是“瓦釜效應”的“共因”。
凱爾納(Douglas Kellner)曾提出“媒體奇觀”(media spectacle)的概念,“媒體奇觀”是指“能體現當代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引導個人適應現代生活方式,并將當代社會中的沖突和其解決方式戲劇化的媒體文化現象,它包括媒體制造的各種豪華場面、體育比賽、政治事件等。”⑥在他那里,“媒體奇觀”是被媒體放大的事件,其典型主題是商業、體育、犯罪、影視和政治報道。同時,媒體制造的各種豪華場面、體育比賽、政治新聞,也是企業、個人和政府等不同主體以大眾傳媒為渠道制造的一個個聳人聽聞的新聞事件。
“瓦釜效應”與“媒體奇觀”具有相似的社會癥候;但需要商榷的是:站在“瓦釜效應”的邏輯起點上看,那些促發“媒體奇觀”的商業、體育、犯罪、影視和政治報道里,值得批判的到底是什么?其實,并不是它們的題材,而是它們所認同的、來自文化生態的庸眾化旨趣,以及唯利是圖的商業邏輯。正是這些核心的偽文化、非文化,甚至反文化特質,才會導致高價值新聞被不適當壓低流通質量,以及低價值新聞被不適當抬高流通質量,從而產生在宏觀生態上幾乎不可逆的“瓦釜效應”。
阿多爾諾(T.W.Adorno)對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的弊端進行了嚴厲批判。在他看來,“文化工業”的興起,表明文化藝術已納入了市場交換的軌道,交換價值和利潤動機成為了決定性因素。他曾把一味迎合顧客需要的流行音樂,稱之為“音樂拜物教”。⑦實際上,我們又何嘗不能把陷入“瓦釜效應”的新聞業稱之為“新聞拜物教”?這樣的新聞的或傳播的拜物教,不是少數人和單方面的宣講推送,而是所有社會要素的共襄盛舉,摻雜著各傳媒主體在各取所需基礎上的心領神會,以及對趨利避害原則的共同遵行。
因此,有別于“媒體奇觀”中界定不同主體的運行,我想以“循環影響鏈”來強調,不管是(媚俗意義上的)“媒體奇觀”,還是未能達成 “奇觀”的低價值新聞,它們都已匯成了促使新聞市場日益娛樂化、膚淺化、功利化的力量;這個擴散著“瓦釜效應”、不斷螺旋向下、直至實現自我主流化的媒介生態過程,正是媒體、受眾、市場、技術、政策和社會合謀的結局。
三、內在邏輯與交替影響
觀察“瓦釜效應”的運行,我們會看到,“循環影響鏈”的聯接點之間,既是彼此交叉的,也是相互影響的,更是環環相連、首尾相接的。它們彼此選擇、共同推動 “瓦釜”走向主流,其主要惡果,還不在于媒介景觀、新聞市場的畸形,而在于媒體、市場、資本、技術、政策和社會傳統逐漸凝聚而成一個逆向的非文化共同體。在這個“瓦釜俱樂部”里,“瓦釜效應”得以建制化,并使得新聞市場主流難以逆轉、媒介文化凈化少有可能。
具體來說,媒體、市場、資本、技術、政策和社會傳統合力形成“瓦釜效應”,需要一個顯要的邏輯起點,如前所述,這個起點就是商業邏輯里的“趨利避害”。但維持“瓦釜效應”的生態,則需要更強、更系統、并且是內生性的邏輯結構,還需要彼此相洽的驅動力,以及不斷繼起的生態接力過程。就我觀察而言,這些進程與交替影響有五:
1.進程一:媒體迎合
大眾媒體受“第三人效果”的影響,傾向于為受眾提供負面新聞;出于自身的政治本能,媒體回避嚴肅新聞的題材風險;為追逐新聞的關注度,媒體愿意為市場提供缺乏嚴肅意義、但能迎合注意力的低價值新聞。
“第三人效果假說”的創建者戴維森(W.P.Davison)指出:“受眾傾向于過高估計大眾傳媒傳播的信息對其他人在態度與行為上的影響,也即:每個接觸到勸服傳播信息(無論此信息是否具有勸服意圖)的受眾,將會預期此勸服信息對其他受眾的影響,大于此信息對自己的影響。換言之,絕大多數的人會傾向低估大眾媒介對自己的影響力,或高估大眾媒介對別人的影響力。”⑧這里,一個主體對媒介影響他人的預期無疑將會導致自己采取行動。同時,從心理上來說,負面信息往往比正面信息更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因此,集中在負面信息上的“第三人效果”驗證,也成為了該理論的主要成果。在一項本土性的研究報告中,張國良等指出:“我們發現,訪談對象的大多數(73%)認為,自己周圍的人更關注負面信息(中立6%,正面21%)。”⑨
事實上,所謂負面信息的社會心理優勢,本有可能將新聞報道轉向新聞的社會監督和媒體的政治瞭望功能,但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回避嚴肅新聞題材風險的本能,戰勝了新聞生產者對發布這一部分負面信息的“成名想象”,于是,寄予著“第三人效果”期待的負面信息,大部分轉向了無涉政治、深耕商業的負面,例如娛樂新聞、謠言新聞、八卦新聞等軟性題材。對于這些低文化價值的新聞產品,新聞生產者未必自己有興趣,但他們會傾向于認為,受眾對它們的興趣更大。于是,基于日趨激烈的媒體競爭,在普遍功利主義導向下,為低價值新聞配置高媒體資源,成為媒體經營的通衢大道。這一步,其實也是“瓦釜效應”的原初驅動。
一方面,大眾媒體對“循環影響鏈”的發動,是由于商業化大眾媒體的倫理均值較低,對市場欲望缺乏免疫力,對外部壓力缺少承受力。另一方面,大眾媒體首先啟動了“循環影響鏈”,究其本質,還是外部因素的壓力大到媒體足以放棄原教旨的新聞價值觀,足以將自身的知識分子行業屬性轉為文化工業。有了這些因素作為第一驅動力,“瓦釜效應”的其他進程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2.進程二:市場認同
大眾媒體對低價值新聞的高資源配置,使受眾的低價值新聞消費擁有了正當性;同時,特定的低價值新聞社群(圍繞娛樂、八卦、謠言、隱私、掐架等新聞主題所建構的受眾圈層)的壯大,也強化了低價值新聞消費人群的內在認同性。整個媒介市場由內到外,被低價值新聞所建構,形成相當程度的一致性。
3.進程三:資本驅動
受眾對低價值新聞的消費升溫,使媒體從市場利益上得到了正向反饋。受此激勵,資本必然會驅動媒體增強“瓦釜化”的量級,從生產、流通、人力資源等各環節尋求對低價值新聞作更高的資源配置,以期獲得更高的利益。純商業化的互聯網信息服務業,由于資本力量占據絕對優勢,其驅動力之強則更會異乎尋常。
4.進程四:技術強化
媒體的終端資源(包括版面空間、議題與框架)畢竟是一個有限度的常數,同時,在媒介競爭、媒體競爭不斷加劇的條件下,受眾的注意力也日漸成為短缺資源。由此,低價值新聞市場與高價值新聞市場成為零和博弈,也因此,占據上風的低價值新聞開始左右傳媒生態。
到這一進程時,實際上媒體、受眾、市場和資本的力量都開始站在低價值新聞一邊,“瓦釜效應”也已初步形成。一旦外部因素傾向于制約嚴肅新聞、忽略娛樂新聞,將使得“循環影響鏈”上的每一環節都在“瓦釜”方向上得以強化,直至主流化。
與此同時,這個時代的媒介技術發展潮流,也加重了娛樂、低俗新聞的權重。因為在移動互聯時代,受眾的選擇權變大,在觀念、興趣和立場上的自我強化的趨勢日漸明顯,而社會統計學意義上的“大數法則”(在樣本數量極大的條件下,樣本均值和真實均值充分接近)亦已開始呈現。“算法至上”時代的來臨,也加重了新聞民粹化的趨向,新聞更加倒向迎合大眾、迎合市場、迎合不良趣味的操作范式。這也是為什么——在自媒體時代,媒介文化的主體并沒有擺脫“瓦釜”主流的控制、更未能超越“瓦釜效應”,相反,從線下粉絲群、微博、微信、貼吧、QQ群到自媒體的文化環境里,“瓦釜市場”都得到了更多的鞏固,“瓦釜人群”都得到了更多的認同。這也是為什么在大數據、云服務、人工智能時代,工具理性依然能夠壓倒價值理性,市場法則依然能夠壓倒道德律令。而其結果則是,“瓦釜效應”在新舊媒體的不同場域內都得到了更強的呈現和集聚。
5.進程五:社會斷裂
最后,最壞的消息則是社會在文化意義上的崩潰,社會傳統中原本可以制衡“瓦釜效應”的文化產品,因為高價值新聞與低價值新聞在市場和資源上的此消彼長,逐步因“馬太效應”而變得“弱者恒弱”;同時,高價值新聞人群為了保持認同的區隔,日漸退出主流新聞市場,他們當中包括專業新聞人、屬于“嚴肅新聞”的新聞受眾,還有廣義的知識分子階層。社會的斷裂、分化乃至兩極化,有力地促使“瓦釜效應”成為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四、瓦釜效應的動力模型
文化進程相繼發生,生態要素交替影響,在文化資源反向配置現象得到強化后,媒體、市場、資本、技術、政策和社會等六個核心要素,在政策允準的環境下,也已完成了對媒介文化生態的合圍;此時,交替影響如果產生循環的動力機制,“瓦釜效應”將逐步趨向于建制化。
在本文的兩個圖式中,圖1為抽象意義上的六要素基礎模型,我假設其要素結構可以解釋媒介文化生態發生的普遍機制。圖2則可視為圖1的理論場景驗證,它以“循環影響鏈”的發生機制的闡釋,為“瓦釜效應”做出了一個具體的動力學說明。

圖2 瓦釜效應:“循環影響鏈”模型
“循環影響鏈”的主旨是:在媒介文化生態的諸影響鏈里,每一個鏈條都連接著兩個以上的生態“進程”,這些進程就是要素(如“資本”)得以對“瓦釜效應”發生效用(如“驅動”)的過程。同時,這些文化進程的實現,也基于其內在因子的相互運行——我們在此稱之為生態“線程”。
按計算機學的程序術語來說,進程(process)是一個應用程序在處理機上的一次執行過程,它是一個動態概念;一個進程中,往往還包含多個線程(threads)在運行,線程之間獨立運行,但是它們彼此共享虛擬空間,也是真正的執行單元。
在圖2中,我是把媒介文化生態的動力機制視為一個總體的社會計算(在本文主旨里,則是“瓦釜效應”的發生),把媒體、市場、資本、技術、政策和社會傳統這些要素效用的產生,理解為一個個應用程序在這個社會處理機上的執行過程。一個要素效用與下一個要素效用之間,類似于程序繼起的上下文關系,它們是這個社會計算的進程間通信,故此我將其稱為影響鏈。“瓦釜效應”的動力機制,基本上可以用這個起承有序的總體關系來闡釋。
而從進程應依托于線程的計算邏輯來看,“瓦釜效應”真正的奧秘,應該是每一個要素發生效用的內在因子之間的關聯,以及一個要素與其他所有要素之間的多元博弈——以程序語言來說,在“瓦釜效應”這一社會計算的循環往復的諸級進程那里,每一個復雜的生態進程內均蘊含多個生態線程——例如,在“社會斷裂”這一進程內,存在著各社會因子(階層、群體)的持續互動,以及它們與政策、市場、資本諸要素內各類因子的全面關聯,在六要素結構內的博弈充滿著“潛網”式的規制力和影響力,也是六要素發揮效用、形成文化生態“進程”的真正驅動力。
需要說明的是,社會發生學的系統絕非線性而機械的技術圖譜,這里,以社會動力為計算程序所形成的模型,只能視為媒介文化生態研究的認知輔助。對社會文化宏觀系統的高信度描述,仍有賴于對一系列具體問題(尤其是一組組要素及因子間的關系)的定性研究;同時,對這一六要素基礎模式,如試圖作具體的程序書寫和權重計算,顯然還有待于進一步的實驗驗證。
綜上所述,我們總結一下“瓦釜效應”的思想體系,如下:
(1)媒介文化六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形成媒介生態的影響鏈。每一個鏈條連接著不同要素,不同要素產生不同的功能效用,由此形成不同的“進程”。
(2)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及特定的發展時期,不同生態進程及其要素效能,各有權重差別。在“瓦釜效應”的模型中,媒介的趨利避害和價值觀異化成為“起因”,政策要素因為具有核心的支配地位,而成為約束條件和激發系統的“主因”,而參與共謀的其他因素,則相繼成為媒介生態瓦釜化的“共因”。
(3)在邏輯上,媒介文化生態的進程應該是不斷有序繼起、產生交替影響的,但是,在諸要素內各文化生態因子之間存在復雜博弈,這些具體的生態“線程”可以是同時、或錯雜運行的,可能是資源共享、或互不可見的。在“瓦釜效應”的生態中,諸要素內外,均以復雜的運行“線程”博弈“利、害”關系,并最終就媚俗和 “崇低”這一“次優解”形成了默契。
(4)從生態線程到生態進程,再到進程間的影響鏈,媒體文化生態諸要素能形成合力,并建立正反饋式的循環,拼接為自我強化的影響鏈。在本題中,則是生態系統上發生了建制化的“瓦釜效應”。
(5)如無內在擾動,這一瓦釜化歷程將會持續下去——直到媒介開始反思生態“起因”,并且,支配環境的公共政策開始變革生態“主因”。變革發生后,經過復雜的社會互動,以及漫長的自我凈化,傳媒文化生態或能告別“瓦釜效應”,恢復具有價值理性的新聞市場,重返信息傳播的健康有序。
以上,是我對“瓦釜效應”這一理論假說的基本陳述。
注釋:
① 杜駿飛:《大眾傳媒的瓦釜時代》,《南方周末》,2007年5月10日,第D27版;杜駿飛:《“中國第一博”案的媒介社會行為分析》,《新聞記者》,2007年第9期。
② W.Breed.SocialControlintheNewsroom:AFunctionalAnalysis.Social Forces,vol.33,Issue 4,1955.pp.326-335.
③ 張五常:《荒謬的“定律”》,《經濟學消息報》,2004年3月12日。
④ 李俊慧:《“劣幣驅逐良幣”的神話——從唐肅宗的“乾元重寶”史實說起》,《經濟學家茶座》第30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
⑤ 崔慧永:《論劣幣驅逐良幣的根源》,《商業經濟》,2016年第9期。
⑥ [美]道格拉斯·凱爾納:《媒體奇觀:當代美國社會文化透視》,史安斌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
⑦ [德]阿多爾諾:《論爵士樂》,轉引自歐力同等,《法蘭克福學派研究》,重慶出版社1990版,第287頁。
⑧ W.P.Davison.TheThird-personEffectinCommunicat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47,Issue 1,1983.pp.1-15.
⑨ 張國良、廖圣清:《中國受眾的信息需求與滿足》,《新聞記者》,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