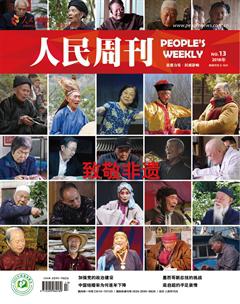個稅修法考驗征管水平
王純
近日,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提請人大常委會審議,并在7月底之前向社會公示一個月,公開征求各方意見。這是個稅法自1980年出臺以來的第七次大修,將迎來一次重要變化。
這次個稅法修改涉及的民眾關注點較多,令人期待。比如:個稅起征點由每月3500元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萬元);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和特許權使用費等四項勞動性所得首次實行綜合征稅;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繼續教育支出、大病醫療支出、住房貸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專項附加扣除;優化調整稅率結構,擴大較低檔稅率級距等。此外,為堵塞稅收漏洞,個稅法修正草案擬首次增加反避稅條款,針對個人不按獨立交易原則轉讓財產、在境外避稅地避稅、實施不合理商業安排獲取不當稅收利益等避稅行為,賦予稅務機關按合理方法進行納稅調整的權力。
稅制設計,關鍵在可操作
中國稅務學術委員會研究部召集人、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研究員涂龍力說,修改個稅法已經呼吁多年,修改草案綜合考慮了社會變遷、立法創新、民意訴求等諸多方面。“可能多數老百姓首先關注到的是個稅起征點的提升,其實個稅改革另外一個主要的內容是簡化稅制,十九大確定的稅制改革定位是簡化稅制,個稅的綜合征收正是簡化稅制的一個體現。調節高收入、擴大中收入、扶植低收入是原則,征管是關鍵,畢竟再好的稅制設計也要可操作。”
從國際慣例看,一般將個人所得稅納稅人分為居民個人和非居民個人兩類,兩類納稅人在納稅義務和征稅方式上均有所區別。現行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的兩類納稅人實質上是居民個人和非居民個人,但沒有明確作出概念上的分類。為適應個人所得稅改革對兩類納稅人在征稅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要求,便于稅法和有關稅收協定的貫徹執行,草案借鑒國際慣例,明確引入了居民個人和非居民個人的概念,并將在中國境內居住的時間這一判定居民個人和非居民個人的標準,由現行的是否滿1年調整為是否滿183天。
現行個人所得稅法采用分類征稅方式,將應稅所得分為11類,實行不同征稅辦法。按照“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的要求,結合當前征管能力和配套條件等實際情況,草案將四項勞動性綜合所得納入綜合征稅范圍,適用統一的超額累進稅率,居民個人按年合并計算個人所得稅,非居民個人按月或者按次分項計算個人所得稅。
“綜合征收的一大難點就是征管。”涂龍力說,過去個稅是按月征收,現在是在參照月收入的基礎上核算出一個月征收數,然后年終算總賬一并扣除,按照年收入6萬的起點來征收,拉長了時間跨度。專項抵扣的實施,要求個人向稅務部門申報教育支出、房貸利息或房租信息的同時,幼兒園、學校、銀行、房主等相關機構或個人也須申報相應信息,以保證信息的真實性。另外,對于工作不在一地或者收入來自異地的納稅人來說,如何申報、在哪里申報這也是問題。以上個稅草案的種種變化,在實踐操作的精細化方面將給稅收征管帶來相當大的挑戰。
個稅修改契合民意
個稅起征點自2011年調至3500元后,至今已時隔7年,此次上調至5000元為歷史最高點。個稅改革此前呼吁多年沒有實施,主要原因之一是技術條件還不成熟,比如稅務部門需要與其他部門共享相關信息,掌握納稅人收入及家庭支出情況,以便于實施綜合征稅、專項附加扣除等。
草案的個稅起征標準綜合考慮了人民群眾消費支出水平增長等各方面因素,并體現了一定前瞻性。按此標準并結合稅率結構調整測算,取得工資、薪金等綜合所得的納稅人,總體上稅負都有不同程度下降,特別是中等以下收入群體稅負下降明顯,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強消費能力。
涂龍力稱,四項勞動性所得實行綜合征稅,既減輕了納稅人稅負,也減輕了征稅成本,稅制改革就應當是一個由“減稅”政策到“簡化稅制”的過程,或曰通過“簡稅”達到“減稅”。
按照年收入來收取個稅更有利于對多渠道收入以及高收入人群的征管。前一段時間明星“大小合同”獲天價片酬在網絡上炒得沸沸揚揚,更多的人只是追逐“熱鬧”而去,鮮有人從正面挖掘產生現象的本質及教訓。雖然此事目前相關部門仍在調查,尚待結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小合同”并不是個案,演藝圈的行業潛規則由來已久,只是明星效應才得以迅速引來眾人“圍觀”。
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拓寬居民勞動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渠道。”那么,如何才能得以較好地落實?
“按中國經濟現狀,個稅收入應該成為中國第二大稅種。相信國稅地稅合并之后,個稅流失問題將得到有效遏止。”中國稅務學會學委會副秘書長焦瑞進說,當下大家關注“大小合同”與“偷逃稅”,但實際上所得稅與合同并沒有直接關系,不管有沒有合同,發生實質交易并取得所得都必須依法繳稅。雖說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簽了合同最終交易卻未成的事例,但合同首先應當合法、真實,在涉稅官司中,合同作為交易的前奏和可能,可以作為旁證或線索。
中國稅收教育研究會常務理事潘明星說,合同長期以來被作為一個源泉征收依據,“大小合同”的存在本身就是違法的,支付單位和扣繳義務人需要負相關法律責任,如果涉案金額達到一定標準,還可能承擔刑事責任。
大數據技術當為個稅征管護航
實質交易支付是個人所得稅義務產生的必要條件,那為什么稅收征管不采取措施加強征管,而眼看著“大小合同”偷逃稅呢?這主要是稅法規定與征管措施手段和基礎條件不銜接。
“合同涉及簽約方和稅收關系,它除了要符合相關法定原則,區塊鏈或許能夠在技術手段方面提供監管方案。合同簽約涉及商務多方,簽約內容是否違法涉及工商,這么,可以運用區塊鏈技術將多種因素共同編碼,并應共享信息向全社會公布。經由區塊鏈,合同涉及的相關業務又怎能逃避稅源鏈條監管形成偷逃稅呢?所以說,區塊鏈技術將在稅收管理領域大有用武之地,完善法治加上區塊鏈技術密切配合,將有望根治隱性收入偷逃稅的現象。”焦瑞進說。
涂龍力認為,個稅改革應當破解二大瓶頸:一是“良法”,即實體制度設計,改了這么多年,但一直未成系統,頭痛醫頭,政策替代系統改革。二是“善治”。即程序制度設計,不解決信息源頭管稅的問題,即使是“良法”也難“善治”。
從上世紀90年代啟動的個稅改革以來,一直都未能納入“簡稅制”“強征管”“社會共治”的軌道,不解此扣,“大小合同”及明星偷逃漏稅則無解。“大數據等現代技術的運用是簡化稅制、真正實現信息管稅的充分、必要條件,是優化稅收環境和深化稅收放、管、服的前提。”
“20年前我出去講課,講課費通常放在信封里就給我了,后來需要我簽字,再后來還需要留下身份證號碼,現在300元的稿費也必須要通過銀行轉賬給我。這恰恰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個稅監管正在逐步完善。”潘明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