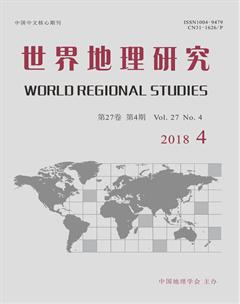統一后原東德城市收縮現象及機制研究
鄧嘉怡 李郇
摘 要:20世紀90年代,收縮城市開始從歐美發達國家蔓延至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其中以統一后的德國東部城市最為典型。統一后原東德收縮城市的案例表明,城市收縮引發的人口流失與經濟衰退現象,主要表現為企業大量倒閉,勞動力市場萎縮,人口總量及出生率急速下降以及城市失業率飆升等;而兩德統一帶來的體制變化是導致原東德城市收縮的主要原因,此外,人口流動、過激私有化、郊區化和過度補貼等一系列反應進一步加劇了城市的收縮;本文最后對統一后,在華盛頓共識的影響下原東德地區采取的斷崖式改革所引起的城市變化進行了探討和反思。
關鍵詞:城市收縮;原東德;體制變化;城市化;私有化
中圖分類號:K901.8 文獻標識碼:A
20世紀50年代起,在去工業化與全球化的背景下,歐美發達國家的很多城市都面臨發展衰退的問題。國外相關學者對此高度重視,并將此現象總結為“城市收縮”。這些城市一方面經歷了較大地域范圍內大量的人口流失,另一方面也存在經濟轉型帶來的結構性危機[1]。“收縮城市”的概念最早在德國被提出[2],而后不少學者對其進行了量化。收縮城市國際研究網絡(SCIRN)將其定義為,人口數量在一萬人以上的人口密集區,至少兩年以上在大區域內面臨人口流失,同時正在經歷經濟轉型以及結構性的危機[3]。美國學者Schilling則認為,收縮城市是過去40年間人口流失超過25%的城市,并伴隨著城市中空置與廢棄的住宅、商業與工業建筑的不斷增加[4]。
直至90年代初,全球已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大都市經歷過或正在經歷收縮[5]。在后社會主義以及后福特主義轉型的相互影響下,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城市也開始逐漸走向收縮[6],其中以統一后的原東德最為典型。統一為原東德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東西部城市發展出現巨大的差異。1991年,原東德的GDP僅為西德的1/8,勞動生產率也僅為西德的40%,科技水平更是比西德落后10至15年的水平[7]。此外,伴隨封閉屏障的解除,大量居民從東德涌入西德,原東德的失業率與房屋空置率不斷提高[8]。對原東德而言,統一帶來的體制變化對城市發展究竟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城市發展的衰退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城市收縮背后的機制怎樣?當地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應對收縮?本文將結合數據分析,探索原東德城市收縮的現象與機制,并期望為中國正在或將要面臨收縮的城市發展提供經驗參考。
1 體制變化下的城市收縮
目前,城市收縮現象在全世界不斷蔓延。數據顯示,有13%的美國城市區域以及54%的歐洲城市區域正在經歷人口的收縮[9]。美國的城市收縮可以被看作是標準化后工業轉型的結果,制造業的衰落是其導火索,城市出現“空洞化”發展[10]。相比之下,歐洲城市收縮的導火索則是城市人口總量的下降,空置、遺棄的建筑與正在使用的建筑高度混合,城市空間呈現“穿孔式”發展[11]。導致城市走向收縮的動因大致可歸納為人口、環境、經濟、空間以及體制變化等五大層面[12]。
20世紀90年代初,體制變化帶來的城市收縮主要發生在蘇東前社會主義國家[13]。在歐盟東擴后,這些國家在短期內,伴隨產品和勞動力競爭壓力的加大,城市發展面臨顯著的調整壓力[14]。而對原東德城市而言,國家統一意味著東、西德政治邊界的完全消失,東部城市不得不面臨來自原西德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的沖擊。在此背景下,華盛頓共識的出現導致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盛行,原東德地區的大量國有企業被迫私有化,并加入自由貿易市場的競爭體系中。原東德的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產業發展與就業環境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直到1994年底,原東德共有14萬的國有企業被重組,GDP僅在一年間就下降了將近30%[15]。原東德產業發展受到了來自西德以及東歐其他國家的雙重競爭壓力,原有的優勢制造業日漸衰落,城市失業率急劇飆升。統一后,僅僅在四年時間內,250萬的就業崗位從德國東部流失。此外,自由市場的開放使得郊區獨戶住宅的建設得以落實,進一步加劇了原東德的郊區化。伴隨著人口的不斷外遷,內城空置現象日益加劇。
另一方面,統一后柏林墻的倒塌使得大量勞動力以及技術人才從東部流向西部,原東德地區的人口總量急速下降,出生率隨之下滑,人口老齡化趨勢日益明顯[7]。面對統一后城市人口與經濟發生的巨大變化,原東德地方政府并沒有采取及時的補救措施,反而將大量的補貼資金運用于低效的城市建設中。城市大量無利可圖的生產受到了來自政府的大力扶持,聯邦政府對非自愿臨時失業以及虧損企業進行補貼,仍然無法阻止原東德城市失業率的持續飆升[16]。因此,體制變化為原東德城市帶來了一系列的變化,同時也導致城市面臨經濟發展衰退、人口規模減小以及社會發展停滯等問題。
2 原東德城市收縮的表現
2.1 經濟發展水平與西德相比差距顯著
統一后,原東西德在經濟層面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國內生產總值、土地價格以及進出口貿易三方面。1991年德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為28536億馬克,其中原東德僅占7.22%,而原西德的占比則高達92.78%,兩者存在巨大差距[17]。原東德經濟在1990至1991年期間急速下滑,GDP水平下降了將近30%,1991年工業生產總量甚至不及1989年的50%[10]。此后,原東德的經濟發展有所回暖。至2014年,原東德GDP占比已升至12.5%,東西經濟差距仍然顯著。
其次,統一后原東德的土地價值與原西德相比,處于劣勢地位,具體表現為可建設用地土地價格的巨大差距。1991年,西德各州的土地價格均高于每平方米25歐,而原東德則普遍低于每平方米12.5歐。貿易方面,1991年原東德的進出口貿易額總計18657百萬歐,原西德則高達607125百萬歐,是東德地區的三十余倍。1991至2001年期間,原東德的土地價格穩步攀升,貿易水平有所提高,然而與西德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圖1)。
2.2 人口總量急劇下降,衰減趨勢延續至今
統一后,原東西德的人口差異主要體現在人口總量與密度、出生率與死亡率以及人口結構等方面。1991年,德國人口總量達到8025.7萬人,其中原東德占19.7%,而原西德占比則高達80.3%。2014年,東西德人口差距進一步擴大,分別占17.5%與82.5%。
1991年至2001年期間原東西德人口密度的變化差異十分顯著。原西德人口密度的年均增長率普遍為正值,大部分地區超過0.6%,而原東德城市則普遍呈現負增長(圖2)。1991年,薩克森州的人口密度基本可以達到原西德城市的平均水平,但在此后的十年間,人口密度的年均增長率卻低至-0.69%,與西德城市呈現相反的變化趨勢。
此外,統一后原東德的出生率低于西德,死亡率卻比西德高。1991年,原東德各州的出生率普遍維持在7‰的水平,西德各州的出生率則大都高于10‰。1991至2001年間,原東德的人口自然增長量持續呈現負值,并在1993年達到了最低峰;而西德各州的人口則普遍呈現正增長,僅在1995年出現了短暫且少量的下滑。此外,1989年以后,原東德地區登記結婚的數量急劇下滑,到1992年,結婚人數僅為1989年總數的37%。而在20世紀80年代期間,原東德的結婚率一直高于西德,到1992年卻比不上西德的一半高[18]。
人口結構方面,原東西德呈現相似的形態,均處于從穩定型到縮減型的過渡階段,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圖3)。兩者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原西德各個年齡段的人口數量均占有明顯優勢,其峰值出現在25-30歲以及50-55歲,中青年基數較大。而原東德的人口年齡結構則較為勻稱,起伏較小,最為突出的峰值出現在50-55歲,適齡勞動人口相對較少。
2.3 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原東德失業情況卻持續惡化
統一后,原東西德在物質層面存在一定的社會差異,具體表現在工資與薪金、失業率以及住房三方面。1991年,原東德每周工作時長為40.7小時,對應的平均收入為217歐元。而原西德工作時長為39.3小時,收入卻高達432歐元。可見,原東西德的工作待遇差異明顯。至2001年,兩者的收入差距雖不斷縮小,但仍十分顯著。
此外,1989年原東德的就業人數高達980萬人,五年后卻縮減至620萬人,并且這種嚴重的失業情況仍在持續惡化中。1991至1992年間,原東德的失業率從原來的10.3%飆升至14.8%,雖然在1995年出現短暫下降,但很快又恢復快速增長。至1995年2月,原東德登記的失業人數已高達110萬人。如果加上提前退休、改行培訓、進修和安排臨時工作等隱性失業,失業人數高達150萬余人,失業率升至35%,這意味著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失業或隱性失業[19]。與之相比,原西德失業率的變化則較為平緩。
3 原東德城市收縮的原因
統一后,原東德的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自由市場轉換,伴隨貨幣、政策等發展條件的變化,原東德的經濟結構土崩瓦解,人口總量急劇下降。對大部分東德城市而言,收縮現象具備一定的歷史根源,而體制變化是導致城市發生收縮的根本原因,具體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3.1 人口流動
早在二戰期間,原東德城市化水平就已很高,有超過70%的人居住在城市中。在這一時期,為了保障區域的糧食儲備以及農業生產,強勢的東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農村向城市的移民。盡管如此,日漸下降的出生率并不能補償城市化導致的農村人口損失。1971至1980年間,原東德的農村人口數量下降了11%[20]。德國城市化的特點之一就是數量眾多的小城鎮。然而大部分的工作機會和發展投資都集中于大中型城市,小城鎮向大中城市的移民成為主流。早在統一前,城市化驅動下的人口流動以及老齡化問題就已經在原東德的部分地區出現端倪。伴隨柏林墻的倒塌,原東西德居民出入的限制被打破,大量人口從東部涌入西部。1990至1999年間,原東德超過10萬人的大城市流失了將近16%的居民[21]。全德國范圍內,人口流入的中心集中在下薩克森州以及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圖5)。兩個中心的人口流入主要來自東部城市。原東德各州均有不同程度的人口外遷,其中薩克森州以及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的人口輸出量相對較大。
3.2 經濟體制轉變
1989年,位于華盛頓的三大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政府,針對拉美和東歐轉軌國家,提出一套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被稱為“華盛頓共識”[22]。該理論主張以市場經濟為導向,減少政府干預,并促進貿易和金融自由化,先前由國家運營或管理的部門必須移交到私人領域并進行松綁。
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統一后的東德地區,走向了國有企業全面私有化的道路。前東德原有的大型國有工業企業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中并沒有受到政府部門的保護。1990年6月,德國政府建立了一個信托機構——托管局,主要負責將原東德的資本進行私有化處理。托管局的主要任務是控制并執行中央計劃資產的私有化,同時對城市衰退的工業以及房地產業進行販賣。直至1994年年底,托管局處理了約14000間公司,僅僅四年時間,原東德就失去了250萬個工作崗位[23]。與此同時,原有大型國有企業的活動被一系列小企業接管,實現資產的分拆。這些接管企業的規模普遍比西部地區的企業小,其進軍國際市場的機會也就相對較少,從而使得原東德經濟的發展錯失了不少良機。工業資產激進的私有化過程進一步加劇了城市的去工業化,為原東德帶來了致命的打擊。
此外,隨著自由貿易的開放,東德城市逐步融入區域貿易一體化的過程中。城市居民不僅可以自由無阻地進入西部地區,還可以選擇購買由原西德貿易商提供的商品,這導致來自原東德以及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商品需求急速下降。面對自由市場中的競爭體制,與西部地區高質量的商品生產以及部分東歐國家提供的廉價商品相比,原東德的制造業在國際貿易中失去了競爭性[24]。隨著國有資產的逐步私有化,城市往日繁華的工業每況愈下,商品生產受阻,大量工廠倒閉,失業人口顯著上升,經濟呈現萎縮,就業結構也出現供需失衡。原東德城市在經歷快速去工業化的同時,沒有脫穎而出的優勢產業能夠替代原有的制造業,經濟發展對政府的依賴程度非常大。1990年,在東德城市萊比錫的就業結構中,加工制造業依然占據第一的位置,但是與鼎盛時期相比,已有明顯地減少。與此同時,政府部門與社會保障部門的就業人口占比非常突出,達到24.02%[25]。
3.3 過度補貼
統一后,原西德政府將城市建設的重心集中在社會、經濟結構優化及產業轉型上。而原東德政府則是更多地把資源與精力聚焦于城市的建設與發展中,希望能在短時間內趕上西部地區的發展水平。在這一時期,原東德城市的發展不僅受到了當地政府部門的全面支持,還得到來自聯邦政府及州政府的項目支撐(表1)。這些城市的重組項目大多依靠政府、私企與民眾的共同努力,重組城市結構,吸引投資,旨在擴大城市的發展規模[26]。
來自西部的大量資金向原東德地區集聚。1990年推出的“奧地利”計劃最初的預算為945億歐元,計劃用于資助城市再生、危險廢物場地以及工業中心的重建。不久后,項目又繼續為原東德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640億歐元的額外資金,用于建設新的道路和鐵軌。此外,東部城市還受到了來自歐盟的財政援助。在此背景下,東德政府將城市發展的目標定位于提供充足的住房和零售基礎設施。大量的援助資金使得政府對城市未來經濟和人口發展的預期過于樂觀,政府為所有愿意在城區內進行投資的商人提供便利,房屋建設如火如荼。1989至1992年間,東德城市萊比錫的住房共增加了1330套,住房數量的增加與人口的下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除住房空間呈現擴張的趨勢外,城市零售產業面積同樣逐年遞增。1989年,萊比錫共建造了82.2萬平方米的零售空間,其中48%位于內城,52%位于城市邊緣[27]。面對統一后人口與經濟的急速下滑,原東德地方政府沒有過多地考慮如何挽留人才以及實現人口回流等問題,而是一味地進行住房以及產業空間的建設。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落后于住房、廠房面積增長的速度,與此同時,城市就業崗位缺失的問題沒有得到實質性的解決,人口回流的拉力難以形成。政策引導的失誤加劇了原東德城市的收縮現象,進一步導致城市經濟、社會的萎縮。
3.4 郊區化
統一前,原東德城市空間發展具備一定的特殊性,其中主要體現在住房上。一方面,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導致城市住房短缺,城市不斷向外拓展,尋求邊緣的低價土地進行住房建設。1975至1990年間,東德地區萊比錫的城市范圍從34%增長到38.6%,而德累斯頓從32.1%增長到34.7%[16]。另一方面,原東德城市的中心區仍保留著大量1945年以前的住房。住房固有存量基數大且增量仍在不斷升高,與此同時,部分區域的人口數量開始減少,兩者共同導致了80年代初住房盈余現象的出現。早在1990年以前,空地塊、空住房以及廢棄建筑就已經成為東德城市常見的景象。
此外,在統一前的社會主義體制下,東德城市大量建設集體住房,獨戶住宅的建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制約。1967年,東德的獨戶住宅數量僅僅占住房總數的1%,反觀同期的西德,獨戶住宅比例已高達47%[28]。伴隨著東德人民對獨戶住宅需求的日漸增長,且統一為原東德地區帶來大量的財政與資金支持,獨戶住宅的建設得到了落實與推進,城市邊緣快速發展。這一時期,原東德城市呈現的郊區化實際上不再是由城市中心的擴張以及郊區人口的流入導致的,反而更像是一個人工制造的過程,伴隨著稅收的減少以及直接或間接的補助性資本投入而產生。這一時期,郊區化的發展不僅僅局限于住房和工業投資,還包括許多大型購物設施的建設[29]。郊區化的過程進一步加劇了城市內城的空置現象。
4 原東德城市收縮的應對措施
面對統一后經濟與人口的持續衰退,原東德政府在產業、空間以及基礎設施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應對收縮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措施以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策略為主,同時,也涉及部分自下而上的公眾參與。下文將以原東德的萊比錫及科特布斯兩座城市作為具體案例,展開詳細介紹。
4.1 萊比錫
在原東德的收縮城市中,以萊比錫最為典型。統一后伴隨大量人口的流失,萊比錫成為德國東部地區房屋空置率最高的城市[27]。然而,當地政府采取積極的措施應對城市收縮,在基礎設施建設、空間修復及產業發展等方面付出諸多努力,最終重塑城市活力。
一方面,當地政府重新擬定住房及空間規劃政策,不再盲目地向城市邊緣拓展,而是將重點放在穩定當前人口和調整住房面積上[16]。借助聯邦政府項目提供的資金,對適宜居住的房屋進行翻新和維護,對廢棄房屋進行拆遷并重建大量的城市綠地及公共空間,實現城市空間的優化[30]。另一方面,提供充足的住房和零售基礎設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吸引人口回流。2001年,寶馬和保時捷相繼在萊比錫建立新工廠,帶來了超過一萬個的就業崗位。隨后,德國郵政和亞馬遜也在此建立起物流集散中心[31]。此外,萊比錫還通過在文化、藝術以及體育方面的發展,重塑地域認同并增加城市吸引力。
4.2 科特布斯
在德國東部地區,科特布斯是除首都柏林外,勃蘭登堡州的第二大城市。統一后,城市失去大量人口,房屋空置率飆升,人口老齡化及失業問題進一步加劇[32]。為此,當地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應對措施,試圖實現“剩余住房”的拆遷或循環利用,同時整頓并升級老舊房屋。由政府推動的“Sachsendorf-Madlow”項目,試圖將不同政策和補貼納入城市更新計劃。國際建筑展覽會(IBA)的成立,則旨在通過市政府、住房協會、建筑師和當地農業計劃等多方面的共同協作,支持區域重建,并使得更多的居民能夠參與到城市更新計劃中[33]。
5 反思與啟示
從計劃經濟向自由市場的轉換并沒有為原東德帶來所謂的“盛世景觀”,反而區域內城市在人口、經濟與社會方面均遭受強力的沖擊,甚至在統一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城市發展仍在不斷衰退[34]。追溯原東德城市收縮的原因,其中有兩點內容值得引起反思。其一,華盛頓共識下的“休克療法”所帶來的經濟變革并不是循序漸進的,而是采取斷崖式改革的方式,全面、大規模和快速地實行私有化[35],全盤否定政府對經濟的調節作用。這種激進的改革導致原東德的經濟出現嚴重衰退。因此,原東德經濟結構的快速轉型并未成功地構建城市再次增長的機會,反而帶來一系列問題。其二,統一后的原東德政府忽視了城市發生的一系列變化,一味地單方面強調發展,錯誤的投資方向最終導致城市建設的供需失衡。政府財政的決策失誤導致城市經濟出現危機,規劃建設體制的僵化進一步加劇了收縮現象。
近年來,中國的部分城市開始走向收縮。1990年代末以來,我國大都市區的行政區劃調整與重組包括了撤縣(市)設區、行政區合并和行政界限調整等。這些體制的變化意味著原有行政領域的消亡以及新行政領域的出現[36]。行政區劃的調整不但滿足了發達中心城市對空間的強烈需求,而且為周邊中小城市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會與挑戰。面對調整后市場競爭帶來的壓力,一些中小城市發展出現衰退的跡象。2002年,廣東省政府采用撤縣(市)設區的方式推行市域經濟一體化政策,將順德、南海、高明、三水4個縣級市改為佛山市4個行政區,由地級市政府直接管轄,形成“大佛山”的城市架構。行政區劃的調整打破了區域經濟的分割,避免惡性競爭,佛山四區的人均GDP、財務收支以及各產業增長率均呈現不同程度的增長。然而區域經濟的增長僅僅是短期效應,行政區劃的調整同樣改變了過去地方的市場格局。伴隨區域市場的開放,地方政府權利卻遭到弱化。區劃調整對經濟增長的效應逐年下降,五年后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基本消失,部分區域的經濟發展甚至出現一定程度上的衰退[37]。盡管如此,相關學者與政府規劃部門并沒有對這些增長減緩或是衰退的現象引起足夠重視。本文對統一后原東德城市收縮的探究為中國城市未來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借鑒,即快速的市場化過程可能并不會為城市帶來新的發展契機,反而會導致城市經濟的萎靡不振。面對城市的衰退現象,相關政府以及規劃部門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制定合理的應對措施。
參考文獻:
[1] Pallagst K. Shrinking cities: planning challenges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R]. Cities growing smaller,2008,10.
[2] HauBermann H. Siebel W. Die Schrumpfende Stadt und die Stadtsoziologie[M]. Soziologische Stadt forschung.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1988:78-94.
[3] Wiechman T. Between Spectacular Projects and Pragmatic Deconstruction[C]. Conversion Strategies of Contracting Urban Regions. Dortmund, Germany:2007.
[4] Schilling J, Logan J. Greening the rust belt: A green infrastructure model for right sizing Amer ica's shrinking citie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2008(72):451-466.
[5] Oswalt. Philipp (ed.) Shrinking cities volume 2–Interventions[W], Hatje Crantz,Ostfildern,2006.
[6] Turok I, Mykhnenko V. The trajectories of European cities, 1960–2005[J]. Cities,2007,24(3):165-182.
[7] Michael, C, Burda. Factor Reallocation in Eastern Germany after Reunific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368-374.
[8] Heiland F. Trends in East-West German migration from 1989 to 2002[J]. Demographic Research,2004(11):173-194.
[9] Pallagst, Karina M, T. Wiechmann. Shrinking smart? Staedtische Schrumpfungsprozesse in den USA, in:Gestring, Norbert et al (Ed.) Jahrbuch StadtRegion 2004/2005 Schwerpunkt Schrumpfende Staedte, VS Verlag fuer Sozialwissenschaften[M]. Wiesbaden,2005:105–127.
[10] Blanco H, Alberti M, Olshansky R, et al. Shaken, shrinking, hot, impoverished and informal: Emerging research agendas in planning[J]. Progress in Planning,2009,72(4):195-250.
[11] Schetke S, Haase D. Multi-criteria assessment of socio-environmental aspects in shrinking cities.Experiences from eastern Germany[J].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008,28(7):483-503.
[12] 周愷,錢芳芳. 收縮城市:逆增長情景下的城市發展路徑研究進展[J]. 現代城市研究,2015,09:2-13.
[13] Schett S. An analysis of shrinking cities[J]. Urban Ecology, WS, 2011(12).
[14] 李郇,殷江濱. 國外區域一體化對產業影響研究綜述[J]. 城市規劃,2012(05):91-96.
[15] Dornbusch R, Wolf H C. East German economic reconstruction[M]//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Volume 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155-190.
[16] Marco Bontj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shrinking cities in East Germany: The case of Leipzig[J]. GeoJournal,2004,611:.
[17] Deutschland 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92-2016.
[18] Eberstadt N. Demographic shocks after communism: Eastern Germany, 1989-93[J]. Population and De velopment Review,1994:137-152.
[19] 譚揚芳. 轉軌后德國東部狀況及反思——兼談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J]. 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05):110-122.
[20] Ciela A. “Shrinking city” in Eastern Germany[D]. Bauhaus-Universitt Weimar, 2013.
[21] Rink D. Wilderness: The nature of urban shrinkage? The debate on urban restructuring and restoration in Eastern Germany[J]. Nature and Culture,2009,4(3):275-292.
[22] 田春生. "華盛頓共識"及其政策評析[J]. 南開經濟研究,2004,(05):3-8.
[23] Sinn, G. and H.-W. Sinn (1993) Kaltstart. VolkswirtschaftlicheAspekte derdeutschen Vereinigung,Tübingen:Mohr.
[24] Brezinski H, Fritsch M. Transformation: the shocking German way[J]. MOST: Economic Polic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1995,5(4):1-25.
[25] Statistischer Quartalsbericht Leipzig 1989-2015[R].
[26] Lotscher L. Shrinking East German Cities?[J]. Geographia Polonica,2005,78(1):79.
[27] 巴斯欽·蘭格,許玫. 創意萊比錫:在“自下而上”的城市里創意經濟如何演變[J]. 國際城市規劃,2012(03):6-10.
[28] Rink D, Haase A, Bernt M. Work package 2: Urban shrinkage in Leipzig and Halle, the Leipzig-Halle urban region,Germany[J].2010.
[29] Schmidt S. Sprawl without growth in eastern Germany[J]. Urban geography,2011,32(1):105-128.
[30] Bernt M, Haase A, Gro?mann K, et al. How does(n't) urban shrinkage get onto the agenda? Experi ences from Leipzig,Liverpool, Genoa and Byto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 search,2014,38(5):1749-1766.
[31] 張潔,郭城. 德國針對收縮城市的研究及策略:以萊比錫為例[J]. 現代城市研究,2016(02):11-16.
[32] Lotscher L. Shrinking East German Cities?[J]. Geographia Polonica,2005,78(1):79.
[33] Hunger B. Wo steht der Stadtumbau Ost—und was kann der Westen davon lernen, Informationen zur Raumentwicklung,2003,53,647-656.
[34] Bernt M. Partnerships for demolition: The governance of urban renewal in East Germany's shrinking ci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9,33(3):754-769.
[35] 林毅夫,劉培林. 何以加速增長 惟解自生難題——《前10年的轉軌——東歐和前蘇聯的經驗和教訓》述評[J]. 經濟學(季刊),2003(04):237-252.
[36] 羅小龍,殷潔,田冬. 不完全的再領域化與大都市區行政區劃重組——以南京市江寧撤縣設區為例[J]. 地理研究,2010(10):1746-1756.
[37] 李郇,徐現祥. 中國撤縣(市)設區對城市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J]. 地理學報,2015(08):1202-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