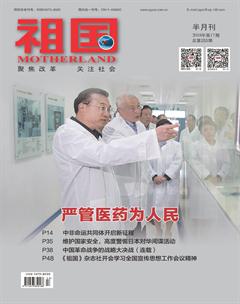尋蹤丱兮城
劉育新
摘要: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為求長生,派方士徐福帶數千名童男童女去海上求仙尋不死之藥僑居的城池叫丱兮城。2000多年前的丱兮城究竟處在何地?這是考證徐福第二次東渡出海始發地的重要依據,學術界目前仍各執其說。
關鍵詞:丱兮城 尋蹤 徐福東渡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為求長生,派方士徐福帶數千名童男童女去海上求仙尋不死之藥僑居的城池叫丱兮城。“婉兮孌兮,總角丱兮”,句出詩經·齊風·甫田。丱在古代即兒童之意。我認為,丱兮城是泛指當年徐福招募的童男、童女僑居之地,而非專指某一城、一地,所以歷史記載中先有千童之名(西漢)而后有丱兮之名(南北朝)前后出現相距七百多年。2000多年前的丱兮城究竟處在何地?這是考證徐福第二次東渡出海始發地的重要依據,學術界目前仍各執其說。
歷史上唯一得到漢王朝確認的徐福東渡的出發地是隸屬渤海郡的千童縣。《漢書·地理志》明確記載:“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以秦之徐福率千名童男女僑寓此邦(注意:此處是此邦而非此地。編者)而此置千童縣,隸屬渤海郡。”而千童縣舊址就在與黃驊市接壤的今河北省鹽山縣千童鎮。徐福第二次東渡的時間,史書上記載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距漢高祖五年的公元前202年僅有8年之隔,所以舊千童縣一帶為第二次徐福東渡三千童男女及種種百工的招募、集結地應是確鑿無疑的。司馬遷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距離徐福第二次東渡的時間相隔僅65年。漢武帝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編寫《史記》,時在公元前104年。 他于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4年完成此書,據徐福東渡的公元前220年間隔時間僅有120來年。所以他的記述應該是可信的。
確定了千童縣的設置與徐福第二次東渡的淵源。那么僑居三千童男童女的丱兮城究竟在哪里呢?《天津府舊志》謂“饒安即丱兮城遺址”。清代南皮學者葉圭綬說:“鹽山縣舊城即丱兮城也”。清同治《鹽山縣志》標注丱兮城在今黃驊東北六里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南朝梁、陳間官員、文字訓詁學家、史學家顧野王(公元519—581年)摘抄各種書籍材料,成書于陳時的《與地志》中記載:“滄州高城縣東北有丱兮城,秦始皇遣童男童女數千人至海求蓬萊不死藥,筑此城以居之,號曰丱兮,漢因置千童縣。”《與地志》成書時,高城縣治已遷大留里(北齊天保七年,公元556年遷今黃驊舊城村)。《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丱兮城,在直隸鹽山縣東北,相傳秦始皇遣徐福發童男女千人,入海求仙,筑城僑居童男女,故名。”賈恩紱先生編撰的民國《鹽山新志》記載丱兮城“城在今治(鹽山)東北七十里楊(羊)二莊之西北”。賈恩紱先生并論述說:“后世因千童由丱兮而起,遂謂千童丱兮為一,其誤顯然。千童即后漢之饒安,東北去丱兮且一百二十里,不容相混。古人名地,不過取故實之距近者。此類殆難枚舉。……謂千童因徐福僑居而得名則可,謂僑居之丱兮即千童縣則不可也”。 這就好像新中國解放前為紀念1938年犧牲于原新海縣(今黃驊市)羊二莊鎮大趙村的楊靖遠烈士,經上級批準, 1940年將樂陵、鹽山和慶云三縣各一部劃為靖遠縣,1945年鹽山縣與靖遠縣合并稱為靖遠縣一樣,而大趙村照樣還稱作“大趙村”同理。至此丱兮城的位置坐落于鹽山縣東北,應該在現黃驊市境內基本上得到了大家的共同認可。
現黃驊境內依舊殘存的和徐福東渡淵源相近的戰漢古城遺址共有兩處。一處是位于現黃驊市羊二莊回族鎮的丱兮城遺址;一處是坐落于黃驊市區北面緊鄰黃驊城區的郛堤城。
丱兮城遺址位于現黃驊市羊二莊回族鎮南街村西北1公里處。2014年黃驊市博物館委托勘探隊對丱兮城遺址進行過一次考古勘探工作,確定了城墻范圍以及城內部分遺跡。2016年3月——6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黃驊市博物館組成考古隊,在2014年考古勘探工作的基礎上對丱兮城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勘探、挖掘工作。在地表深處發現了大量繩紋板瓦、筒瓦、夾沙、夾蚌紅陶片、泥質灰陶片等。初步推斷出丱兮城遺址的時代應為戰國晚期至西漢中期。其中發現帶字的陶片,經專家權威認定為丱兮城的《兮》字,而且是秦代流行的大篆字體。這對丱兮城遺址修建年代、作用地認定提供了一份有力的佐證。該遺址疑似應為徐福東渡時的一處兒童僑居地或一處物資籌備基地。
有關史書記載:“西漢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封公孫敖為合騎侯,于此地置合騎侯國,稱合騎城;《長蘆鹽法志》則稱:系為防猗盧而設的屯兵之所,稱伏猗城,當地訛稱武帝城,今稱郛堤城。
2011年黃驊市邀請保定市文物管理所會同黃驊市博物館組成聯合考古勘探隊,對郛堤城城址分為古城墻和古城址內遺跡兩區進行了勘探。
2014年黃驊市又邀請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會同黃驊市博物館組成聯合考古隊,對郛堤城址進行考古調查和對城址西南角、城址東門及東城墻、和城內7號建筑遺址進行試掘。
兩次對郛堤城遺址挖掘、勘察、認定郛堤城“屬于一座防御性的軍事城址”,是基于郛堤城遺址內沒有發現官衙、民居等建筑遺跡。而郛堤城遺址不論是地表暴露和地下埋藏的大量陶片(多為燕國紅陶釜、豆等生活用器)。卻又給郛堤城“屬于一座防御性的軍事城址”,的認定提出了質疑,但又沒法做其他的解釋。大凡軍事城池,必定有一個堅實、穩固的城墻基礎,而郛堤城和丱兮城遺址一樣,就修筑于地表土層以上,且城墻土質疏松,沒有多大抵御功能,只好解釋為這是沿海地區一種新的臨時筑城方式。
黃驊市去年5月首次在郛堤城遺址附近發現甕棺葬后,經過幾個月持續發掘,已發現甕棺葬超過110座.據黃驊市博物館館長張寶剛介紹說,“由于2000多年來河道挖掘以及自然環境破壞,目前我們發掘的只是整個甕棺葬群遺址的一小部分。據現場勘查,在發掘點南南北200米、東西90米范圍內均有甕棺葬分布,此處甕棺葬估計有近千座,這片甕棺葬群應是國內發現的數量最多的甕棺葬群之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白云翔考察了該甕棺葬群后認為,“甕棺葬墓地實際上是郛堤城的一部分,城說明人的存在,墓地的存在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城的時代和這個城當時的繁榮。”這些甕棺墓葬的發現,足以說明:在戰漢某一個歷史時期里,郛堤城曾聚集、居住過大量的古代先民,這就推翻了郛堤城僅是一座防御性的軍事城址的推論。據張寶剛館長介紹:“通過挖掘甕棺墓葬群得知,戰漢時代郛堤城附近的土地,板結、堅實,不適宜農作物生長。”據此判斷,當時聚集,居住在這里的肯定不是以農耕為生的先民。這批甕棺葬的埋葬時間相對集中,并且排除了是家族墓的可能。那么為什么此處在短時間內夭折了這么多兒童呢?這樣就使我們不得不把史籍記載與當地民間傳說和徐福東渡的事件聯系起來。
2017五月《甕棺葬與古代東亞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黃驊召開,會議期間,與會專家、學者親臨郛堤城考察。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鄭同修研究員當場斷定這不是一座軍事城池。“郛堤城是一座非軍事城池”的論斷、認定得到了大部分與會專家學者的一致認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高崇文教授認為:黃驊又是古黃河入海口,各種跡象與“徐福東渡”事件高度吻合。“徐福東渡”的出海地就在黃驊一代。直接參與過郛堤城遺址考古挖掘的山西大學考古系李君教授更認為:“徐福東渡”的出海地,最能拿出證據的就是黃驊區域。迄今為止,史籍、口碑、歷史遺跡和考古均證明“徐福東渡”出海地在黃驊,這一形成一個完整的、可以互相參照的證據群落。據此郛堤城的修筑時間和作用這一千古之謎應該塵埃落定了。因此我們可以說郛堤城就是當年徐福第二次東渡童男女僑居的丱兮城。
那么有的讀者可能會說了,丱兮城不是在羊二莊鎮嗎?怎么這里也成了丱兮城了呢?我在本文的開頭曾說過,丱兮城應是泛指當年招募的童男、童女僑居之地,而非專指某一城、一地之名,更何況歷史上對丱兮城的具體位置早記述不一。試想當年三千童男女加上招募、照顧這些孩子的人員,以及百工巧匠、弓弩手、船工等人,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再加上攜帶的五谷雜糧種子、生活用品以及數量可觀的渡海船舶,處在那樣的時代,這樣一場載入史冊的舉動,沒有沿海幾處地方官員協力合作恐怕是難以完成的。所以饒安(即后來的千童縣)一帶是招募和集結地,渤海岸邊的古柳縣(今黃驊)即是徐福東渡第二次出海起航的集結地又是始發地,而郛堤城就是當年童男女僑居的丱兮城。
參考文獻:
[1]王升.徐福東渡五大問題新論——以《史記》與《山海經》為線索[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05):52-56.
[2]李小紅,袁玲兒.徐福東渡再探[J].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0,(03):55-59.
(作者單位:河北省黃驊市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