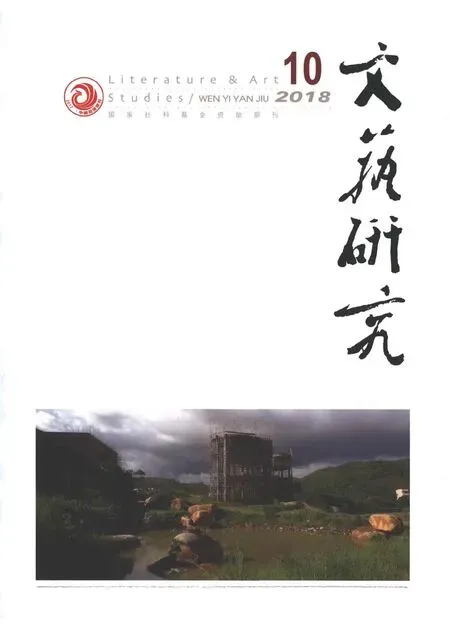“翻轉劇場”與“反場所的異托邦”
——參與式藝術的兩種空間特性
王志亮
按照汪民安的判斷,“最近二三十年文化變革的一個顯著征兆就是當代藝術的盛行”①,那么近十幾年來,當代藝術最為核心的理論論爭之一便是圍繞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而展開。這場論爭主要由法國批評家尼古拉斯·博瑞奧德的“關系藝術”為引線,討論藝術家、參與者與公眾之間應該建立何種關系。這場討論將藝術家在項目中嘗試建立的關系大體分為兩類:對抗與協商。顯然,對抗與協商是兩個政治哲學的概念,其底色是尚塔爾·墨菲和尤爾根·哈貝馬斯的政治哲學理論②。但是,直到目前,我們依然沒有辦法在兩種對立的方案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擇。筆者認為,與其在這兩類政治哲學判斷中擇其一,不如嘗試從具體空間入手,分析參與式藝術的空間生產方式。
一、基于空間生產的前衛藝術實踐
之所以能夠從空間的視角分析時下熱議的參與式藝術(或藝術介入社會),主要基于筆者對前衛美學譜系的基本判斷,即前衛藝術的發展史很大程度上體現為藝術家占據空間和改造空間的歷史。我們也可以借用列夫菲爾的“空間生產”概念來重述這一判斷:前衛藝術的歷史是一部空間生產的歷史。根據這一定義,參與式藝術無疑是最有代表性的當代前衛藝術形式。
前衛藝術之前,沒有任何一種藝術形式專注于塑形既存空間。自歷史上的前衛藝術之始(未來主義、達達藝術和生產主義等),我們才看到專為改造空間而生的藝術形式。經典藝術門類,即便是為占據空間而生的雕塑,也大多不過是特定空間的擺件。當經典雕塑變化形式,開始塑形空間時,就會激起部分人的強烈反應,這正是邁克爾·弗雷德批評極少主義雕塑時所感知到的空間危機。他批評極少主義的文章,可以看作經典現代主義者對藝術塑形空間的極端反應。但是顯然,極少主義并非前衛藝術,它僅僅是對經典現代主義雕塑的一次越界。空間在極少主義的作品中僅具有抽象的物理特性,而無社會屬性。前衛藝術的空間既包括美術館的白立方,又包括日常生活空間和自然空間。總之,前衛藝術塑形的空間絕非抽象的物理空間,而是具體的社會空間。
彼得·比格爾認為,前衛藝術為了融合藝術與生活,不得不反對特定的藝術體制。而這個藝術體制的具體承載者,便是各式各樣的展示和表演空間。所以,前衛藝術的目標指向最后往往落實到空間中。前衛藝術的空間生產具體是指藝術家用作品或自身表演改變了既定空間的固有屬性。沿著空間這條線索,我們可以看到前衛藝術空間生產的兩條脈絡。一是現成品,其中以杜尚的《泉》為典型代表。基于這條線索的前衛藝術可以劃分為歷史上的前衛和新前衛(或后前衛),前者主要涵蓋20世紀初的各類前衛藝術團體,后者則以“體制批判”為核心,特指20世紀60—80年代的一批藝術家,如德國的漢斯·哈克。在學術著作方面,美國“十月學派”的《1900年以來的藝術:現代主義、反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可謂這一脈絡的代表③。二是基于參與的表演和行動,其中以未來主義劇場、蘇聯實驗戲劇和達達現場表演為基礎,經偶發藝術,發展至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參與式藝術。在學術著作方面,克萊爾·畢莎普的《人造地獄:參與式藝術與觀看者政治學》很好地勾勒和分析了前衛藝術的這條譜系。
上述兩條脈絡是前衛藝術發展的兩翼,兩者可共同歸于有關“空間”問題的討論。“空間”成為我們今天理解前衛藝術的核心范疇。批判藝術體制是現成品藝術的核心意義,這已成為眾所周知的論斷。但進一步講,現成品批判藝術體制,目的終究是去改變展示空間的固有屬性,使其和日常生活空間相連接。發展自現成品本身的體制批判,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的新前衛實踐中被進一步精確化了。現成品之外,前衛藝術家基于參與的表演和行動涉及的面向更廣闊,生命力更強。由現成品發展而來的裝置藝術,在當代已經演變為撼人的景觀裝飾,而只有那些強調參與的表演和行動依舊游走在藝術和日常生活的邊界上。前衛藝術發生之始,參與式的表演和行動就不只面對展出空間,更挑戰了演出空間——劇院,以及日常生活空間——廣場、街道、酒館。直到今天,參與式藝術依然活躍于這類場所之中。
按照列夫菲爾的空間三元辯證法,空間可被分為“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再現性空間”(space of representation)。空間實踐是絕對的原始自然形態的空間;空間的表征是社會化的空間;再現性空間則是主體真實體驗后對空間的再現,它受到空間的表征的壓抑,又超越它,返回空間的實踐中④。我們的藝術處于再現性空間之中,而前衛藝術卻是對再現性空間的“越出”。前衛藝術不停留在“再現”階段,而是“越出”至“空間實踐”和“空間的表征”領域。前衛實踐即是一種空間生產。正如列夫菲爾賦予空間的歷史邏輯,如何取代資本主義那抽象的、勻質的空間?社會主義必須進行自身的空間生產,這個空間即是差異性空間。
接下來的問題在于,前衛藝術如何越出再現性空間呢?正如上文所述的兩條脈絡,前衛藝術一般使用現成品和參與兩種方式。無論哪種方式,前衛藝術總是要創造“震驚”(astonishment),從而取代“共鳴”(empathy)。這也是本雅明的消散遣心與阿多諾的靜觀冥想之差異。無論在繪畫領域,還是戲劇領域,觀眾或是坐在劇場,或是站在畫前,都一定要浸入作品,產生共鳴,方能完成欣賞。自從歷史上的前衛藝術開始,讓觀眾“走神”就成為他們的重要目的。但是,現在看來,現成品和拼貼確實已經應驗了比格爾對新前衛的預言,形成了自我否定,完全成為景觀裝置或者影像景觀。這類作品現在達到的效果恰是“走神”的反面,重新返回對觀眾身體和注意力的控制——這也是弗雷德批評劇場化的依據。如今只有參與式藝術,最能代表前衛藝術的當代形態,因為它既沒有完全進入藝術體制,又保持了讓觀眾“走神”的接受特點,準確說,參與式藝術甚至沒有觀眾。參與者不是觀看者,而是表達者、述說者和行動者。
“翻轉劇場”和“反場所的異托邦”是參與式藝術空間生產的兩種方式,兩者都以越出再現空間、直接進入空間實踐和空間的表征領域為目標。翻轉劇場是布萊希特戲劇“間離效果”的當代極端形式,它不僅顛倒了觀眾與表演的關系,而且將社會場所和自然景觀轉化為劇場空間。至于反場所的異托邦,我們用來指另外一類排斥劇場式表演的藝術實踐。藝術家在社會一隅,用藝術的方式進行改造社會的實驗。他們正實實在在地塑形實體空間。
二、弗雷德與畢莎普:劇場與翻轉劇場
2017年在美國古根海姆美術館舉辦的“世界劇場”展,因美國人策劃,又因涉及虐待動物,導致某些作品被迫取消展示。這讓該展覽成為藝術界熱議的話題,“劇場”也隨之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詞匯。當然,策展人孟璐(Alexandra Munroe)的“劇場”是總體性的隱喻,而本文中談論的“劇場”則基于現實空間。在當代批評理論中,討論“劇場”概念的最著名文章是邁克爾·弗雷德的《藝術與物性:論文與評論集》。沈語冰曾精確地總結過弗雷德劇場理論的三個關鍵點:設計觀眾的“情境”,追求跨界的“綜合”,呈現無限的“延綿”⑤。筆者認為,“情境”和“延綿”是弗雷德劇場的關鍵。二者分別指涉空間和時間,對于劇場的建構來說缺一不可。誰的空間和時間呢?當然是觀眾的。極少主義作品不僅自己占據空間,而且將觀者納入自身空間之中;時間則是觀眾觀看作品時需要不斷移動視線和位置而經歷的過程。
如今當我們都在信服弗雷德的“劇場”概念時,可曾反問過,既然極少主義是劇場,那還有什么作品的展示不是劇場?顯然,弗雷德拿現代主義的空間自足和瞬間性來對比極少主義的劇場化時,僅僅基于單件作品來考慮,從未在整體上把展示空間與劇場空間進行過比較。歷史上沒有任何作品如波洛克和羅斯科的繪畫一樣,需要巨大的尺寸,需要占據一個獨立的立方空間。假如我們把一個獨立展廳看作一個整體,那么根據現在的展示空間來看,弗雷德對劇場的界定已然失效。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展示空間不在構建觀眾的情境,不再呈現無限的延綿。當代美術館和畫廊中的展廳設計,其劇場化的程度顯然要遠遠高于極少主義的劇場效應。
弗雷德提出劇場化的最大貢獻在于,他指出了極少主義作品的觀看機制。而這個概念可供討論的地方卻在于,他未經轉化地把劇院空間和美術館空間相比較,完全抹去了兩者的本質差異。回到極少主義設計的觀看機制,作品設計了觀眾的情境,觀眾身體的進入和移動成為作品的一部分。但是,對比一下劇院的情況,劇院中觀眾的位置是被固定的,舞臺位置獨立于觀眾位置,兩者涇渭分明。這樣的空間安排,難道不是經典現代主義藝術的空間結構嗎?而在這樣的劇場中,表演產生的效果是“間離”,還是“共鳴”,則完全依賴于演員和導演使用的技巧。
所以筆者認為,弗雷德的“劇場”概念一開始就是翻轉劇場,而不是傳統的表演與視聽的劇場。相反,無論是古典藝術,還是現代藝術,它們在經典的劇院和博物館中,都遵循表演與視聽的二元關系——這才是真正的劇場。因此,我們與其說弗雷德反對劇場性,不如說弗雷德反對翻轉劇場性。對于他而言,現代藝術的審美應該呈現經典劇場的模式,觀眾是觀眾,表演是表演,兩者各占據一個自足的空間。
至此,我們面臨一次概念的顛倒。極少主義不是劇場性,而是翻轉劇場性。弗雷德所支持的現代主義藝術才是經典的劇場性。無論劇場還是翻轉劇場,“在場”(presence)都是兩者的關鍵概念,它們的區別只不過體現在觀眾的身體是否移動而已。所以,我們用弗雷德的“劇場”概念來討論當代的參與式藝術,顯然是錯位的。參與式藝術的譜系不在于極少主義的翻轉劇場性,而是在于歷史上前衛藝術對劇場空間的顛覆和拓展。

1920年尼古拉·埃夫雷諾夫在圣彼得堡導演的《東宮的震蕩》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參與式藝術的劇場化時,還應從畢莎普提出的劇場譜系出發⑥。畢莎普為整個參與式藝術的翻轉劇場譜系找到了這樣三個起點:一個是意大利的未來主義劇場,另一個是蘇聯的大眾劇場和大眾景觀,第三個是巴黎達達的戶外表演。對比畢莎普談論的“劇場”概念,我們會發現,弗雷德的“劇場”僅是隱喻意義上的,與表演沒有任何關系。而自未來主義劇場開始,藝術家早已在真實劇場中開始了翻轉劇場的表演。這類翻轉劇場的表演發展至今,已經涉及到日常生活的各類空間,如劇院、酒館、畫廊和美術館,甚至是戶外空間。
首先是在劇院中反劇院,這也是翻轉劇場的最原初形式。激活觀眾是這類翻轉劇場的重要目的。從未來主義劇場到蘇黎世達達在伏爾泰酒館中的表演,這類最初的翻轉劇場都旨在混合多種表演于一體,給觀眾造成足夠的震驚。1910年開始,未來主義藝術家——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卡拉 (Carlo Carra) 和 魯 索 洛(Luigi Russolo)——參與了幾場意大利的“晚會”。雖然我們沒有辦法看到當時晚會的照片,但卻可以通過藝術家的兩件速寫,了解到當時的大體情況。一件作品是波丘尼的《漫畫:1911年1月1日,未來主義者在特雷維索的晚會》,另一件是杰拉多爾·多托里(Gerardo Dottori)的《未來主義者在佩魯賈的晚會》。在這兩張帶有記錄性質的漫畫中,未來主義者將美術館和劇場空間進行了交錯并置。劇場的核心功能是展示動態表演,但未來主義者展示的卻是靜態繪畫。漫畫中的會場一片混亂,未來主義者在舞臺上發表演講,觀眾們在呼喊,繪畫在這個舞臺上成為主角。當然,未來主義者并沒有真正摧毀美術館,而是把作品直接搬進劇場,以此否定美術館的權威性。與此同時,劇場的空間性質也被改變。他們創造了一個綜合性空間,藝術家、作品和觀眾同時在場。面對這樣一個混雜性空間,我們可以說未來主義者把美術館搬進了劇院,亦可以說他們把劇院改造成了新型美術館。所以,未來主義者實際建立了一個似是而非的空間,它既不是普通的劇場,更不是美術館,而是兩者的混雜體。未來主義者要與觀眾共享同一空間,要求觀眾在場。馬里內蒂將這種混雜性的空間稱為“未來主義劇場”(Futurist Theatre),以此區別于傳統劇場被動、無聊和死氣沉沉的氣氛。未來主義者借助交響樂、詩歌、繪畫和雕塑的混合再現,讓劇場不再是劇場,讓原來靜坐的觀眾運動起來,究其原因,是要顛覆美術館象征的父權。未來主義崇拜速度、運動和時間,因此那些代表過去的空間——美術館、圖書館和學院——成為被攻擊的對象。未來主義劇場正是他們建構的替代性空間,一個完全面向現時和在場的空間。

波丘尼 漫畫:1911年1月1日,未來主義者在特雷維索的晚會
其次是公共空間的劇場化。在這類翻轉劇場中,劇院的室內空間被翻轉至戶外,成千上萬的大眾被召集起來參與演出。這早在蘇聯被稱為“大眾景觀”(Mass Spectacle)。“大眾景觀”雖然遵循戲劇的基本形式,卻使用壓倒性的集體意象,來調動公眾意識⑦。如為紀念十月革命,1920年尼古拉·埃夫雷諾夫(Nikolai Evreinov)在圣彼得堡導演的《東宮的震蕩》,有八千多人參與,吸引了超過十萬觀眾觀看。大眾景觀與更早一點的“大眾劇場”(Proletkult Theatre)一起構成了當時蘇聯實驗戲劇意識形態的兩翼,一側是集體主義,另一側是平等意識。大眾劇場更在意消除表演者與觀眾的等級秩序,于是改變了劇場的空間布局,以及強調演員的業余性。例如弗謝沃洛德·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和弗拉基米爾·馬雅科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的《神秘滑稽劇》。在舞臺設計中,梅耶荷德改變了舞臺布置,讓舞臺通過斜坡直接與觀眾坐席相連接。表演過程中觀眾可以來回走動,最后一場表演時,觀眾被邀請上臺一起參與表演。比上面這一事例更進一步的是業余者劇場(Amateur Theatre),這類劇場實驗為了讓戲劇大眾化,完全依靠業余演員完成演出。
同樣是將公共空間劇場化,但后來蘇聯的“集體行動小組”(Collective Actions Group)則與早期的戲劇實驗有著全然相反的目的和意義。集體行動小組以藝術家安德烈·莫納斯特爾斯基(Andrei Monastyrski)為核心,自1976年開始不斷在莫斯科的郊外策劃集體活動,他們把這類活動稱為“郊外旅行”(Trips out of Town)。
為區別于大眾景觀,我們可以稱集體行動小組的項目為“小眾劇場”。大眾景觀與城市廣場相結合,而小眾劇場則與郊外空域相結合,兩者形成鮮明對比。前者是蘇聯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后者則是逃離集體的個體沉思。莫斯科郊外空曠無人的空間被翻轉為劇場,它的“空性”為主體的獨立思考提供了可能性。例如,在1976年的作品《顯現》中,近三十位參與者接到邀請到莫斯科郊區的伊斯馬洛夫斯基地區(Izmaylovskoe field)。當參與者到達該區域一邊后,兩名表演者從另外一邊出現,穿過空地到達參與者所在地,分發給觀眾每人一份證書,以證明他們到場參與了這次活動。由于集體行動小組的“郊外旅行”一般發生在空闊的郊區,因此,參與者到達目的地需要耗費一定時間。表演者與參與者之間相隔遙遠,彼此視野非常模糊,而且觀眾并未被提前告知表演內容。寒冷的環境中,聚集在一起的觀眾等待觀看對面要發生的事情。這個等待的過程,包括乘坐火車、公交車等交通工具到達和離開聚集地的過程,以及事后參與者對事件的評論,都成為集體行動小組作品的有機組成部分。于是,集體行動小組的翻轉劇場也包含了劇場之外的時間。正是在這些似乎什么都沒有發生的“空白時間”中,莫納斯特爾斯基強調了他們的核心美學話語:“集體行動小組的美學話語不是建立在藝術行為本身,而是其伴隨而來的附屬物,例如到達現場的各種限制因素,以及與計劃沒有直接關系的事件等。”⑧參觀者到達活動場地的等待時間,以及在活動過程中出現的等待時間(等待表演者出現、靠近、消失等),都成為莫納斯特爾斯基所謂的“中斷”(pause),時間的“中斷”恰是主體沉思的開始。這種沉思被蘇聯觀念藝術家伊利亞·卡巴科夫(Ilya Kabakov)生動地描述出來。作為參與者,他曾這樣描述自己在活動過程中的感受:“從我上火車那一刻開始……這是第一次,我回到了我的‘自身’;我們擁有了自己的世界,與現實世界平行。”⑨在參與者經歷多重“中斷”的過程中,集體行動小組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布萊希特的“間離效果”理論。

杰拉多爾·多托里 未來主義者在佩魯賈的晚會

集體行動小組1976年的作品《顯現》
翻轉劇場的第三個表現形式是美術館的劇場化。表面看來,這是我們在當代藝術展示空間所見最多的劇場形式,實則不然。當代藝術展覽現場的多數表演依然是傳統的劇場,因為這類表演未在根本上改變藝術家表演與觀眾觀看的二元關系。一場在美術館中的表演可被稱為“翻轉劇場”,它必須同時討論表演者和觀看者的身份問題。在古巴藝術家塔尼亞·布魯格拉(Tania Bruguera)的作品中,她將當代美術館翻轉為劇場,意味著劇場將成為控制主體行為的權力空間。《塔特林的低語,5#》實施于2008年的泰特現代美術館旋渦大廳,表演者為兩位倫敦騎警。表演開始,兩位騎警進入旋渦大廳,關閉入口。大廳中的觀眾并沒有接到有關表演的通知,因此,騎警的出現對于他們來說是一場意外。騎警采用日常工作中的方法控制觀眾,例如通過馬匹的側移,不斷將觀眾分組、拆散與再分組,持續時間二十分鐘。
按照布魯格拉的說法,她更傾向于將這件作品作為一個事件來看待,然后才是一件作品。騎警和觀眾都非表演者。騎警隸屬于倫敦警察廳,他們進入展廳,對觀眾采取控制措施。這些行為屬于他們日常工作的再現。在這樣一個臨時翻轉的空間中,沒有所謂的表演者和觀察者,只有實施控制者與被控制者。
總之,翻轉劇場是對傳統劇場形態的顛覆。在這個過程中,顛覆既有的空間功能是藝術家的首要任務,之后便是對于觀眾和表演者身份的顛覆。我們也可以說,只有顛覆了傳統的表演者與觀看者之間的固定位置和身份,我們才能完成對整個劇場空間的翻轉。無論劇場如何翻轉,劇場空間都無法擺脫臨時性與虛擬性的特征。未來主義劇場和大眾劇場翻轉的室內空間,大眾景觀與集體行動小組翻轉的室外空間,《塔特林的低語,5#》又返回到室內空間。這類空間的翻轉隨著各自所處時間和地域的差異,其背后的文化意義顯然各不相同。無論哪種翻轉劇場,事件結束,被翻轉的劇場也隨即消失。所有參與者對所參與事件的臨時性與虛擬性早有準備,即便是突然“闖入”泰特現代美術館的兩名騎警,也不過配合藝術家演出了一部自由發揮的戲劇。觀眾被暫時限制人身自由,一開始的驚恐必然會轉為表演式的配合,因為在美術館中,任何觀眾都會意識到這是一個安全之地。在無法擺脫空間的臨時性和虛擬性的情況下,異托邦成為參與式藝術的另一種空間轉化方式。

布魯格拉 塔特林的低語,5#
三、作為反場所的異托邦
異托邦(Heteropopias)天然具有顛覆既定社會空間屬性的特征,福柯稱之為“反場所”。場所即是那些已經存在于現實世界的日常生活空間。我們只有重述福柯的異托邦理論,才能用反場所來分析參與式藝術的異托邦特征。福柯在1967年的一次題為《另類空間》的演講中提出了“異托邦”的概念。他解釋道,異托邦是“類似于反場所的東西,是有效實現了的烏托邦,在其中,真正的場所被同時表現著,爭論著,倒置著……這類地方絕對不同于他們所反映,所談論的所有場所”⑩。可見,“異托邦”既反映著社會,也對抗社會的常規空間。它并置異質空間。
福柯雖然界定了異托邦的反場所屬性,但在具體的論述中,顯然沒有給它劃定明確的邊界。按照福柯的闡釋,異托邦幾乎囊括社會空間中除工作和私人生活之外的所有場所。他闡述了四種類型的異托邦。第一種類型以養老院和精神病院為典型,這類異托邦專為身體脆弱和異常的社會成員所設立;第二類以公墓為典型,它們存在于整個人類歷史中,但意義有所不同,并占據不同的地理位置;第三類以劇院、影院和花園為代表,它們可以并置異質性空間;第四類以圖書館、博物館和集市為代表,它們是異質時間的集合。當然,在福柯的論述中,四種類型的異托邦界限并非如此清晰,不可逾越。例如公墓,福柯認為它也屬于第四種類型的異托邦,因為公墓的時間顯然不同于我們日常生活的時間。每種異托邦都有一道屏障——或可見,或不可見——將自己與現實場所隔離開來。與現實空間相比較,異托邦不是創造幻象空間,就是創造補償性空間。
根據福柯對異托邦的舉例和規定,我們自然會問:還有什么空間不是異托邦嗎?恐怕只剩下我們的日常起居空間了。哪怕是我們的工作空間也有可能是異托邦。例如,對于那些在公墓、花園、監獄和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來說,異托邦和常規空間就合二為一了。
所以,福柯規定的異托邦顯然太過寬泛,不足以幫助我們尋找真正的異質空間。或者說,福柯的異托邦原本就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行的關鍵因素,它們就是真實的場所本身。從某種程度上說,當代藝術,尤其是參與式藝術創造的空間才是真正的異托邦。因為它具有真正的反場所特征,與常規場所呈現異質性關系。這類異托邦改變了所有既定場所的固有屬性,創造出一個個全新的存在空間。
法國批評家博瑞奧德在闡述關系藝術時,就已經涉及到這樣的“異托邦”概念,他用了“迷你烏托邦”的概念:“建構共活關系(Convivial Relation)是60年代藝術的歷史常態。90年代藝術重拾這個問題,但是擱置了六七十年代最為核心的藝術定義問題……社會烏托邦和革命的希望讓位于日常生活的迷你烏托邦和模仿策略。”迷你烏托邦來自20世紀60年代有關社會烏托邦的理想,但是它在90年代卻顯得更加現實。更準確地說,博瑞奧德的迷你烏托邦更類似于情景主義者試圖建構的情境,不過,在他看來,德波號召的“建構情景”概念是以替代為核心,“試圖用藝術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驗性實現來替代藝術再現”?。就關系美學的主張來說,藝術的邊界在90年代年已經不是問題,關系藝術也不再希冀讓藝術在生活中實現。依照博瑞奧德的觀點,藝術在一個獨立時空中生產出新的關系模式,遠比試圖在日常生活中實現藝術更能提示景觀的破壞力。也就是說,歷史上的前衛藝術的烏托邦是一個面向未來的時間概念,一個從未實現的空間概念,而迷你烏托邦是面向當代,確實存在于整個社會結構中的一個時空。當然,博瑞奧德提倡的關系藝術并非都符合反場所的異托邦概念,但藝術家提拉瓦尼亞(Rirkrit Tiravanija)的作品卻具有明顯的異托邦特征。這位藝術家的作品一般會改變畫廊和美術館空間的固有屬性,從而創造一個臨時的異托邦。
參與式藝術中的異托邦與劇場有著根本區別。首先,在經典劇場和翻轉劇場中,總是上演各種形式的戲劇。反場所的異托邦則從根本上拒絕表演,它是一系列實在事件的集合。其次,發生在美術館內和美術館外的翻轉劇場,它所承載的是一系列臨時性事件,而反場所的異托邦則是發生在社會空間中的連續性事件,它總以檔案的形式進入美術館。鮑里斯·格羅伊斯(Boris Groys)所謂藝術作品轉向藝術檔案,實際就是指反場所的異托邦的檔案化問題?。再次,翻轉劇場從不改變空間形態,表演結束,劇場即消失。反場所的異托邦則不然,它以改變特定空間的固有屬性為目的,這是所謂“反場所”的關鍵。總之,反場所的異托邦不僅占據空間,它還創造空間。正如列夫菲爾論述的再現性空間,反場所的異托邦超越空間實踐和空間表征,生產出新的空間。
近幾年來中國當代藝術家在鄉村展開的一系列藝術實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反場所的異托邦是如何創造了新型空間。如果說鄉村是常規空間的一個特定場所,那么由于藝術實踐的介入,這類常規空間反而成了反場所的異托邦。當代藝術家介入鄉村,把鄉村改造成反場所的異托邦的同時,也把鄉村改造成藝術的問題現場。在此之外,反場所的異托邦使得藝術家與當代藝術體制拉開距離,讓他們獲得某種程度上的創作自由。甘肅省石節子村設立的石節子美術館應該算是較早的反場所的異托邦的嘗試,西安美術學院雕塑系的靳勒勒既擔任石節子村的村長,又擔任美術館館長一職;在西南地區,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的焦興濤作為發起人,2012年開始在貴州羊磴鎮建立“羊磴藝術合作社”,持續開展藝術創作;2015年唐冠華等人在福州開始實踐南部生活“共識社區”?。
這類鄉村實踐一般具有以下四個基本特點。第一個特點是自我組織。任何一個在鄉村展開的參與式藝術,都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為,而是由藝術家自發組成團體,然后在鄉村展開實踐。自我組織的核心是藝術家行動的自發性。由于藝術家的一切藝術實踐都是自發行為,所以自然產生了第二個特點,即自我授權。沒有人賦予藝術家相應的權利和義務介入鄉村生活,他們自我規定著自己的權利邊界,沒有統一的行動目標。正是因為此,每個團體所處理的問題和實踐效果各有差異。第三個特點是付諸行動。參與式藝術都將行動而不是展示放到第一位。藝術家的行動改變著參與者的日常生活結構。例如,共識社區在福建的具體活動得以落實到一個微型的社會結構中,他們在福州閩侯縣荊溪鎮關中村建設自己的生活空間,而藝術成為維持空間發展的必要因素;羊磴藝術合作社的許多項目都直接改變著羊磴鎮建筑外觀,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第四個特點是預設平等。之所以說這樣的社團具有政治性,主要因為他們在自己成員之間、自己與社區鄰居之間預設了一個平等的概念,平等又以最基本的協商為手段,這是我們至今可以討論其政治性的關鍵點。平等觀念是羊磴藝術合作社的基礎行動理念,其組織者焦興濤用更加明確的協商來概括他們的藝術實踐。例如,焦興濤曾總結過“羊磴藝術合作社”的幾個原則,其中第一個原則就是“藝術協商”?。協商讓藝術不再是藝術本身,它促使藝術家跨入人際交流的領域。

羊磴藝術合作社 馮豆花美術館
最后我們要追問:反場所的異托邦有何意義呢?我們可以用“亞政治”(sub-politics)這樣的術語來描述反場所的異托邦的意義。反場所的異托邦的空間同時也是亞政治的空間。亞政治從短期效果來看,往往不會對制度權威構成挑戰。它發生在階級和政黨政治之外,所涉及的問題也不再通過傳統意識形態來表達,同時也不是要訴諸政治制度來加以解決?。按照烏爾里希·貝克的觀點來說,亞政治不是主體對政治權力作出的反應,而是對社會現代性消極后果的回應。亞政治的主體不再是特定階級,而是對某一問題有共同意見的各類人群。
反場所的異托邦實現了亞政治的作用,它讓那些被個人主義抽離出社會秩序的主體重新回到社會現場。這個現場在亞政治領域不必然意味著對公共話題展開討論,而是進入一種人際關系共處的網絡。這些主體包括參與社團的藝術家和一般公眾,以及社團活動所邀請和涉及到的其他個人。
當然,筆者也總是懷著矛盾的心情觀察這類鄉村實踐,因為它們統一避免了政治性的“抗爭”,選了協商的和平路徑,所以時常顯得政治正確。其次,這些社團是否達到了協商的目的?面對這些實踐,狹義的藝術和審美顯然已經無法適用。鑒于此,我們考察的標準是否應該回到社團如何影響了社區形態和參與者的意識,又在多大程度上實踐了協商原則?這些問題現在依然不明朗。沒有什么藝術實踐比反場所的異托邦更需要時間來檢驗。

南部生活“共識社會”
結語:拓展美術館功能
從歷史上的前衛藝術開始,以美術館為代表的展示空間就成為藝術家進行空間生產的主要場所。作為前衛藝術的當代形式,參與式藝術對美術館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翻轉劇場,還是反場所的異托邦,藝術家都在強調藝術的事件性質。藝術事件或許可以重演,但卻絕對不能被靜止地陳列。在反對復制性這個層面上,反場所的異托邦比翻轉劇場更激進,藝術家們從事的空間生產即是生活本身,日常生活無法被重演,只能以檔案的形式呈現出來。基于此,當代的參與式藝術給美術館帶了更多挑戰,或者更準確地說,在美術館試圖包容這類藝術形式時,無形中拓展了自身的功能。在常規的藝術品展示、收藏和教育功能外,美術館逐漸具有了檔案館的職能,它不再展出藝術作品本身,而是展出有關藝術的種種檔案。這類檔案現在已經頻繁現身于各大雙年展的現場。另外,美術館展出這類檔案,又進一步推動了藝術事件的持續發展,所以,美術館往往又成為藝術事件發展的推動者,有時甚至是觸發者。例如,2016年上海雙年展的“51人”項目,由五十一個一次性事件組成。如果沒有美術館和雙年展為依托,這個項目或許從來不會發生。顯然,相比基于現成品的裝置藝術,參與式藝術已經成為21世紀更前衛的藝術形式。它通過事件來從事空間生產,從而進一步影響了當下的整個藝術體制。同樣,如何定義和言說這類藝術形式,也是我們當下藝術理論面臨的巨大挑戰。
① 汪民安:《藝術批評為何?》,《從A到Z:當代藝術關鍵詞——FRIEZE25年精選集》,北岳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6頁。
② 這場論爭涉及法國哲學家雅克·朗西埃、美國批評家格蘭·凱斯特和克萊爾·畢莎普等,具體討論可見蔣洪生《關系藝術,還是歧感美學:雅克·朗西埃VS.尼古拉·布里歐》,http://gallery.artron.net/20130529/n456459.html;王志亮《對抗還是協商:參與式藝術爭論的兩條審美路線》,載《美術觀察》2017年第1期。近五年間,有關參與式藝術的實踐和討論在中國迅速展開,僅在2017年就出現兩個較大型的以社會參與為主題的展覽,一個是“城市共生——深港城市/建筑雙年展”(深圳),一個是“社會劇場——重慶青年美術雙年展”(重慶);相關討論也不斷涌現,如《碧山》雜志2017年第10輯專辟“藝術介入社會”討論該問題,2018年“藝術社會學青年學者論壇”(東南大學)也對藝術介入社會和城鄉發展展開專題討論。
③ Cf.Hal Foster,Rosalind Krauss,Yve-Alain Bois,Benjamin H.D.Buchloh,Art Since 1900,New York:Thames&Hudson,2016.
④ 張子凱:《列夫菲爾〈空間生產〉評述》,載《江蘇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
⑤ 沈語冰:《譯后記》,邁克爾·弗雷德《藝術與物性:論文與評論集》,張曉劍、沈語冰譯,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3年版,第417頁。
⑥ 據筆者了解,畢莎普首先提示了這一譜系的源頭,而本文接下來的論述將主要從空間轉換角度,來展示參與式藝術的空間特征。詳細內容參見Claire Bishop,Artificial Hells:Par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Landon:Verso,2012,pp.41-65。
⑦ Claire Bishop,Artificial Hells:Par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p.58.
⑧⑨ Boris Groys(ed.),Empty Zones:Andrei Monastyrski and Collective Actions,London:Black Dog Publishing,2011,pp.72,14.
⑩ 參見福柯《另類空間》,王喆譯,載《世界哲學》2006年第6期。
? Nicolas Bourriaud,Relational Aesthetics,trans.Simon Pleasance and Fronza Woods,Paris:Les Presses du Reel,2002,p.31.
? 格羅伊斯在《生命政治時代的藝術:從藝術作品到藝術檔案》一文(詳見Boris Groys,Art Power,Cambridge:MIT Press,2008,pp.53-66)中,詳細闡釋了當下藝術的檔案轉向,他提出藝術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而藝術作品僅僅成為對這類生活的記錄。
? 這是一個實驗社區,它指有共識的某類人群自發組成的獨立生活社區。詳見“家園計劃”微信公共號(anotherland)。
? 這幾個原則分別是:“藝術協商”“五個不是”“緩慢的持續”“有方向無目標”“警惕意義”,詳見焦興濤《尋找例外:羊蹬藝術合作社》,載《美術觀察》2017年第12期。
? “亞政治”是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的術語(詳見烏爾里希·貝克、安東尼·吉登斯、科斯特·拉什《自反性現代化》,趙文書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18—31頁)。墨菲對貝克的評論詳見《論政治的本性》,周凡譯,江蘇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版,第30—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