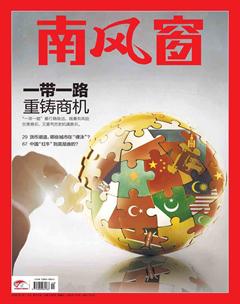新科技對發展中國家是福是禍?
丹尼·羅德里克
新技術降低了人們所使用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還能不斷推陳出新。無論是在窮國還是富國,所有的消費者都從中得到了好處。移動電話就是一個新技術深刻影響生活的明顯例子。同樣,通過手機提供的移動銀行,也可以為那些沒有銀行網點的偏遠地區提供金融服務。這些都是科技改善窮人生活的實例。
但是,如果要為發展做出真實且持續的貢獻,科技不僅應當提供更好更便宜的產品,還必須帶來更多高薪工作。換句話說,它必須在生產者和消費者兩個角度去幫助窮人。而一個被經濟學家泰勒·科文稱為“手機而非汽車廠”的增長模式,則提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如何才能買得起手機?
讓我們再次回到移動電話和手機銀行的例子。由于通信和金融都是生產性投入,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既是生產者服務又是消費者服務。舉個例子,一項知名研究記錄了印度喀拉拉邦的手機普及如何讓漁民得以利用當地市場之間價差進行套利,使其利潤平均增加了8%。而肯尼亞無處不在的移動銀行服務M-Pesa顯然讓貧困婦女能夠從小農經濟轉向非農業經濟,從而為最底層民眾帶來了顯著收入增長。
新數字技術在改變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大規模農業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大數據、GPS、無人機和高速通信,使得服務得以改善和擴展;優化了灌溉、農藥和化肥使用;建立了預警系統,實現了更好的質量控制。這些改進提高了農業生產力,促進了農業向具備更高回報的非傳統作物實施多元化擴展。
然而,圍繞這些新技術所創造的可能性,還存在一些宏觀問題。生產力增益是否足夠大?它們能否在整個經濟中迅速擴散?
任何關于全球價值鏈貢獻規模的樂觀情緒,都必須回應三個令人清醒的事實:首先,近年來全球價值鏈的擴張似乎有所止步。第二,除了某些亞洲國家之外,發展中國家對全球價值鏈的參與仍然非常有限。第三,或許也是最令人擔憂的一點,是近期貿易和技術趨勢對各國國內就業的影響令人失望。
細看之下,就會發現全球價值鏈和新技術展現出了一些限制(甚至可能損害)發展中國家經濟表現的特征。其中一個特點是總體偏向于技能和其他能力,拉低了發展中國家在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等活動中的相對優勢。其次,全球價值鏈使得低收入國家更難以利用其勞動力成本優勢,來抵消其技術劣勢。
對這些問題的常規回應是,強調建立互補技能和能力的重要性。我們經常聽見的說辭是,發展中國家必須升級其教育系統和技術培訓,改善其商業環境并加強其物流和運輸網絡,以便更充分地利用新技術。
但指出發展中國家需要在所有這些方面取得進展的觀點,既不新穎,也沒有用。這就如同說“發展就是發展的前提”那樣。貿易和技術在能夠利用現有能力時才能算是提供了機會,從而提供了更直接和可靠的發展途徑。當它們首先需要昂貴的投資時,就不再是一條制造業主導型發展的捷徑。
將新技術與傳統的工業化模式進行比較后會發現,后者才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首先,制造業是可交易的,這意味著國內產出不受國內需求的限制。其次,制造技術訣竅相對容易在各國之間轉移,特別是從富國到窮國。第三,制造業對技能的要求并不十分高。
這三個特點結合在一起,使得制造業成為發展中國家向更高收入水平攀登的自動扶梯。而新技術在技術訣竅轉移的難易程度及其所隱含的技能要求方面,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因此,它們對低收入國家的凈影響似乎更加難以拿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