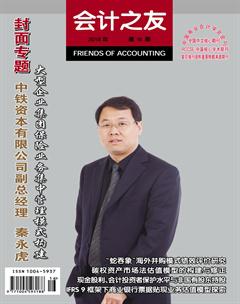創業投資IPO退出回報影響因素研究
王力軍 張羅倩 范雪艷
【摘 要】 以1996—2016年有創業投資參與的749家IPO公司為樣本,考察了創業投資特征與被投資公司特征對于創業投資機構退出回報的影響。研究表明,國有、民營和外資創業投資在IPO退出回報方面沒有顯著差異;領投創投機構持股比例、領投創投機構投資距IPO時間、被投資公司銷售增長率和凈資產收益率與創業投資回報倍數顯著正相關,領投創投機構管理資產規模、最終控制人控制權比例和回報倍數顯著負相關,創投董事占董事會比例、投資地理距離、投資輪數、公司所在地等與創業投資IPO退出回報均不相關。我國應完善創業投資發展的宏觀環境和政策體系,提高創業投資機構的業務水平和從業人員素質,促使創業投資在支持我國創新創業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關鍵詞】 創業投資; IPO; 回報倍數
【中圖分類號】 F83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8)16-0036-06
一、引言
創業投資作為一種向具有高增長潛力的未上市創業企業進行股權投資并提供管理增值服務的投融資制度創新[1],自20世紀中期從美國開始發展以來,就在支持企業創業活動、推動戰略新興產業成長和提升經濟整體競爭力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IPO是創業投資最重要的退出渠道。通過被投資企業IPO上市,可以為創業投資機構帶來巨大的品牌效應和豐厚的財務收益。國內外許多文獻考察了創業投資IPO退出績效。Yael et al.[2]發現更多聯合投資能夠顯著提高創業投資組合公司中通過IPO退出比例;Nahata[3]則發現聲譽高的創投機構投資的企業更可能成功IPO或被收購;Lindsey[4]發現創投機構投資建立了戰略聯盟的企業更容易通過IPO或被收購實施退出;Ozmel et al.[5]發現在聯合投資中有更多居于網絡中心位置的創業投資提高了IPO退出比例;Chen et al.[6]針對美國研究發現集聚在舊金山、波士頓和紐約地區的創投機構所投資企業通過IPO成功退出比例更高。錢蘋等[7]利用調查問卷采集的數據,發現我國國有創投機構退出項目平均投資回報率顯著低于非國有創投機構,創投機構的資本規模與回報率顯著負相關,上海和深圳兩地創投機構退出項目回報率顯著高于其他地區;劉志陽等[8]則發現我國創投機構參與聯合投資可以提高創業投資退出率。
不同于以上研究主要以IPO退出比例來度量創業投資機構績效,本文直接以被投資企業IPO時的投資回報倍數作為度量創投機構退出績效的指標,并綜合考察創投機構特征及被投企業特征對其IPO退出績效的影響,研究對于認識我國創業投資現狀及其發展趨勢具有重要意義。
二、研究變量與模型設定
(一)研究變量
1.被解釋變量
創業投資機構IPO退出回報。在實務和研究中,度量創業投資項目退出回報最常用的量化指標是投資回報倍數。投資回報倍數(Multiples)是指創投投入金額在最終退出后的增值倍數,等于退出現金流總金額/投資總金額。本文以企業IPO上市當日作為創投最終退出時點,并以該日股票收盤價乘以創投機構持股數量作為創投的IPO退出總價值,計算其回報倍數;如創投機構在公司IPO之前中途轉讓過部分股份,還需加入該部分轉讓所得金額;具體計算公式為:投資回報倍數=(IPO當日股票收盤價×創投持股數+IPO之前轉讓股份所得金額)/創投投資總金額。鑒于存在多個創投投資一家公司的情況,選取其中持股比例最大的VC作為領投創投機構,并針對其開展研究。
2.解釋變量
(1)VC機構的特征因素
領投創投機構性質:虛擬變量,分為國有(VC_state_
owned)、民營(VC_private_owned)和外資(VC_foreign_owned)。領投創投機構為民營性質取1,否則為0;領投創投機構為外資性質取1,否則為0。與國外成熟市場不同,中國市場中同時存在國有、民營和外資三類VC,其性質差異可能會給被投資企業帶來不同影響,從而影響VC退出回報。
持股比例(VC_shareholding):領投創投機構持股數除以IPO公司發行后總股數。持股比例越高,創投最大化自身價值的動機越強,越有可能通過積極的管理參與來監督企業并為企業提供增值服務,從而有利于創投機構IPO退出回報。
VC董事占比(VC_director):公司IPO時創投董事數量除以董事會總人數。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機制,公司重大戰略制定、投融資決策、高層管理人員聘選等事項均需董事會決議通過,創投進入董事會既可以獲取很難被外界所知的內部信息,更好地了解企業管理運營中存在的問題;又能夠利用表決權對企業重大管理事項直接提供意見和建議,有助于創投監督和增值服務職能發揮,最終提高創投機構IPO退出回報。
聲譽(reputaion):參照Peggy et al.[9]的研究,分別以領投創投機構IPO時資產規模(VC_size)和投資公司時年齡(VC_age)作為代理變量。創投的聲譽來自其歷史經營業績,創投管理能力越強、過往業績越好,投資者越愿意將資金投入其所管理的基金,管理資產規模越大;創投機構年齡越長,說明其經營持續性較好,從業經驗也更豐富,從而聲譽越高。
聯合投資(syndicate):界定所有投資輪次中有兩家及以上創投投資取1,否則為0。不同創投機構具有不同的信息、資源和技能,通過聯合投資,可以在選擇投資項目時提供互補信息,減少逆向選擇問題;投資后則可以在監督和提供管理增值服務方面發揮各自不同的資源和技能優勢,提高企業價值,從而有助于創投機構IPO退出回報。
投資地理距離(investment_distance):領投創投機構所在地和被投資企業注冊地所在城市地理距離(公里)的自然對數。創投距離被投資企業地理距離越近,監督和溝通成本越低,可以實施更緊密的監督,更有效地提供管理咨詢建議,有利于提高創投機構IPO退出回報。
創投機構所在地域(VC_address):虛擬變量,領投創投機構注冊地在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和浙江取1,其余為0。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和浙江既是我國經濟最發達地區,也是創投機構和創業企業聚集最密集的區域,廣泛的資源和發達的網絡關系應該更有利于創投機構開展業務,其退出回報也應較高。
投資期限(investment_time):領投創投機構投資日期距公司IPO上市時的年數。我國創投市場中存在企業IPO之前“突擊入股”現象,此類Pre-IPO投資目的只是為了獲取企業上市時價格差異帶來的投機收益,創投機構既缺乏時間也缺乏動機提供增值服務,其退出回報應該較低。
投資輪次(rounds):IPO公司上市前被創投機構在不同時點投資次數。Tian[10]發現投資輪次越多,VC監督頻率越高,監督強度越大;Lerner[11]則認為后期輪次的參與更多是搭便車行為。由于信用不健全,中國市場上的創投可能需要更頻繁的監督被投資企業;另一方面,中國創投市場近幾年也存在過熱現象,眾多缺乏經驗的創投利用各種關系先后投資入股擬上市企業,這些創投機構可能缺乏管理能力。因此,投資輪次數的影響需要實證檢驗來具體判定。
(2)IPO公司的特征因素
終極控制人控制權比例(controller_shareholding):追溯到IPO公司最終控制人的金字塔結構持股比例之和。最終控制人的控制權有負的“侵占效應”,會損害公司價值。控制權越大,公司價值越低,創業投資IPO退出回報也應較低。
IPO公司住址(firm_adress):虛擬變量,公司總部所在地為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和浙江取1,否則為0。經濟越發達地區,優秀企業越多;企業素質更好,競爭力更強,企業價值更高,創業投資IPO退出回報也應較高。
銷售增長率(sales_growth):(上市前一期營業收入-上市前兩期營業收入)/上市前兩期營業收入。銷售增長率越高,公司成長性越好,投資者會給予更高的估值,從而有利于創業投資IPO退出回報。
凈資產收益率(ROE):招股說明書披露上市前一期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財務績效越好,企業市場價值也應越高,創業投資IPO退出回報也應較高。
創新度:以企業上市前科技研發員工所占比例(technical_employee)作為度量企業創新度的代理變量。科技研發員工占比越高,企業的創新性應該越強,未來成長性越好,企業價值越高,創業投資IPO退出回報也應較高。
除此之外,對公司規模(firm_size)、年齡(firm_age)、資產負債率(leverage)、董事會規模(director_number)、所屬行業(industry)、上市年度(years)和上市板塊(board)也進行了控制。
(二)模型設定
本文研究創業投資IPO退出回報及其影響因素,根據題意,所設定的回歸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multiples是創業投資IPO退出回報倍數;創投特征變量包括領投創投機構性質、領投創投機構持股比例、創投董事占比、領投創投機構聲譽、是否聯合投資、領投創投機構投資地理距離、領投創投機構所在地域、領投創投機構投資距IPO時間長度、投資輪次數;公司特征變量包括終極控制人控制權比例、公司住址、銷售增長率、凈資產收益率、科技研發員工所占比例;控制變量包括公司規模、年齡、資產負債率、董事會規模、所屬行業、上市年度和上市板塊。
三、樣本選擇與描述性統計
(一)樣本選擇
本文從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和金融界等網站獲取深滬兩市截至2016年所有IPO公司招股文件,以考察公司IPO前是否有創投機構參股。創投機構是指名稱中含有“創業投資”“風險投資”“創新投資”“高科技投資”“股權投資”等字樣的機構;有些機構名稱中雖然沒有體現上述內容,但如在招股說明書中披露其業務范圍包括創業(風險)投資、高新技術投資等內容,也被視為創投機構。通過逐一閱覽IPO公司招股文件,發現最早有創投參股的IPO年份為1996年。最終確認的研究樣本為1996—2016年有創投參與的749家IPO公司,其中滬市135家,深市614家。創投機構的特征數據手工收集于IPO公司招股文件,其余變量來自國泰安中國上市公司首次公開發行數據庫。
(二)描述性統計
表1是主要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統計分析表明,投資回報倍數的均值為16.73,意味著創投從投資至IPO退出平均可獲得16.73倍的回報,最大值為411.08,最小值為1.20,說明最高回報超過投入金額的400倍,最低回報僅帶來了20%的增值收益;國有創投機構領投的IPO樣本占比33%,民營創投機構占比60%,外資創投機構僅占比7%;領投創投機構上市后持股比例平均為7.43%;創投機構在董事會占比平均為10.63%;領投創投機構平均資產規模為12.61億元,但中值只有2.36億元,說明有少數創投機構管理資產規模遠大于絕大多數機構;領投創投機構投資公司時年齡平均為3.19年,中值則只有1.24年,說明大多數都是比較年輕的投資機構;聯合投資較為普遍,60%的樣本公司存在聯合投資現象;領投創投機構辦公所在地距IPO企業住所城市平均為969.11公里;74%的領投創投機構辦公所在地在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和浙江這些經濟發達地區,說明中國市場也存在集聚現象,類似于美國創投機構主要集中于硅谷等地區;領投創投機構投資距公司IPO時間平均為3.18年;IPO公司上市前平均有1.53輪次投資。創投投資企業最終控制人控制權比例平均為58.42%,意味著IPO時最終控制人平均處于絕對控制地位;60%的樣本公司來自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和浙江等經濟發達地區,說明這些地區優質企業資源較為豐富,導致在IPO公司中占了很大比重;樣本公司上市前一期銷售增長率為35.73%,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為31.58%,說明創投參股IPO公司成長性和財務績效均較好;樣本公司研發技術人員平均占比21.65%,公司上市前總資產規模平均為35.82億元;從開始營業到IPO平均為15.76年;上市前資產負債率平均為45.62%;董事會平均人數為9.07。
四、回歸分析及穩健性檢驗
(一)回歸結果與分析
表2是回歸結果。模型1是在控制了公司規模、年齡、資產負債率、董事會規模、行業、上市年度和板塊之后,針對創投特征因素的檢驗結果。回歸結果表明,國有、民營和外資創投在IPO退出回報方面沒有顯著差異。國有創投雖然存在激勵約束機制不健全、目標多元化等弊端,但也具備政府和信用等多方面的資源優勢;民營創投存在發展歷史較短,信用水平較低和機會主義行為的缺陷,但具有機制靈活、市場化水平較高的優點;外資創投從業經驗豐富,人員素質和管理能力較高,但可能缺乏資源優勢和對中國本地市場的深刻理解;三種類型的創投各有特定優勢和不足,相互抵消后產生了沒有差異的結果。領投創投機構持股比例與回報倍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持股比例高的確促使創投更加積極地介入公司管理增值服務過程之中,提高了IPO退出回報。創投占董事會比例與回報倍數不相關,且系數符號為負,與預期并不一致;可能原因在于其占董事會比例低導致較小的投票權不足以影響董事會決策結果,另外一般情況下創投董事要同時負責多個投資項目,不可能將全部精力放到一家企業的管理活動當中,也影響了其董事會參與的效果。創投管理資產規模和回報倍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在中國市場創投規模不具有聲譽效應。創投年齡的系數也不顯著,同樣也說明不具有聲譽效應。聯合投資的系數為負但不顯著,說明在中國市場聯合投資不能夠產生信息和資源互補以及共同治理的效果,反而可能因為惡性競爭帶來了負面影響。投資地理距離和創投所在地域的系數符號符合預期,但均不顯著。創投投資距IPO時間與回報倍數顯著正相關,說明投資時間越長,回報倍數越高;投資時間越長,創投對企業管理的介入程度越深,有利于提升企業價值,從而提高退出回報。投資輪次數的系數為正且不顯著,可能表明監督強度和搭便車兩種行為的結果相互抵消,導致多輪投資并不顯著影響退出回報。
模型2則是在控制了相關變量后,單獨針對公司特征因素的檢驗結果。最終控制人控制權比例在1%的水平上與回報倍數顯著負相關,與預期一致;說明最終控制人控制權比例越大,創投的退出回報越低;最終控制人擁有較高控制權時對公司的控制力更強,在與創投談判時會占據更大優勢,從而提高了創投的投資成本,降低其投資回報。公司住址系數為正但不顯著,說明公司位于經濟發達地區具有各種資源優勢,但也會因為更激烈的競爭而抵銷了這些優勢。銷售增長率和凈資產收益率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預期一致;企業上市前較好的成長性和盈利水平能夠反映其更高的價值,創投退出回報也會更高。研發技術人員所占比例的系數為正但不顯著,可能表明研發技術人員占比高雖然能夠提升企業創新能力,但由于較高創新能力所帶來的高成長性已經體現在銷售增長率方面,導致其結果不顯著。
模型3是將創投特征因素和公司特征因素納入同一回歸模型的檢驗結果。與模型1和模型2的結論基本一致,唯一的差異是最終控制人控制權比例的系數變為不顯著,但符號仍保持不變。
(二)穩健性檢驗
1.以年度內涵收益率(IRR)作為因變量的檢驗結果
除了投資回報倍數,內涵報酬率也是反映創投盈利水平的一個量化指標。年度內涵報酬率(IRR)是指創投投資至最終退出時點假定凈現值為零時的年度內部收益率。投資回報倍數雖然反映了創投的真實回報水平,但它易受投資期限長短不同的影響;年度IRR消除了投資期限不同的影響,可以使得各個創投的投資回報以年度為單位標準化比較。
表3是以年度IRR作為因變量回歸的結果。與以投資回報倍數作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相比,大多數變量的系數符號都保持不變,但在顯著性方面部分變量有所差異。創投持股比例的系數仍為正,但變為不顯著;創投董事比例的系數仍為負,但變為顯著;創投資產規模的系數仍為負,但變為不顯著;聯合投資的系數仍為負,但在模型1中變為顯著;投資輪次數的系數仍為正,但在模型3中變為顯著;最終控制人控制權比例的系數仍為負,且在模型3中顯著。創投投資距IPO時間這個變量的系數在穩健性回歸模型中變為顯著為負,而非之前的顯著為正;這恰恰反映了IRR和投資回報倍數的界定不同所導致的差異所在,創投投資距IPO時間越短,其投資回報按年度度量越高;而投資回報倍數卻是投資持有時間越長,其最終IPO回報越高。銷售增長率在穩健性檢驗模型中變為不顯著相關,而非之前的顯著正相關;研發技術人員比例的系數在穩健性檢驗的模型3中變為顯著負相關,而非之前的為正且不相關。
2.改變部分自變量的穩健性檢驗
仍以投資回報倍數作為因變量,改變部分自變量來考察回歸結果的穩健性。用創投在董事會人數替代創投董事比例;采取聯合投資的另外一個定義,即任何一輪投資中有兩個及以上VC機構是聯合投資;用本科以上學歷員工比例替代研發科技人員比例,重新回歸的結果基本不變。限于篇幅未報告上述結果。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1996—2016年有創業投資參與的749家IPO公司為樣本,考察了創業投資特征與被投資公司特征對于創投機構退出績效的影響。研究表明,國有、民營和外資創投在IPO退出回報方面沒有顯著差異;領投創投機構持股比例、領投創投機構投資距IPO時間、銷售增長率和凈資產收益率與回報倍數顯著正相關,領投創投機構管理資產規模、最終控制人控制權比例和回報倍數顯著負相關,創投占董事會比例、投資地理距離、投資輪次數、公司所在地等與創投IPO退出績效均不相關。上述研究結論說明發達市場創業投資研究的部分結論在我國尚不適用。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開始引入創業投資以來,歷經30多年的發展,期間經歷多次起伏波折,真正開始快速增長不過十余年的時間。總體而言,我國創業投資行業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行業發展的宏觀環境、政策體系尚不成熟,創業投資機構的業務水平和從業人員素質仍有待提高。創業投資已然成為支持我國創新創業的重要金融力量,未來隨著內外部環境的不斷成熟,我國創業投資行業也必然會取得進一步的規范發展。
【參考文獻】
[1] 劉健鈞.創業投資制度創新論:對“風險投資”范式的檢討[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2] YAEL V H,et al.Whom you know matters:venture capital networks and investment performance[J].Journal of Finance,2007,62(1):251-301.
[3] NAHATA R.Venture capital reputation and investment perform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8,
90(2):127-151.
[4] LINDSEY L.Blurring firm boundaries:the role of venture capital in strategic alliance[J].Journal of Finance,2008,63(3):1137-1168.
[5] Ozmel U,et al.Strategic alliances,venture capital,and exit decisions in early stage high-tech firm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3, 107(3):655-670.
[6] CHEN H,et al.Buy local? The geography of venture capital[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10,67(1):90-102.
[7] 錢蘋,張幃.我國創業投資的回報率及其影響因素[J].經濟研究,2007(5):78-90.
[8] 劉志陽,江曉東.我國創業投資網絡績效研究[J].財經研究,2010(6):58-68.
[9] PEGGY M L,et al. Grandstanding,certification and the underpricing of venture capital backed IPO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4,73(2):375-407.
[10] TIAN XUAN.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venture capital stage financing[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1,101(1):132-159.
[11] LERNER J.The syndication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J].Financial Management,1994,23(3):1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