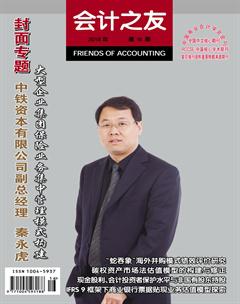“蛇吞象”海外并購模式績效評價研究
苑澤明 顧家伊 富鈺媛
【摘 要】 文章以協同效應理論、技術創新理論和后發企業國際化理論為依據,基于“蛇吞象”并購模式和動機,旨在從企業盈利能力、管理效率、技術創新能力以及國際化水平四個方面構建“蛇吞象”海外并購績效評價體系,并采用縱向案例研究方法,選取吉利集團2009—2016年海外并購事件,對指標評價體系進行應用并得出結論:吉利集團“蛇吞象”海外并購顯著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吉利集團“蛇吞象”海外并購對盈利能力和管理效率無明顯增強作用;吉利集團“蛇吞象”海外并購一定程度上提升企業國際化程度,但波動性較大。
【關鍵詞】 蛇吞象; 海外并購動機; 海外并購績效; 績效評價
【中圖分類號】 F2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8)16-0060-06
一、引言
隨著中國國際化進程的加快,我國海外并購市場風起云涌。根據普華永道2018年報告①顯示,過去5年中,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總交易數量達到2 576宗,累計交易金額高達4 853億美元。報告還顯示,自2010年開始,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目標由資源導向——原材料、能源、礦產等向戰略資產導向——發達國家企業技術和品牌等轉變,并呈現出“蛇吞象”特點,如吉利并購沃爾沃、雙匯并購美國史密斯菲爾德、美的并購德國庫卡等。可以看出,我國企業正在通過并購發達國家企業實現技術與品牌的升級。
已有文獻對海外并購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并購動因和并購績效評價兩個方面。其中并購動因主要包括資源需求(蔣冠宏等,2012)、市場需求(Kolstad et al.,2012)及戰略資產需求(劉青等,2017)等。資源需求動機在我國海外并購初期體現較為突出,占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總金額的40%。而自2010年以來,以獲得技術、品牌和市場份額為目的的海外并購占比高達75%,表明企業海外并購動機向市場及戰略資產需求尋求轉變②。對于并購績效評價方法,主要包括事件研究法(顧露露等,2011;劉瑩等,2017)、會計指標法(樊秀峰等,2014)、平衡計分卡法(劉文炳等,2009)和數據包絡分析法(左曉慧等,2016)等。
現有文獻對并購動因的研究已較為豐富,但在評價并購績效時,大多采用以財務指標為核心的績效評價體系,雖然部分加入非財務績效評價指標,但鮮有研究基于“蛇吞象”并購模式和動因,從戰略資產和市場尋求兩方面選取非財務指標,故對該問題展開探索有助于從理論和實踐角度豐富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績效評價研究。
二、文獻回顧
(一)海外并購動因研究
有關并購動因的研究,西方已形成交易費用理論、市場勢力理論、折中理論、協同效應理論等較為成熟的理論。交易費用理論(Coase,1937)以降低市場交易費用為主要并購動機;市場勢力理論(Comanor,1967)強調企業通過橫向并購達到減少競爭對手,獲得市場壟斷的目的;折中理論(Dunning,1977)從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市場內部化優勢三個方面闡述海外并購動因;協同效應理論(Fred Weston,1990)則認為,企業通過海外并購旨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提升并購雙方效率,主要體現在經營、管理、財務協同效應三個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已有理論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企業海外并購(蘇敬勤等,2013)。以市場勢力理論為例,西方理論較為強調市場壟斷及市場網絡中心地位獲取,而中國作為新興市場國家,企業比較弱化地強調市場領先的并購動機[1]。總結來看,新興國家企業海外并購動機主要為戰略資產尋求和市場尋求。其中戰略資產尋求包括技術尋求[2]及品牌尋求[3]等,較強的戰略資產尋求動機表明中國企業正在將跨國并購作為能力躍升的杠桿,通過并購發達國家目標企業獲取技術、資源和品牌,實現戰略轉型,形成國際競爭力[4]。此外,對海外市場的尋求也是新興市場國家海外并購的主要動機之一[5],我國企業通過海外并購可繞開貿易壁壘,快速進入東道國,有效利用東道國區位條件優勢實現東道國內生產與銷售活動,使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6]。
(二)海外并購績效評價方法研究
海外并購績效評價方法主要有事件研究法、會計指標法、平衡計分卡法及數據包絡分析法(DEA)等。上述方法中,財務指標選取既包括盈利能力、營運能力、償債能力及成長能力等比率指標[7],也包括總資產、主營業務成本、主營業務收入及凈利潤等絕對指標(左曉慧等,2016);非財務指標選取包括股票市場績效指標及戰略績效指標,其中股票市場績效指標有累計超額收益率(CAR)[8]、連續持有超額收益(BHAR)[9]及反常收益率(AR)[10],戰略績效指標有客戶品牌關注度、研發費用、研發技術人員比例及專利數量增長率等[11]。
考慮我國企業“蛇吞象”并購模式主要在于市場尋求和戰略資產尋求兩大動因視角,本文依據協同效應理論、技術創新理論和后發企業國際化理論,構建“蛇吞象”海外并購績效評價指標體系,選取吉利集團2009——2016年海外并購事件,采用縱向案例研究方法,對其海外并購績效進行整體評價。
三、“蛇吞象”企業海外并購模式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一)評價指標構建的理論依據
1.協同效應理論
協同效應[12]指并購后公司收益超過原來兩家收益的總和,主要表現在效率的改進,包括經營、管理、財務協同效應三個方面(Fred Weston,1990)。其中,經營協同效應主要來源于規模與范圍經濟,企業在整合之后成本下降,收益上升;管理協同效應指任何兩個管理能力存在差異的企業并購后,企業績效受到擁有更優秀管理經驗的企業影響,整體管理效率得以提升;財務協同來源于并購后企業規模的擴大而帶來舉債能力的提高、資本成本的降低(Larsson,1990)等。
結合“蛇吞象”模式下戰略資產尋求動機,就經營協同效應而言,我國企業通過并購獲取目標企業先進的技術和廣闊的營銷渠道優勢,并與自身產能優勢相結合,實現在全球范圍內生產要素的最有效配置和資源的高效利用,從而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盈利能力,產生經營協同效應。就管理協同效應而言,我國企業通過學習發達國家企業優秀管理經驗,使得企業整體管理效率得到提升。財務協同效應并不完全適用我國企業海外并購模式,“蛇吞象”模式可看作是一項海外戰略資產投資行為,旨在消化吸收發達國家企業先進技術從而實現自身戰略升級,而不是為了獲取較低成本的外部融資及提升資金實力。因此,協同效應理論下的經營協同效應、管理協同效應為“蛇吞象”海外并購績效指標體系中的盈利能力、管理效率指標選取提供了理論基礎。
依據協同效應理論,“蛇吞象”海外并購模式下的經營協同效應主要體現在通過并購雙方優勢互補達到生產成本的降低,盈利能力的提高;管理協同效應體現為管理效率的提升。因此本文結合現有研究,選取總資產收益率(胡海青等,2016)、銷售毛利率(何璐玲,2018)指標評價“蛇吞象”并購的盈利能力;選取管理費用率衡量其管理效率。
2.技術創新理論
經濟學中,“創新”概念由美籍經濟學家熊彼特[13]于1912年首次提出,即建立新的生產函數,實現生產要素與生產條件的新結合,并將其引入新的生產體系,以獲取潛在利潤。熊彼特所界定的“創新”概念包含了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工藝創新、市場創新和組織制度創新等廣泛內容。其中,技術創新是生產力水平提升的重要來源(Solow R,1957),并成為經濟發展的內在因素(Romer P M,1986)。20世紀90年代之后,企業的技術創新模式逐漸發生轉變,以往傳統的封閉創新模式逐漸顯現出自身的局限性,跨組織合作的開放創新模式得到推崇[14]。2003年,切斯布魯夫[15]提出開放創新的概念,指出應有效地利用外部的互補性資源,并對內外部資源進行整合以進行技術創新。
“蛇吞象”模式下的海外并購是尋求外部技術等創新資產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符合技術創新理論中開放創新的理念。對于缺乏核心技術和品牌影響力的新興企業來說,通過“蛇吞象”的并購方式獲取外部技術等戰略性資產可以快速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故技術創新理論為“蛇吞象”模式海外并購績效評價中技術創新水平指標選取奠定了理論基礎。
依據技術創新理論,技術創新能力是指企業依靠技術創新推動企業發展的能力[16]。在企業并購中,可將其理解為并購企業通過引入目標企業先進技術,使自身產品滿足或創造市場需求,提升自身創新水平。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通常從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兩個角度展開。其中,技術創新投入指標主要包括研發費用率、科技人員比例等[17],技術創新產出指標主要有新產品銷售收入比例、企業新申請發明專利數[18]、技術型無形資產比重[19]等。結合“蛇吞象”并購模式下戰略資產尋求動機,中國企業通過獲取發達國家先進技術與品牌后,需要采取一系列整合措施進行吸收學習,最終將外部獲取的優勢資產內化為自身創新能力的提升。其中對技術的吸收學習過程需要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力度,而創新能力的提升反映為創新產出的增多,故本文采用研發費用率衡量“蛇吞象”海外并購績效評價中技術創新投入力度,用新申請專利數和技術型無形資產比重指標評價其技術創新能力的產出情況。
3.后發企業國際化理論
后發企業是指面臨技術和市場雙重劣勢,通過快速學習克服劣勢,以追趕為目的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后發企業的國際化過程更多的是通過組織變革和戰略變革在國際市場上確立優勢地位,提升國際競爭能力(Mathews,2006)。其中,組織變革包括國際化人才的引進及組織文化多元化等,旨在高效整合目標企業優秀的管理經驗與文化理念,進而提升后發企業的管理效率。戰略變革指后發企業通過并購發達國家企業先進技術等,實現自身戰略由成本領先向技術領先的轉型升級,從而提升核心競爭力。后發企業國際化的目的則是將國際擴張作為跳板,用來獲取戰略資源和減少市場約束,以彌補自身競爭弱點,克服后發劣勢[20]。
結合“蛇吞象”并購模式下市場尋求動機,由于并購方存在品牌劣勢,通過并購發達國家品牌,可幫助企業的自有品牌打破目標企業所在地所設置的政治及貿易壁壘,從而促進在全球范圍內的快速發展,加速國際化進程[21]。因此,后發企業國際化理論為“蛇吞象”海外并購績效評價中國際化程度的指標選取提供了理論依據。
依據上述理論,后發企業的國際化行為旨在獲取先進技術與開拓海外新市場,以彌補后來者劣勢。目前對企業國際化程度常用的測算方法有Sullivan五因素模型、Welch和Luostarinen六要素模型、跨國指數等,其中跨國指數因簡單便捷而最為常用[22]。本文借鑒已有研究,采用跨國指數③指標衡量“蛇吞象”海外并購績效評價體系中的國際化程度。
(二)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本文依據協同效應理論、技術創新理論和后發企業國際化理論,結合我國“蛇吞象”模式下戰略資產尋求以及市場尋求這兩大并購動機,從盈利能力、管理效率、技術創新能力和國際化水平四個方面構建海外并購績效綜合評價指標評價體系,如表1所示。
(三)評價方法
本文采用財務與非財務指標相結合的指標評價法。在具體數據分析方面,本文通過縱向比較分析法,挖掘吉利集團2009—2016年“蛇吞象”海外并購數據,發現各指標并購后的變化趨勢,旨在檢驗“蛇吞象”海外并購績效效果。
四、“蛇吞象”海外并購績效指標評價體系應用
(一)案例選擇
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吉利集團”)于1997年進入轎車領域,旗下擁有沃爾沃汽車、吉利汽車、領克汽車、Polestar、寶騰汽車、路特斯汽車、倫敦電動汽車、遠程新能源商用車等汽車品牌。2008—2016年,吉利集團的銷售量年均增長達到23%。2017年總銷售量達124.8萬輛,同比增長約為50%,位列中國汽車品牌的第六位,民營汽車品牌的第一位。吉利集團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企業迅速發展成為連續5年進入世界500強的跨國集團,其海外并購戰略在其中功不可沒:2006年收購百年車企——英國錳銅19.97%的股份,并建立合資企業,助力吉利集團進入出租車行業并實現中國生產、英國銷售的國際化產銷模式;2009年,收購全球第二大變速器制造商——澳大利亞DSI自動變速器公司,使得吉利集團在自動變速器生產制造中走在了行業前列,完善了產品戰略;2010年,以18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世界高端車品牌沃爾沃轎車100%股權及相關資產,進一步提升了自身技術水平與品牌地位;2013年增資英國錳銅至100%的股權,掌握該企業所有的市場和核心技術;2017年,吉利集團再次出手,一舉收購馬來西亞寶騰49.9%的股份以及英國路特斯51%的股權,加快了國際化進程;2018年,吉利集團再次斥巨資收購德國戴姆勒公司9.69%的股權并成為第一大股東,試圖與其展開新能源汽車方面的合作,提升自身研發能力和品牌競爭力。吉利數次海外并購均屬于“蛇吞象”模式的并購,所選目標企業均具有較強的技術優勢,且在當地乃至全球范圍內具有深遠的品牌影響力,折射出吉利集團旨在通過海外并購實現技術和市場跳躍發展的戰略動機。可見,本文選擇吉利集團作為研究樣本具有典型性。
(二)數據來源
本文以2009年吉利集團并購澳大利亞DSI公司為起點,以2016年作為其“蛇吞象”并購的終點,選取相關數據,對上文構建的“蛇吞象”海外并購績效評價指標體系進行應用。本文所涉及財務數據均來自于Wind數據庫、吉利控股集團2011—2016年年報及債券評級報告;非財務數據來自于吉利汽車官方網站、專利檢索及分析網站、中國企業聯合會網站及公司社會責任報告等。
(三)“蛇吞象”海外并購績效評價
1.盈利能力評價
如圖1所示,吉利集團銷售毛利率在2009—2013年持續下降,說明其間海外并購事件并未帶來明顯的規模效應,2013年之后,該指標有所提升,但2016年基本與并購初年持平,無明顯提高。總資產收益率在2009—2012年波動較大,2012年之后觸底反彈,呈現平穩上升趨勢。結合其并購事件發現,集團于2010年并購沃爾沃,其總資產收益率超高增長正是由于此項并購為集團帶來110.84億元并購折價而導致營業外收入大幅上升,最終使得吉利集團凈利潤實現超高增長。而在并購沃爾沃之后的兩年,集團盈利能力呈現下降趨勢。一方面,受優惠購車政策退出、油價持續上漲和國內貨幣政策等因素影響,我國汽車行業快速發展勢頭有所減緩,吉利集團的盈利能力受到一定影響;另一方面,并購沃爾沃后的整合風險開始顯現,主要表現為管理費用大幅提升,因此,并購后兩年內,總資產收益率的下滑反映并購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集團的盈利能力。不過,2012年之后,隨著沃爾沃與吉利實施零部件聯合采購策略,集團整體成本控制效果顯著,經營協同效應不斷顯現,集團盈利能力出現平穩上升趨勢。長遠來看,在吉利集團近8年海外并購歷程中,整體盈利能力有所提升,但提升效果并不明顯,基本與2009年持平,這說明數次海外并購并沒有為其帶來明顯的經營協同效應。
2.管理效率評價
如圖2所示,2009—2016年,吉利集團的管理費用率基本維持在6%~8%之間,2010、2011兩年上升明顯,時值吉利并購沃爾沃初期,并購后的整合工作需要耗費較多的管理費用。之后,管理費用率維持在8%左右,無較大變化。因此,從該指標上看,數次海外并購事件并未提高吉利集團的管理效率,其需要進一步優化并購整合策略,學習吸收目標企業先進管理經驗,從而整體提升自身管理效率。
3.技術創新能力評價
(1)研發投入力度④
為排除國家政策等外在因素對該指標的影響,本文選取長安汽車、比亞迪與吉利集團進行對比,二者與吉利同為我國自主品牌車企,且實力相當,但在2011—2016年間未發生“蛇吞象”海外并購事件。如圖3所示,從總體來看,長安汽車與比亞迪研發投入占比均呈下降趨勢,而吉利與這兩大車企相反,在2013年,研發投入力度超過長安汽車,又在2015年一舉超越比亞迪,研發投入占比總體呈上升趨勢,從2011年5.17%上升為2016年6.83%。這說明,吉利集團通過三次“蛇吞象”海外并購事件后,不斷獲取海外先進技術,同時也加大自身研發投入進行技術整合,從而實現后發企業技術追趕。近年來,吉利頻繁在世界范圍內設立研發中心,包括吉利英國研發中心、吉利歐洲研發中心(CEVT)、吉利(杭州灣)研發中心等,這也表明了其對研發投入的高度重視。其中吉利英國研發中心是由英國錳銅位于考文垂的工廠改造,其目的在于消化吸收來自英國錳銅的成熟技術與造車經驗,并用于自身的商用車生產;歐洲研發中心(CEVT)是吉利與沃爾沃聯合開發的研發中心,其目的在于加強與沃爾沃的技術溝通,高效完成與沃爾沃的技術整合。總體來看,吉利集團在一系列“蛇吞象”海外并購之后,對自身研發能力的重視度大大提升,有利于自身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
(2)技術創新成果
圖4描述了吉利集團2009—2016年新增專利數的變化趨勢。其2016年新增專利數高達1 301項,約為2009年專利產出的5倍。進一步分析其無形資產構成,如圖5所示,技術性無形資產(包括專利權、非專利技術和專有技術)占無形資產總額也呈現大幅上升趨勢,由2009年的37%提升為2016年的65%,由此看來,在不斷消化吸收海外先進技術的基礎上,吉利集團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不斷增強。綜上所述,經過近9年海外并購之路,吉利集團技術創新能力通過獲取國外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實現改進提高這一路徑得以形成,數次海外并購提升了其技術創新能力。
4.國際化程度
近年來,在一系列海外并購之后,吉利集團通過采取合資或合作建廠等靈活多樣的商業模式,大力發展海外業務。2009—2013年,其海外目標市場主要包括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斯坦,以及位于中東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位于南美洲的巴西、烏拉圭、巴拉圭和智利等。從2013年開始,吉利汽車為進入歐美市場進行全面布局,包括CMA中級車模塊化架構研發、歐美市場競爭對手研究、歐美市場消費者偏好研究以及歐盟26國的先后進入順序調研等。
2011年,中國企業聯合會首次發布中國100大跨國品牌跨國指數,以此評價中國跨國品牌國際化水平。從其發布的結果來看,吉利集團跨國指數歷年來均位居榜首,遠遠高于平均水平(13%左右)。如圖6,與其自身比較而言,吉利集團在經歷連續四年上升之后,自2015年開始呈現下降趨勢。究其原因,由于本集團若干主要出口市場的政治及經濟環境不穩,且新興市場貨幣兌美元及人民幣走弱,該市場的汽車需求大幅放緩,導致集團海外收入連年下降。總的來看,吉利數次海外并購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品牌的國際化水平,但發展波動性較大,吉利集團應采取相關措施規避海外風險,穩步提升自身國際化程度。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從“蛇吞象”海外并購動因入手,依據協同效應理論選取戰略資產尋求動機下盈利能力評價指標和管理效率指標,依據技術創新理論選取戰略資產尋求動機下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依據后發企業國際化理論選取市場尋求動機下的國際化程度評價指標,并據此構建“蛇吞象”海外并購績效指標評價體系,最終選取吉利集團2009—2016年數次海外并購案例,將上文構建的績效評價體系進行應用,得出以下結論:(1)數次“蛇吞象”海外并購對吉利集團技術創新能力提升效果最為顯著;(2)盈利能力和管理效率無明顯增強;(3)企業國際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但波動性較大。
區別于過去以財務指標為主的評價方法,本文指出缺乏技術優勢的新興企業之所以不惜重金收購發達國家目標企業,看中的正是這些企業所擁有的技術、品牌和市場優勢,因而在評價類似并購模式時,針對并購動機選取指標更能準確、全面地評價其并購績效。此外,吉利海外并購這一成功案例為我國新興企業海外并購有一定借鑒作用:一方面,我國企業應積極推進國際化戰略,適時通過“蛇吞象”并購模式獲取海外先進技術與品牌,以克服后來者劣勢,提升自身能力基礎;另一方面,我國企業應加大研發投入,積極消化吸收海外資源,將其內化為自身核心競爭力的提高,以加快技術追趕。
本文仍存在諸多局限性,比如:由于受中國企業跨國并購動機的影響,本文構建的“蛇吞象”海外并購績效評價體系可能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只能提供一個全面評價“蛇吞象”并購績效的思路,未來可關注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企業“蛇吞象”海外并購,通過比較研究,相互印證,推動發展中國家海外并購績效評價方法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蘇敬勤,劉靜.中國企業并購潮動機研究——基于西方理論與中國企業的對比[J].南開管理評論,2013(2):62.
[2] MATHEWS J A.Dragon multinationals:new players in 21st century globalization[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6,23(2):139-141.
[3] 郭銳,陶嵐,汪濤,等.民族品牌跨國并購后的品牌戰略研究——弱勢品牌視角[J].南開管理評論,2012,15(3):42-50.
[4] 吳先明,蘇志文.將跨國并購作為技術追趕的杠桿:動態能力視角[J].管理世界,2014(4):146-164.
[5] 劉青,陶攀,洪俊杰.中國海外并購的動因研究——基于廣延邊際與集約邊際的視角[J].經濟研究,2017,52(1):28-43.
[6] 廖東聲,劉曦.中國制造業企業海外并購問題研究[J].會計之友,2017(2):44-47.
[7] 胡海青,吳田,張瑯,等.基于協同效應的海外并購績效研究——以吉利汽車并購沃爾沃為例[J].管理案例研究與評論,2016,9(6):531-549.
[8] 顧露露,Robert Reed.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失敗了嗎?[J].經濟研究,2011,46(7):116-129.
[9] 林季紅,劉瑩.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績效研究——以并購整合為視角[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6):115-124.
[10] 馮梅,鄭紫夫.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績效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2016(1):93-100.
[11] 劉文炳,張穎,張金鑫.并購戰略績效評價研究——基于聯想并購IBM PC業務的案例分析[J].生產力研究,2009(14):92-93,101.
[12] ANSOFF H.Corporate Strategy[M].NY:McGraw-Hill,1965.
[13] SCHUMPETER J A.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credit,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M].New Brunswick (U.S.A),London(U.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34.
[14] 倪自銀,劉強.開放創新模式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研究[J].軟科學,2013(10):59-63.
[15] CHESBROUGH H W.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 [M].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03.
[16] 支軍,王忠輝.自主創新能力測度理論與評估指標體系構建[J].管理世界,2007(5):168.
[17] 崔總合,楊梅.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2,29(7):139-141.
[18] 徐立平,姜向榮,尹.企業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科研管理,2015,36(S1):122-126.
[19] 苑澤明,金宇,王天培.上市公司無形資產評價指數研究——基于創業板上市公司的實證檢驗[J].會計研究,2015(5):72-79,95.
[20] LUO Y D,TUNG R L.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a springboartd perspective [J].Journal of Internationnal Business Studies.2007(29):563-582.
[21] 姚鵬,王新新,靳代平.“蛇吞象”式并購條件下的品牌管理研究述評與展望[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5(2):51-57.
[22] 龐明川.區位變遷、逆向并購與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化成長——以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實踐為例[J].財經問題研究,2012(8):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