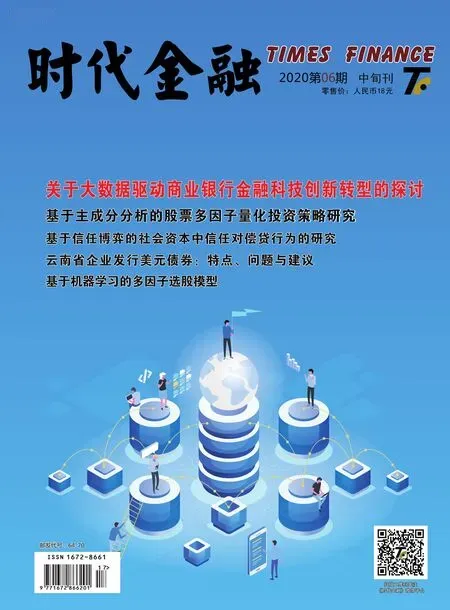證券分析師預測目標價格的動機分析



【摘要】本文運用2006-2011年分析師研報數據,檢驗了分析師預測目標價格的動機。研究發現:聲譽和信號傳遞假說有效解釋了分析師預測目標價格的動機。為了維護既得聲譽,聲譽越高的分析師越不可能披露目標價格;而為了向市場傳遞信號,內在能力越高的分析師越可能披露目標價格。且聲譽與內在能力對分析師是否報告目標價格的行為決策具有交互作用,分析師的對低(高)聲譽分析師預測目標價格的可能性有(無)顯著的正向影響。
【關鍵詞】分析師 目標價格預測 聲譽 信號傳遞
一、引言
我們通常假定,分析師是在價值評估的基礎上對股票進行評級的,價值評估的直接產品是目標價格,根據目標價格與當前交易價格的差異形成股票的評級。如:“買入”或“推薦”評級可認為該股票的價值被低估;“持有”評級說明當前價格比較合適;“賣出”或“減持”評級代表股票價值被高估(Bradshaw,2002)。早期,證券分析師僅披露盈利預測與投資評級,并不報告目標價格。美國從1996年末開始有分析師報告目標價格(Brav and Levary,2003),我國從2006年初開始有分析師報告目標價格,且報告的比例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Brav與Lehavy(2003)、Asquith,Mikhail與Au(2004)的研究發現即使在控制了同期的盈利預測調整與評級調整后,市場對目標價格調整也有顯著的市場反應;Huang與Mian,et al.(2009)發現綜合一致評級調整與一致目標價格調整設立的投資組合收益高于單獨以二者設立的投資組合收益。Da與Schaumburg(2011)發現根據行業內分析師一致目標價格的高低進行投資組合可以獲得超額收益。這些研究表明目標價格在盈利預測與薦股評級之外提供了增量信息,是有價值的信息。然而,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盡管幾乎所有分析師都會在研究報告中披露評級,卻不一定報告目標價格預測。分析師選擇報告或不報告目標價格其背后的動機是什么?以上這些從美國資本市場得到的研究結論在中國成立嗎?
本文基于聲譽與信號傳遞的理論假說,研究了分析師額外報告目標價格的動機。我們對2006-2011年分析師評級報告的大樣本數據進行了研究,發現:高內在能力的分析師與低聲譽的分析師更可能報告目標價格;低聲譽的分析師內在能力越高越可能報告目標價格;高聲譽的分析師,內在能力與分析師報告目標價格的可能性沒有顯著的聯系。
本章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相關文獻回顧,第三部分為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第四部分介紹研究設計,第五部分報告主要的實證結果,最后是結論。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分析師的行為動機既可以從理性的角度進行解釋,也可以從非理性的角度進行解釋。理性的解釋主要是建立在分析師的理性預期、風險回避、效用最大化以及相機抉擇等假設基礎上對其預測行為的動機進行解釋,非理性的解釋主要是從認識偏差、決策偏差等角度進行解釋。第一,理性方面的解釋認為分析師出于對自身利益的關注,其預測行為會受到利益沖突、聲譽的影響。一方面,分析師面臨的利益沖突會導致過度樂觀的預測行為(Michaely and Womack,1999;原紅旗,黃傅茹,2007;Gu,Z.,Z.Li and Y.G. Yang,2009)。另一方面,分析師出于對自身職業生涯或聲譽的關注,過度樂觀的機會主義行為會受到抑制(Jackson,2005;Fang and Yasuda,2004;Ljungqvist et al.,2006),進而提高預測的準確度;但是,分析師維護既得聲譽的動機會導致分析師的從眾行為,進而降低預測準確度(Bikhchandani et al.,1999;Hong,Kubik and Solomon,2000)。此外,分析師的預測行為還會受到個人特征的影響。歷史預測越準確、供職于大的券商、頻繁預測的分析師傾向于發表大膽的預測(Clement and Tse,2005)。過去的表現比較差或比較好時,更可能做出大膽的預測(Clarke and Surbramanian,2006)。第二,非理性的解釋認為分析師的過度自信、代表性偏差或情緒等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可以解釋分析師的過度樂觀行為(Easterwood and Nutt,1999;Jegadeesh et al.,2004;伍燕然,2007)。對分析師預測目標價格的動機,本文主要從理性解釋的角度,基于信號傳遞假說與聲譽假說研究分析師目標價格預測的動機。
(一)信號傳遞假說
在資本市場上,分析師每天發布大量的投資評級報告,不同分析師受到的激勵與內在能力不同,導致投資評級的質量差異很大,面對大量的投資評級報告,市場上的投資者往往難以區分不同分析師投資評級的質量。根據信號傳遞理論,信息優勢方會主動提供信息給信息劣勢方,從而形成市場交易機會。因此,對于投資者來說,一個簡單的區分方法是觀察分析師評級報告的方式,這將極大地減小投資者的信息搜尋成本。所以額外報告目標價格就成為分析師向市場傳遞信號的一種方式。然而,根據信號傳遞理論,信號傳遞可信的前提是不可以被模仿,或模仿的成本很高(張維迎,1996)。所以高內在能力的分析師更有動機通過額外報告目標價格把其高質量的信號傳遞給市場,而低內在能力的分析師報告目標價格的動機更小,因為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一方面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另一方面一旦目標價格預測偏差過大,將損害自身的聲譽。因此,如果信號傳遞假說成立的話,額外報告目標價格可以傳遞高質量的信息,內在能力越高的分析師,越可能通過額外報告目標價格預測。我們提出假設1:
假設1:內在能力越高的分析師,越可能(在投資評級報告之外額外)報告目標價格預測,反之則反是。
(二)聲譽假說
聲譽機制能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Fama,1980),從而使聲譽成為一項重要的無形資產(Kreps,1996;Tadelis,1999)。高聲譽的分析師市場影響力更大(Stickel,1992;Jackson,2005),且擁有可觀的薪酬和美好的職業前景(Hong and Kubik,2003;Fang and Yasuda,2004)。因此,分析師有建立和維護聲譽的動機。聲譽的建立往往需要通過信號傳遞來實現,低聲譽的分析師基于建立聲譽的考慮,更有動機通過預測目標價格向市場傳遞信號,增加自己在市場中的可見性,并提升行業地位及知名度;而高聲譽的分析師,基于維護聲譽的考慮,額外報告目標價格的動機更小。這是因為高聲譽的分析師已經擁有了較大的顧客基礎和市場影響力,內在能力已經得到了市場的認可,為了維護聲譽,高聲譽的分析師行為更加謹慎(Bikhchandani et al.,1999),而額外報告目標價格本身就是一種大膽的預測行為,因為公司未來的股價不僅受公司盈余狀況的影響,還會受到公司潛在的風險、行業發展趨勢、社會宏觀經濟等因素的影響,目標價格難以預測,一旦預測的偏差過大,可能付出高昂的聲譽代價。基于聲譽建立與維護的假說,我們提出研究假設2:
假設2:低聲譽分析師,通過報告目標價格預測向市場傳遞信號的動機更強,反之則反是。
如果說建立抑或維護聲譽是分析師是否選擇報告目標價格傳遞信號的主觀動因,那么內在能力就是決定分析師是否報告目標價格傳遞信號的客觀動因。因此聲譽與內在能力對分析師是否報告目標價格的行為決策具有交互作用。基于以上分析,進一步提出假設3:
假設3:內在能力對低聲譽分析師報告目標價格的可能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對于高聲譽分析師沒有顯著的影響。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模型
為了檢驗我們的假設,在借鑒以往文獻(Keung,2010;Marks,2008;Francis and Soffer,1997)的基礎上,我們建立了模型(1):
■(1)
模型(1)采用Logistic回歸。其中:Dis為投資評級的同時是否報告目標價格預測的啞變量;P(Disijt=1)表示分析師報告目標價格預測的概率;Ability為分析師能力指標。借鑒郭杰、洪潔瑛(2009)的做法,采用Ability(Dir)與Ability(Beat)衡量分析師的真實能力。前者為分析師基于已觀測到的市場共識,自身的盈利預測朝著公司真實盈利移動的頻率。后者為分析師預測比市場共識更加準確的頻率。具體的計算如方程(2)與(3):
■ (2)
■ (3)
其中,sign表示括號項的符號,■是為公司j的市場一致預測誤差的絕對值(市場一致預測的每股收益—實際每股收益),■為分析師i的預測誤差的絕對值(分析師預測的每股收益—實際每股收益)。Devi,j,t是分析師預測的每股收益與市場一致預測每股收益的差;Ni,j指分析師i對公司j的可驗證的預測次數。Ability(Dir)與Ability(Beat)均為正指標,取值越大,分析師內在能力越強。股票的價值基礎是其未來的盈利能力,因此,分析師預測目標價格、推薦股票的能力是建立在盈利預測能力基礎上的,因此,我們認為在研究分析師目標價格與薦股行為中使用這兩個指標來衡量分析師的內在能力是合適的。Ability(Dir)與Ability(Beat)這兩個指標顯著地高度正相關,在本章的回歸分析中,我們交替使用二者作為分析師內在能力的指標。
Leader為大規模券商的啞變量;Nfirms_R為分析師專注程度,以分析師跟蹤上市公司的相對數量進行衡量;LnFollow為跟蹤當年上市公司j的分析師人數的自然對數;Firmage為上市公司上市年限;Tobin為托賓值;Loss為t-1年公司j發生虧損的啞變量;Pvol衡量股價波動性;Initial為分析師首次跟進公司j的啞變量。
(二)數據來源
其一,分析師盈利預測、投資評級及目標價格預測的數據均來自RESSET(銳思數據庫)中的中國上市公司分析師預測研究數據庫。其二,上市公司公司財務及股票收益率等數據來自CSMAR(國泰安數據庫)的相關數據庫。其三,歷屆最佳分析師數據來自《新財富》雜志官方網站①。其四,分析師所屬券商總資產排名數據來自中國證券業協會網站每年公布的證券公司會員財務指標排名情況②。
(三)樣本的選擇與描述性統計
最初,從RESSET數據庫,我們獲得了2006-2011年A股上市公司524,273個投資評級樣本。從樣本分布情況來看,報告目標價格的樣本在逐年增加,從2006年至2011年,目標價格預測報告的份數從2,418份增加至24,073份,所覆蓋的公司數從574家增長至1,525家,平均每家公司的目標價格預測份數則由4份增加至16份,提供目標價格預測報告的分析師人數由385人增加至982人。從6年合計數來看:提供目標價格預測的薦股報告為59515份,占總薦股報告份數的11%;報告目標價格預測的分析師共1,862人,所覆蓋的公司合計1,880家。即,樣本中有972名分析師未提供過目標價格預測,344家公司沒有被預測過目標價格。
四、實證結果
表1報告了模型(1)中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有26.3%的分析師報告了目標價格預測;Ability(Dir)與Ability(Beat)的平均值均為正數,且中位數也大于零,數據右偏。32.4%的分析師來自大的券商,明星分析師發布的評級報告占15.9%,有26.3%的樣本為分析師首次跟進。
表2的分組檢驗顯示,額外報告目標價格預測的分析師的平均能力與未報告目標價格預測的分析師有顯著差異。報告目標價格預測的分析師評級報告,更可能來自大券商,更不可能來自明星分析師。
表3報告了影響分析師報告目標價格的因素回歸結果。表3第(1)、第(3)列的結果顯示,Ability(Dir)、Ability(Beat)均與Dis顯著相關,表明內在能力越強的分析師越可能報告目標價格,支持了假設1;Star與Dis顯著負相關,這表明,高聲譽的分析師更不可能報告目標價格預測。Leader與Dis顯著正相關,說明隸屬于大券商的分析師更可能報告目標價格預測,這與供職于大券商的分析師傾向于發表大膽的預測這一結論是一致的(Clement and Tse,2005)。原因可能有:其一,規模大的券商有更好的數據支持與行政支持,分析師進行目標價格預測所需額外花費的精力較小;其二,大券商的分析師更容易接觸他們所跟蹤公司的管理層,從而獲取一些私有信息,這些私有信息有助于分析師形成目標價格預測。
從加入交乘項StarAbility的第(2)、第(4)列結果可以發現,Ability的系數依然顯著為正,交乘項StarAbility的系數不顯著。這表明,低聲譽的分析師,內在能力越高越可能報告目標價格預測,但是內在能力對于高聲譽分析師沒有顯著的影響。非明星分析師基于建立聲譽或職業晉升的考慮,通過額外報告目標價格預測向市場傳遞信號的動機更強,內在能力越高,越可能報告目標價格預測。而已經擁有“明星”頭銜的分析師,基于維護聲譽的考慮,行為謹慎,能力對其是否報告目標價格的影響不明顯。
此外,LnFollow、LnSize與Dis顯著正相關,這表明分析師跟蹤人數越多、規模越大,越可能被報告目標價格預測。分析師跟蹤人數越多,其信息被挖掘得越多、越透明(Lang and Lundholm,1993;Bowen et al.,2008),大規模公司受關注的程度高于小規模公司,公開披露的信息比較多(Morck et al.,2009),因此分析師跟進人數越多的公司、規模越大的公司,分析師生成目標價格預測的成本越低,從而更可能預測其目標價格。Tobin、Pvol與Dis顯著正相關,表明成長性越高、股價波動性越大的公司,越可能被報告目標價格預測。成長性越高、股價波動越大的公司,投資者對其目標價格預測的信息需求越大,因而,分析師更傾向于為這兩類公司預測目標價格。Initial與Dis顯著正相關,表明當年如為分析師首次跟蹤該上市公司,更可能報告目標價格預測,這與信號傳遞假設是一致的,當首次跟進該上市公司時,區別于大多數分析師的預測方式可能是吸引市場投資者關注的一種途徑。Firmage與Dis顯著負相關,表明上市年限越久的公司,越不可能被報告目標價格預測,這也與投資者的需求有關,因為上市年限越久的公司,越為投資者所了解,投資者對目標價格預測的需求更小。Nfirms_R與Dis顯著負相關,跟蹤公司數目越多的分析師,越不可能報告目標價格預測,跟蹤公司數目越多的分析師,對每家所跟進公司傾注的時間和精力就越少,因而越難以生成目標價格預測。
表中采用Logistic回歸方法,參數的估計方法為極大似然法,括號中的值為Z值。*、**、***分別代表0.1、0.05、0.01的顯著性水平。
五、結論
本章基于2006~2011年分析師評級的大樣本數據,檢驗了分析師在投資評級之外額外報告目標價格預測的動機。我們發現:高內在能力、低聲譽的分析師,更可能報告目標價格預測;低聲譽的分析師內在能力越高,越可能報告目標價格預測,而高聲譽的分析師,內在能力對其是否報告目標價格的影響較小。此外,分析師是否報告目標價格預測還受到預測成本、投資者需求、專注程度等因素的影響。隸屬于大券商的分析師更可能報告目標價格,分析師傾向于預測大公司及分析師跟蹤人數更多的公司的目標價格;成長性越高、股價波動性越大的公司也越可能被分析師報告目標價格預測;首次跟進的分析師,報告目標價格預測的可能性越大;跟蹤公司數目越多的分析師,報告目標價格預測的可能性越小。
本文的研究表對分析師及投資者均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分析師可以通過額外報告目標價格預測的方式向市場傳遞高能力的信號并提高自身的市場影響力;投資者也可能通過觀察分析師報告的內容和形式所傳遞的信號獲得更好的短期收益。
注釋
①詳見網址:http://www.xcf.cn/zjfxs/。
②詳見網址:http://www.sac.net.cn/hysj/zqgsyjpm/201106/t2011 0602_11432.html。
參考文獻
[1]Agrawal,A.and M.A.Chen,Analyst conflicts and research quality[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Finance,2012,2(02):1-40.
[2]Asquith,P.,M.B.Mikhail and A.S.Au,Information content of equity analyst report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75(2):245-282.
[3]Bradshaw M.T.The use of target prices to justify sell-side analysts' stock recommendations[J],Accounting Horizons,2002,16(1):27-41.
[4]Brav,A.and R. Lehavy.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nalysts' Target Prices:Short Term.informativeness and Long-term Dynamics[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3,(5):1933-1967.
[5]Clarke,J.and A.Subramanian,Dynamic forecasting behavior by analysts: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2, 2006,80(1):81-113.
[6]Clement,M.B.and S.Y.Tse,Financial analyst characteristics and herding behavior in forecasting[J].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5,60(1):307 -341.
[7]Da Z.,Schaumburg E.Relative valuation and analyst target price forecasts[J],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2011,14(1):161-192.
[8]Hong,H.and J.D.Kubik,Analyzing the analysts:Career concerns and biased earnings forecasts[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3,58(1):313 -351.
[9]Keung,E.C.,Do supplementary sales forecasts increase the credibility of financial analystsearnings forecasts?[J]The Accounting Review,85(6):p.2047-2074.
[10]郭杰與洪潔瑛.中國證券分析師的盈余預測行為有效性研究.經濟研究,2009(11):55-67.
[11]原紅旗與黃倩茹,承銷商分析師與非承銷商分析師預測評級比較研究.中國會計評論,2007(03):285-303.
[12]伍燕然,潘可,胡松明,江婕.行業分析師盈利預測偏差的新解釋.經濟研究,2012(04):149-160.
基金項目: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校級青年聯合基金項目“證券分析師目標價格預測的動機、能力與市場反應”(項目編號:12S11)的資助。
作者簡介:鐘子英(1978-),女,江西贛州人,講師,博士學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會計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資本市場與資產定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