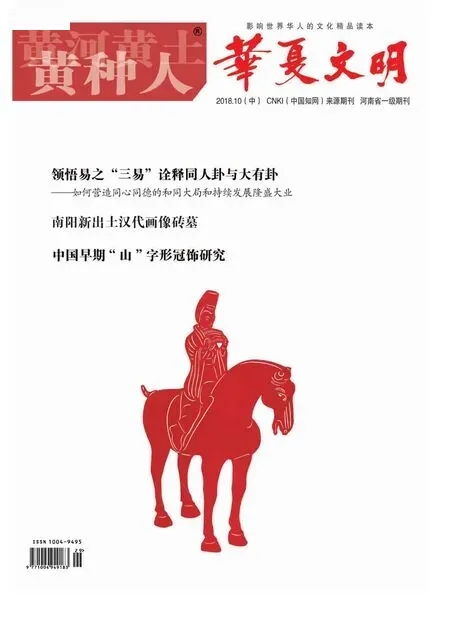馬鞍山地區(qū)出土六朝時期玉石豬手握淺談
□楊彭
馬鞍山市位于安徽省最東部,地接南京,扼守長江,坐擁青山,六朝時便是畿輔之地,歷史上有“金陵屏障、建康鎖鑰”的說法。因其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和戰(zhàn)略地位,王公貴族紛紛選擇在這里下葬。隨著城市基建力度的加大,越來越多的六朝墓葬破土而出,無論是墓葬形制還是出土器物,對研究六朝經(jīng)濟、社會、文化都有著極大的意義。關于馬鞍山地區(qū)的墓葬,很多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過較為詳盡的分析和探討,本文試將馬鞍山六朝墓中具有時代特征的玉石豬手握單列出來,考察、探析其造型演變和現(xiàn)實意義。
一、馬鞍山地區(qū)玉石豬手握出土情況
安徽地區(qū)使用玉石豬手握作為隨葬品的墓葬較少,大多集中在長江中下游的馬鞍山地區(qū),從已發(fā)表的資料看,出土有玉石豬的墓葬共有以下12座:
1976年,馬鞍山東晉(孟府君)墓M1出土 2件。 淺刻線條,呈臥伏狀[1]。
1988年,當涂縣黃山東晉墓M1出土3件。 匍匐狀[2]。
1998年,盆山六朝墓M2出土2件。長方形,匍匐狀。雕刻簡單。長8.5厘米[3]。
2000年,當涂新市來隴村南朝墓群M1出土2件,造型一致,豬呈臥狀,短吻,背部有鬃毛,整體刻畫簡單,通長 6厘米;M3出土1件,豬呈臥狀,長吻,尖耳,背部有鬃毛,刻畫生動,體形較大,通長10.2厘米、高3.2厘米、寬 2.2 厘米[4]。
2001年,馬鞍山市馬鋼花園小區(qū)東晉墓M1出土2件。斷為兩截。呈蹬臥伏。頭部陰刻嘴、眼、耳,兩耳之間陰刻豬毛,脊背中間陰刻兩道平行直線,線外斜刻豬毛,腹部有刻畫符號,后部刻有兩腿,無尾。一件通長7.5厘米、通寬1.3厘米、高1.2厘米。另一件通長7.5 厘米、通寬 1.3 厘米、高 1.2 厘米[5]。
2002年,當涂縣新市鎮(zhèn)東晉楊氏家族墓M1出土2件。造型一致,呈臥狀,拱嘴,睜目,刻畫生動、清晰。一件長8.5厘米、寬1.9厘米,另一件長 8.5 厘米、寬 2.1 厘米[6]。
2002—2003年,當涂青山六朝墓群M23出土6件。M23:14,青綠色玉,腹部為黑色。形體較長,呈趴臥狀,短吻,頭部陰刻出雙耳,圓臀,短尾,下吻部與尾部各有一個穿孔,皆已殘斷。長11厘米、寬2.4厘米、高2.5厘米。M23:15,灰色玉,并有天然紋理。體態(tài)豐腴,呈趴臥狀,短吻,前端鉆有兩個鼻孔,圓雕雙耳,圓臀,長尾下垂,下吻部與尾部各有一個穿孔。長10.8厘米、寬2.5厘米、高3厘米。M23:6,2 件,大小相同。赭灰色,通體光滑。形體瘦長,呈趴臥狀,長吻,吻前端有兩個鼻孔,頭部陰刻出眼、耳,圓臀,長尾下垂。長10厘米、寬 2.1 厘米、高 2.2 厘米。 M23:8,2 件,大小相同。灰白色。形體較短,呈趴臥狀,長吻,吻前端有兩個鼻孔,頭部陰刻出眼,耳為淺浮雕,背部及腿部陰刻豬毛,圓臀,短尾下垂。長8.4 厘米、寬 2.1 厘米、高 2.1 厘米[7]。
1992年,慈湖鄉(xiāng)林里東晉墓M1出土2件,形制大小相同。前腿向前伸直,后腿彎曲,做臥伏式,尖嘴,背上刻鬃毛,頭部刻鼻、眼、耳。 體長 9.4 厘米、高 3 厘米[8]。
2009年,上湖村東晉墓M2出土2件。一面刻畫紋飾。豬呈臥狀,短吻,背部劃有鬃毛,刻畫簡單。兩豬可合二為一。M2:8,長6.8厘米、寬 0.7 厘米、高 1.1 厘米;M2:9,長 6.8 厘米、寬 0.4 厘米、高 1.1 厘米[9]。
通過觀察,可以發(fā)現(xiàn)馬鞍山地區(qū)出土的玉石豬手握造型有一定的演化規(guī)律:西晉末期,雕刻簡單,豬身扁平細長。東晉早期,豬頭低垂,整體呈臥狀,全身圓潤,類細圓筒,刻畫較為簡單,有明顯的“漢八刀”遺風。至東晉中晚期,對器物造型有著更為生動的表現(xiàn),著重表現(xiàn)在后背和腿部豬毛的刻畫上。東晉晚期,又回歸質(zhì)樸,少了細節(jié)的刻畫,僅突出五官、肢體,頭部不變,臀部豐腴。南朝以降,器物整體趨于橢圓,腹背呈桶形,頭部特征逐漸不明顯,臀部渾圓,構造粗糙。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早期玉石豬手握造型精致,藝術性強,隨著時代推移,器形已經(jīng)沒有任何藝術特征,僅存在特定的象征意義。
二、玉石豬手握隨葬的意義
最早的玉石手握,發(fā)現(xiàn)于山東膠州三里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較長時期內(nèi),手握玉石并沒有形成固定的形制,直到西漢葬玉高峰,玉璜向玉豬發(fā)展。西漢后期,玉璜被玉豬替代,直至東漢。六朝開始,滑石豬的使用讓玉豬手握徹底淡出歷史舞臺[10]。滑石為富鎂礦物經(jīng)熱液蝕變而成,顏色多呈淡綠色或者灰白色,因其有硬度較低的特點,適用于制作各種隨葬明器。中國滑石分布廣泛,主要集中在江西、遼寧、山東、廣西、青海等地,安徽產(chǎn)量不是很高。作為隨葬品而制作滑石器,基本是從戰(zhàn)國時期開始的,器形也只有滑石璧一種。漢代呈現(xiàn)一次使用的大發(fā)展,器形囊括了生活、祭祀等多種用具,但到了東漢熱度逐漸下降,六朝的使用也趨于簡化,發(fā)展、并合為滑石豬這種特殊器形。
關于將玉石豬手握作為隨葬品的意義,學術界基本有兩種觀點,一是彰顯墓主的財富[11],二是作為祭祀司命之用[12]。
《漢書·貨殖傳》記載:“澤中千足彘。”《齊民要術》載:“懸臘月豬羊耳,著堂梁上,大富。”由此可見,漢代豬的產(chǎn)量大,養(yǎng)殖數(shù)量可作為衡量家庭殷實程度的重要指標。殷商有將貝幣握于手中下葬的現(xiàn)象,體現(xiàn)了墓主對死后世界財富的依戀。漢至六朝手握物品的墓葬數(shù)目仍然可觀,自然也能夠推出逝者彰顯財富的意味。從馬鞍山地區(qū)出土玉石豬手握的12座墓葬來看,隨葬品為青瓷器和陶器,部分墓葬出土有金、銀、銅器,除已遭施工破壞的,墓長集中在4~8米之間。學術界此前有墓長 4~8 米為中型墓的觀點[5],因此單論墓葬規(guī)模,這批墓等級不低。據(jù)考證,葬制在六朝時期似無嚴格規(guī)定,平民亦能建造前后雙室的中型墓[13],可見墓葬規(guī)模雖能區(qū)分身份高低,但并不能集中體現(xiàn)貧富差距。筆者認為,就全部出土器物數(shù)量而言,玉石豬手握僅作為其他隨葬品的附屬品,財富的彰顯還是要靠對比性強的青瓷器和玉器,對玉石豬手握的理解需更深層次考量,精神層面?zhèn)鬟_出的意義才更符合當時的社會風氣。
作為祭祀司命的資料實證,并且豬還是祭祀中的“上牲”,飼養(yǎng)容易且繁衍簡單,既可滿足百姓的日常食用,也能輕易宰殺祭祀。《禮記·王制》載:“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那時的祭祀,與六朝時最大的區(qū)別就在于禮制跌落神壇,祭祀從集權國家的最高訴求演化成普通人的理想結晶。漢至六朝時期,豬與北斗崇拜有著極為密切的聯(lián)系。《太上玄靈北斗本命長生妙經(jīng)》云:“太上日:天一生水,生自北方,故紫微之垣高崇北辰,北辰之宿列為七元。”天一又稱太乙,即為北斗,在古時天文儀器“圭表”中為“大表”。馮時先生在《中國天文考古學》一書中將紅山文化出土的玉豬龍的象征解釋為“北斗拱極運動而建時的反映”[14],證明北斗很久以前就和豬祭祀有聯(lián)系。《史記·天官書》云:“奎日封豕,為溝瀆。”“奎”封豕(大豬),即為“圭表”中的“大圭”。 奎宿主生殖,北斗主生殺壽夭[15],二者合一正好體現(xiàn)了漢至六朝時期的生死觀,手握玉石豬而葬,既帶著生前的財富,也乞求長生永恒。巫鴻先生有過“已故的更高級貴族不僅可以隨葬明器和生器,而且可以隨葬祭祀活動中使用的‘祭器’”[16]的論斷,玉石豬手握祭祀的意義似乎就更為重要。

表1 馬鞍山地區(qū)出土玉石豬手握情況表
大漢體制的崩潰,給社會思想帶來了嚴重的沖擊,人們在盲目遵循周禮框架的同時,又產(chǎn)生了動搖,佛道二教給過慣了鐘鳴鼎食生活的特權階層和簞瓢屢空的窮苦百姓帶來了希冀。南方佛教在發(fā)展中注重探討義理,迎合了士族的喜好,借由其推向統(tǒng)治階層,再反向傳播至平民,形成一種人人贊善、莫不從風的風氣。不同于佛教追求死后的清平和安詳,道教追求的是自我真實和修仙。在天災人禍頻繁的漢末,道教不依靠高層宣傳,而是通過流民口口相傳來布道,扎根于基層,深得普通群眾信任。服食丹散尋求永生的做法,與六朝士族的歸隱之風和灑脫之氣相符,在文人雅士的互相推介下,道教又逐漸向上攀附,再加上朝內(nèi)寬容放任,形成了另一種并行的信仰體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生長的兩種宗教,在六朝時期相互吸引,卻又永不融合,這種獨特的社會氣候,形成了中國歷史上不可多得的宗教大繁榮階段。
綜上所述,馬鞍山地區(qū)出土的玉石豬手握體現(xiàn)了極具時代特征的演化進程,也反映了六朝都城建康外圍都市的民間信仰狀況。重新審視馬鞍山的六朝墓葬,發(fā)現(xiàn)大部分都帶有濃郁的佛道氣息。道教為東漢末期本土宗教,在建康文化輻射圈內(nèi)較為發(fā)達。此外,東吳伊始,馬鞍山大興佛教,以笮融為先,于當涂大起浮屠祠,其后境內(nèi)又有大批寺院拔地而起,信徒眾多。社會彌漫著濃郁的宗教氛圍,然而任何教派發(fā)展成型后都會脫離人民大眾,淪為統(tǒng)治階層的暴力工具。宗教再發(fā)達也只能緩解一時的疼痛,百姓骨子里還是堅持著歷史長河中約定俗成的一套規(guī)矩。漢代有九竅葬玉的習俗,僅有玉石豬手握沿用至六朝,足以證明從漢代而來的傳統(tǒng)信仰在老百姓心中仍然堅挺。馬鞍山地區(qū)出土的隨葬品,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宗教在這里沒有完全阻隔和扼殺傳統(tǒng)文化,而是主動吸收、兼容并蓄,影響著普通百姓的生死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