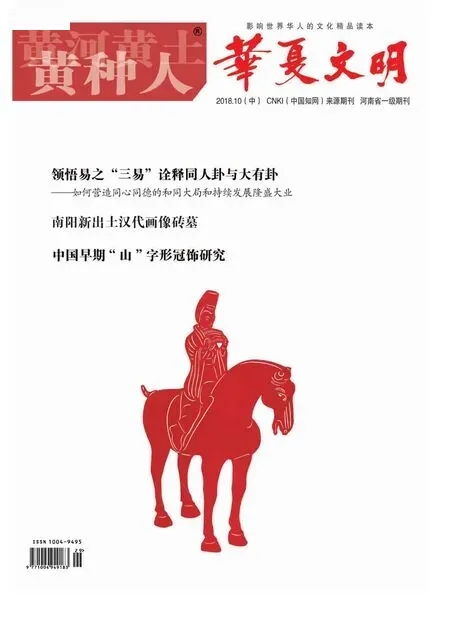后石家河文化玉器論證兩則
□ 顧萬發
論石家河文化“C”形一類玉神鳥造型的生物學來源圖解

圖1

圖2

圖3

圖4 商周神鳥紋

圖5
注:
1.后石家河文化這類玉鳥(圖1羅家柏嶺及婦好墓玉鳥),一般被學者稱為玉鳳。從甲骨文材料看,鳳為神鳥,一般有冠,可用于指代神圣的鳳。
3.以鳥類發展、遷徙史為基礎,結合現鳥類分布變遷的學術研究情況,我們認為后石家河文化“C”形鳥這類玉鳥造型與雄綬帶鳥關系密切;其他像藍鵲類,雖然與婦好墓神鳥較為相似,然無冠羽,所以不應為一類。錦雞、長尾雉類,其尾又與婦好墓神鳥有別,長尾羽較多;同時由于自然界中存在雄綬帶鳥這類肖似的鳥類,所以不宜視為藍鵲等鳥類與其他鳥類特征的組合,也不宜視為鳳。
4.羅家柏嶺出土的后石家河文化玉鳥為正方向“C”形鳥,婦好墓出土的后石家河文化玉鳥為“側身顧首形”“C”形鳥。把生物制作成“C”形的風格最早應該來自北方的紅山文化(圖2-1),又經過凌家灘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圖2-2)傳承而來。“側身顧首形”神鳥在湖北后石家河文化鷙(圖3-1)及湖南澧縣孫家崗龍山時代玉鷙鳥[1]中都存在。在江蘇北部溧陽市出土的龍山時代溧陽圭玉器圖像的神鳥造型中,也存在“側身顧首形”的造型。
5.商代早中期主要是小鳥紋,長尾鳥主要是從晚期開始出現;西周時期長尾鳥較多。(參閱圖4)從這些長尾鳥看,一般都有彎喙特征,這是綬帶鳥所不具備的。又,這些長尾鳥有的明顯具有錦雞或孔雀尾翎的特征。因此我們綜合地判斷,后石家河文化的這類長尾綬帶鳥并不是商周文化語境中鳳的造型。
6.后石家河文化這類“C”形神鳥應來自自然界的雄綬帶鳥造型,其尾羽與龍山時代有的神人首的部分羽翅造型[2]、臺北故宮博物院龍山時代玉圭上的鸮首之部分羽毛[3]、新砦期陶器蓋上的鸮與虎元素融合的神面首之鸮簇羽形羽毛造型非常相似[4]。而若如之所述,圖5-1、3這類神物明顯是具有喙的鸮,其冠之羽毛造型應為鸮羽,主要表現的是其簇羽,這似乎與后石家河文化“C”形神鳥取形于雄綬帶鳥有矛盾[5]。我們認為,這類羽翅的造型只是羽翅的一種表示法,沒有生物屬性之別,對于其他的神鳥羽翅也可以運用其來表現[6]。總體來看,圖5-2應視其冠羽與鷹或鷙鳥有關聯,整個神人應視為擬人化的天命之鷙,是少昊鷙的鷹或鷙神祖。圖5-1所示鸮首的冠羽特征,應是典型的鸮之簇羽;這類尾羽造型與二里頭近年發現的陶刻羽冠(圖5-5)近似,圖5-3鸮首的“介”字形為中心的冠羽除了表示鸮首有典型的簇羽之外,還應擬合太陽大氣光象,與龍山時代或后石家河文化中諸多玉神人之首的“介”字形冠羽類似,譜系上應來自高廟—河姆渡—良渚—大汶口文化介字形系列。至于圖5-2所示弗利爾玉刀神人,有“披肩長發”,其顯系擬合山東龍山或后石家河文化之鷹或即天命生少昊鷙之鷹的枕羽或項羽的,其腦側立著冠羽,與一般“披肩發”神人[7]略有不同。
[1]圖3-2。為“C”形團鳥,以近似條狀為鳥身造型或造型主體,在山東龍山文化中發現不少,在后石家河文化中也有發現。圖2-1那斯臺“C”形無簇羽的鸮也是重要代表。
[2]圖5-2。這是有船型冠并披肩發者同時又有明顯羽翼紋神人的代表。
[3]圖5-3。這是一只生物造型較為明顯的鸮,即郯子所謂的玄鳥氏之象征,該玄鳥氏也即商人玄鳥氏之由來。
[4]圖5-1。該神面之身不能確認,其虎式的鼻子及眼睛的組合非常類似二里頭綠松石銅龍。然其身不易于論定,從良渚文化所謂的獸面紋看,可以是鸮身。不過從三大龍山文化看,也可能是鸮身或“蹲踞式”的人形身,從二里頭及商周融合了鸮元素的情況看,也可能是龍身。可能具有隨機應化的變宜特質。
[5]圖5-4玉器包括兩只鳥,右邊的為象征少昊鷙之所來的鷹神祖(披肩發神人則為類似天命玄鳥生商的天命生少昊之擬人化鷹神祖),左邊的應是象征郯子話語中五雉之一的雄綬帶鳥。
[6]若復原的話,從法國吉美博物館所藏后石家河文化披肩發神人看,最可能是擬人化的“蹲踞式”,此即綜合《山海經·大荒南經》、《拾遺記》等文獻得來的“帝俊生少昊”神話的由來。商人玄鳥氏與少昊鷙關聯密切,同屬于少昊系,又都有神鳥生始祖神話,神祖無論是神鳥形還是擬人又仿照神鳥的“蹲踞式”神人形,都與夋字類似,所以商人祖先嚳之“蹲踞式”造型也易于和少昊鷙之神祖的“蹲踞式”造型混同,然而一為鷹或曰鷙神祖,一為玄鳥或曰鸮神祖,雖然屬于少昊系,然有不同矣。不過三大龍山文化中鷹、鸮常見共存一器,可見少昊系中兩者的密切關聯。
[8]這類“披肩發”都為虎所“食”,與商代虎“食”人圖像應為相近的身份,商人虎所“食”之人從泉屋銅鼓“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圖像看,其為玄鳥神祖,即有部分擬人的鸮神祖。于此,則這類披肩發者(擬鷹或鷙之項羽或枕羽)應為昊族之鷙神祖,少昊始祖則為清或鷙。
論羊舌村晉侯墓地新石器時代玉人高冠及相關問題


(備注:圖片說明指的是器物出土地或所藏處)
羊舌村晉侯墓地出土一件非常重要的玉人(圖1),風格是典型的后石家河文化。關于此件玉器,不少學者予以過論證。關于其頭頂的冠形,是不少學者提及的。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是鷹,另一種認為是神面。于此問題,我們認為非常重要,現予以論證。
這類圖像,在法國吉美博物館藏玉器之鷹(圖2)、臺北故宮博物院玉圭之鷹(圖3)、南陽麒麟崗玉鷹(圖4)、小屯后石家河文化玉鷹(圖5)、天津博物館徐世章舊藏后石家河文化玉器鳥身人面(圖6)身上均存在。實際兩城鎮玉圭一面的鸮圖像介字形冠頂中心也有這類造型(圖7),與圖3鷹神身上的這類造型也特別相似。關于這類圖像,確實非常類似山東龍山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石峁文化等三大龍山文化戴介字形冠神,有的與一些去除雙目的神面也較為類似,像吉美博物館玉器鷹形身飾、麒麟崗玉鷹身飾與譚家嶺玉器(圖8)、天津博物館原徐世璋藏玉雕組合下端神面去掉雙目的造型基本一致。臺北故宮博物院玉圭一面的玉鷹之身飾介字首圖像及小屯M313所出鷹形發笄所飾介字首圖像下端為反向S形,與三大龍山文化玉人枕之羽飾下端或及項的下端相似。關于羊舌村神面之冠,參照林巳奈夫先生[1]關于龍山時代玉器扉牙及筆者的解讀方法,其完全是由羽翼紋組成的,不應視為鷹,具體解讀如圖1。該玉器的重要價值之一在于利于說明獠牙神面頭頂之穿確實有組裝介字首羽飾的現象。
不過,綜合地判斷,我們認為這類造型仍不是神面,有的是因為與一些神面的宏觀主體很類似,似乎易于理解為是這些神面省略雙石目的造型。商代確實也曾發現過無目饕餮。后石家河文化的一類玉神面像陶寺、肖家屋脊所出的那類玉神,其雙目顯然是由羽翼紋圍成的,不能由此認為其也是無雙目神面。另圖6人面鷹身神身上這類介字首造型明顯只是介字形而非具有神面大概輪廓的羽翼紋構圖[2]。另兩城鎮地區也發現不少單獨介字形為單元的組合圖(圖9~11)。龍山文化玉圭或玉人項背有的一面也只是羽翼紋組成的介字形或近似介字形,像何東圭主一面的圖像就是一種羽翼紋組成的近似介字形(圖12),不過與圖1之類聯結在一起的介字形圖像造型構圖方式方面有所區別,上海博物館所藏的后石家河文化玉人頭項背也有這樣一類介字形圖像(圖13)。這類經常位于與神人或神鳥相組的一圭兩面的另一面,或位于人項背之介字形圖像,雖然其與前文所論圖1一類介字首形的羽翼紋構圖有所區別,但是都是羽翼紋造型,本質應屬一類。不過這另一類介字形羽翼已發現多件,似乎未見這類羽翼紋作為冠的情況存在,只是臨朐朱封玉冠飾[3]之介字形冠與它們有些類似,同時大甸子墓地具有明確山東龍山文化風格的彩繪神面有一幅鸮神面也有類似的冠,不過有所變形。另這類無目的的以“介”字形為首的由羽翼構圖的圖像,有的雖然非常類似有目神面之宏觀主體,依然不宜視為具體神面,其可以像羊舌村玉器中的該造型一樣,作為羽冠,也可以像肖家屋脊羽飾玉柄形器一樣[4]。
那么為何這樣的造型均沒有雙目?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關于這一問題,我認為以下幾方面較為重要:
1.這類介字形羽翼紋明確地說,應該直接來自大汶口文化。主要依據是:
(1)造型相似,時代接近;
(2)與昊族有關的歷史傳說在文獻和考古上可以說明,山東龍山和大汶口文化的族群主體是具有連續性的。
(3)大汶口文化這類造型中有的介字形兩側已有羽翼紋,與龍山階段類似。
(4)浙江三畝廟遺址王油坊類型的地層中曾出土有類似大汶口文化“介”字形符號的造型,其中出現了雙目及鼻子的神面。對于我們理解所述無雙目“介”字形有參考價值。即有無雙目的兩者有聯系,但是不可視為是原形和省略。
2.這類造型更早的來源應該是河姆渡文化及高廟文化。其中高廟文化時期已開始出現單獨、兩個或三個介字形相組的形式,并且高廟文化這類介字形多同時有幾種含義:
(1)表示太陽周邊以真太陽為中心的光氣造型,包括太陽光柱。有的為太陽光柱或幻日環方向的光氣造型。可能還與太陽出入之山擬合。多重介字形,往往為三個,有時為兩個,這是明顯的同時擬合山的造型的。
(2)兩側往往有以較完整的呼應其兩側太陽大氣光象神鳥——鷹之尾羽或羽翼組成的近似“介”字形,以示意太陽光氣的“介”字形造型之邊界。
(3)還有一些介字形,同時還表現及擬合太陽大氣光象中的光十字等形。河姆渡文化的“介”字形也有幾種含義:
a.田螺山遺址神鳥形陶盉上有一來自高廟文化的“介”字形,也是表示太陽周邊以真太陽為中心的光氣造型的,包括太陽光柱。該盉上的另一月牙似符號則可能與大汶口文化的這類符號呼應的太陽大氣光象一致,而與切弧及帕瑞弧圍合的近似月牙形呼應的大氣光象不一致。但是若不考慮位置與方向則就一致了。
b.河姆渡的“介”字形中有一類明確是擬合太陽大氣光象的,包括的太陽大氣光象非常豐富。
c.河姆渡象牙骨雕上的兩鳥圍繞太陽、月亮的構圖中,其中的介字形首應呼應太陽的22°暈切弧及其中心向上的光芒,其邊界也是用兩側神鳥的羽翼紋圍合的,與高廟文化中介字形兩側常見神鳥羽翼紋或尾羽類似。所不同的是,高廟文化中的介字形兩側的神鳥一般是呼應宏觀太陽大氣光象的鷹類,是否也存在少量呼應月亮大氣光象的神鳥及相關物象,暫不易找到。而河姆渡象牙骨板太陽頭頂組成介字形的羽翼紋來自表示太陽兩側有關太陽光氣的神鳥之羽翼,包括太陽的幻日。
d.河姆渡遺址河姆渡文化時期曾經出土過完全以羽翼紋表現的太陽光氣造型,也出現過介字形兩側有對稱羽翼紋的材料。這顯然是受到高廟文化的影響并具有創新的現象。同時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這些造型是大汶口文化兩側帶羽翼紋的介字形符號的重要來源。在此言明,河姆渡遺址屬于河姆渡文化的時間下限可能比一般認為的會更晚一些。
3.在良渚文化中,這類介字形文化得到進一步豐富,各類介字形冠眾多。同時一些玉器符號中也出現諸多這類造型,像弗利爾玉璧中的壇臺符號可與文獻中所言的三層昆侖之丘互相印證,屬于山,與大汶口文化中的特殊刻畫符號中的部分符號也可以,并且這類符號與山形相呼應,還呼應太陽光氣或太陽大氣光象。另,弗利爾玉璧的昆侖形壇臺符號中常見的神鳥負太陽造型或曰有羽翼太陽,實際也呼應太陽大氣光象。良渚文化山形與太陽的組合實際與大汶口文化中是有圓形太陽的諸多介字首符號具有相類的文化內涵的,都可以與太陽出入之山聯系。
綜上所述,我們對于羊舌村這一玉人之高冠及所述龍山文化中的類似介字首圖像的性質有以下認識:
1.最早的雛形和文化淵源來自高廟文化,經過河姆渡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在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進一步豐富起來。在龍山文化中逐步形成類型多樣,豐富和簡約并存的介字形為首的圖像。
2.其文化關聯的物像顯然是太陽,在河姆渡文化時期這類圖像關聯的物像中有一幅為月亮。
3.在大汶口文化時期的以山東地區為中心的地域,傳說和文獻記載其主體為昊族,即太昊和少昊。所述大汶口文化與太陽大氣光象有關的諸多著名刻畫符號顯然是昊族的信仰主題,也即有太陽之義。
4.從考古學文化看,大汶口文化時期的人群有相當的成分至少是信仰文化可能與南方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高廟文化有關文獻失載,只是相關古史或傳說失傳而已。從考古學文化看,良渚文化與河姆渡、高廟文化也有密切聯系,有的現象的隔代出現,有可能是早期人群的文化復興。
5.山東龍山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中的介字首圖像的單獨出現,實際在新砦遺址新砦期的高領罐肩膀上也出現過。其作用同于二里頭、荊南寺等遺址二里頭文化高領冠肩膀的代表東夷昊系神面的單目符一樣,用于表明其昊族文化特征。從石峁文化存在諸多的后石家河文化神面、陶鷹、花地嘴遺址相當于石圭的石器上存在鷹、花地嘴遺址新砦期朱砂繪鸮神面、瓦店遺址鷹、瓦店遺址附近南京大學南水北調工程考古工地出土的鷹之類的材料看,少昊系在石峁文化、河南龍山文化及新砦期時,在中原或影響中原的實力非凡。其實從二里頭、商等時期的鸮元素眾多以及商人玄鳥氏屬于少昊系的材料看,少昊系的鷹或鷙系及玄鳥鸮系對于中國早期國家形成和信仰等文明形成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石峁文化主要在西河左右,與啟子武觀地近,夏代尤其是早期與皋陶系也關聯密切。又依據文獻記載,有鬲氏為少昊之裔,有虞氏、有仍氏為東夷之人,少昊之皋陶系輔助夏禹征伐及管理,這樣看來,龍山時期及新砦期時較多出現東夷系少昊系文化因素這一狀況,就不奇怪了!具體地看,石峁文化的統治集團應有啟子武觀系、少昊系以及地方權貴。石峁的少昊系尤其是其中的皋陶家族在當時地位較為顯赫,從諸多文化中存在鷙即鷹的情況即可看出。這樣看,羊舌村晉侯墓地這件玉人有可能來自石峁文化區。不過從諸多玉石考古材料看,制作這類單獨的玉雕人像在后石家河文化區更為盛行,所以不論其直接承自何時何地,恐怕該玉器的原產地仍是后石家河文化區更有可能。
6.三大龍山文化及花地嘴新砦期玉圭上的鷹,應呼應太陽大氣光象,圖6鷹身的菱形即是菱形真太陽。整體與高廟文化中的鷹有類似之處。這類呼應太陽大氣光象的鷹身由羽翼相組的介字形為中心造型,也應與太陽密切相關,這正是高廟、河姆渡等、大溪、良渚、大汶口系列文化中介字形的基本意思。這類鷹應與玄鳥生商神話語境中的玄鳥鸮一樣,是生少昊鷙的天命之鷙,弗利爾博物館玉刀虎“食”披肩發神人與商代虎“食人”、饕餮“食”玄鳥鸮等題材中的人、鸮類似,都應是天命之物或擬人化的神人。天命生少昊之鷹擬人化的材料中,法國吉美博物館所藏一件為完形的“蹲踞式”,可呼應文獻中帝夋生少昊。
7.《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之話有許多不確的地方,然少昊鷙與玄鳥氏等關于少昊的說法有不少真實成份。從后石家河文化、山東龍山文化、石峁文化等之中玄鳥鸮與鷹或其擬人化造型的高度相關性看,少昊系與商人玄鳥氏確實關聯密切。與少昊鷙有關的天命之鷹尤其是其擬人化的“蹲踞式”造型,說明東夷系帝俊的由來原來與這類“蹲踞式”神人有關,并且擬合的是鷹,而非商人的玄鳥鸮。從卜辭中的商人祭祀神祖造型、弗利爾博物館龍身饕餮所“食”跪坐側上半身攏手的擬人化玄鳥神祖、婦好墓出土跪坐并身有蛇腹有蟬身饕餮上帝的擬人化玄鳥神祖看,商人的玄鳥鸮圖騰擬人化也可呈跪坐式或“蹲踞式”,從文字學角度,也都可稱為“夋”,但是商人本身是讀契、夔等字的,卜辭中的所謂高祖嚳則常規隸為夏字,文字上也類“夋”。這些可能也是文獻中嚳、夋混同的本質原因之一。又少昊鷙之鷹鳥神祖擬人化也為“蹲踞式”,就更容易出現商人玄鳥氏祖先與少昊鷙昊族鷙鳥祖先造型的混同了。
少昊鷙的鷹鳥神祖與契的玄鳥神祖,都可擬人化,都可為虎所“食”,并都為“蹲踞式”,依郯子語,兩者同為昊族,誠如是,這可能是考古學、藝術史探索文獻古史的重要案例了。
了解了三大龍山文化鷹之本質,再看這類介字形羽飾,我們可能會對于這類經常出現于鷹身之造型有更為確切的認識。其不是鷹應是明顯的了,因為鷹身再飾一鷹紋顯然不合適。這利于玉料或晚期藝術、民族雕塑不可等同。
綜合地看,這類以“介”字形為中心的造型,本身應該是大汶口文化著名符號中的有明顯羽翼紋并以“介”字形為中心一類圖像的傳承,像南京北陰陽營陶尊上的大汶口文化符號等。這類符號中底端的一組羽翼紋,按照林巳奈夫先生對于玉器扉牙的識別系統和我們的補充,一般是刀型“e”或“s”形首“e”,有的還有“f”及“c”,應該呼應所論大汶口文化這類刻畫符的底端。山東龍山等三大龍山文化的這類以介字形為中心的造型,一旦增加雙目,即為神面。若再增加獠牙、人形的嘴巴等人類面部和人類頭型等特征,即成為具有擬人化特征或部分擬人化特征的神。這類造型與大汶口文化著名刻符有關的現象進一步說明,三大龍山文化中與“介”字形羽翼紋有關的玉神面,無論是何方神圣,都與太陽有關無疑。
[1]林巳奈夫:《中國古玉研究》,日本弘文館出版,1991年。
[2]圖6中的鷹應為天命生少昊之鷙,鷹爪下端的人面鳥身者圓形目,應是鸮鳥身及圓形鸮目的擬人鸮神,該神下端的神面雙目為旋符形,應是鸮面,這也利于說明圖8譚家嶺鷹神下端的圓目者也應是鸮而非虎,其也是與山東龍山文化諸多玉圭圖像一樣,是典型的鷹、鸮組合,或曰少昊鷹神祖及玄鳥鸮神祖組合圖像。黎城戚上有三個神廟,并且其中兩個組合雕刻在一起的神面方向不同。該戚圖像中也有擬人化的披肩發神鷹祖及鸮神祖圖像。這些現象說明文獻中言商人與東夷有關聯確是可以證明的。
[3]實際為戴介字形冠的鸮神,簪子本身代替鸮喙。
[4]該柄形器之羽翼紋可能依然不是神面,鏤空部分主要是為了標明單元羽翼邊界或及我們關于玉器扉牙稱謂所定義的C,整個造型可視為羽翼紋高冠,結合文獻可視山東龍山、后石家河、石峁等三大龍山文化的這類造型為少昊系文化符號。當然新砦陶器蓋神面、花地嘴朱砂甕神面、二里頭、齊家、三星堆、夏家店下層等文化中的牌飾俊有鸮元素,因此與少昊系均有聯系,即與其中的玄鳥氏關聯密切,以玄鳥即鸮為圖騰的商人諸多饕餮神與之相關更不必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