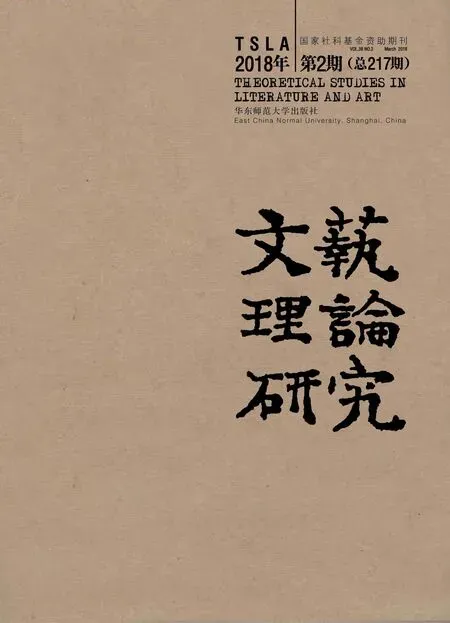“種植我們自己的花園”:藝術如何面對不完美的世界
范 昀
引 言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小說《老實人》名聞遐邇。故事主人公性情率直、思想單純,生活在一個伊甸園式的城堡之中,對世界充滿美好的想象。由于一次與戀人的偷情經歷,使他墜入人生的噩夢。他不僅親身遭受各種酷刑磨難,還耳聞目睹形形色色的災難、戰爭與屠殺。盡管他最終得以從苦難中解脫,并與戀人久別重逢,但她早已美貌不再且脾氣暴躁,小說結局并不完美。作為一部經典的啟蒙時代之作,這部作品不僅暗含對教會的嘲諷,而且還對當時流行哲學提出質疑,該哲學認為“我們這個世界是所有世界中最好的一個”(萊布尼茨)。老實人以親身經歷作出否定:世界非但不是最好,而且極其糟糕。現實的殘酷使其從幻夢中蘇醒,認清世界的真相。但他最終依然熱愛這個苦難重重的世界,即便曾經路過堪比人間仙境的“黃金國”,他都不為所動,還是選擇“種植我們自己的花園(Il faut cultiver notre jardin)”。
伏爾泰此言后成為經典,被人競相引述。盡管他語焉未詳,卻發人深思:既然黃金國這么好,為何還要選擇這個苦難重重的世界?藝術通常被認為超越現實,為何伏爾泰要通過他的藝術鼓勵人們不要放棄這個不完美的世界。當憤世嫉俗成為當代文化的普遍特征,當反抗與救贖成為當代藝術的核心主題,伏爾泰式的“妥協”是否還有意義?面對這個不完美世界,藝術何為?從個體角度看,藝術既能為苦難或虛無人生提供慰藉與救贖;從社會角度觀,藝術也能訴諸對社會與世界的政治關懷。自十九世紀以來,隨著藝術實踐越來越深入地介入社會政治,理論層面的“政治美學”浮出水面,并日益興盛。在此背景下,本文側重藝術的社會政治維度,探討其如何來實現它對社會與政治的關懷。伏爾泰關于“黃金國”與“花園”的對照,恰好為本文討論提供了這樣兩個政治美學的維度。
一、夢想與反叛:藝術的烏托邦之維
在當代藝術實踐與美學視野中,“烏托邦”作為文化符號占據了顯著位置:當代藝術及其理論越來越多地訴諸社會與政治議題。十九世紀以來在藝術家身上發展出來的救世主意識變得愈加顯著,藝術家越來越認為自己能為人類社會帶來解救的福音。尤其自二十世紀以來,政治成為藝術與藝術批評競相追逐的主題。無論是上世紀末各種意識形態批評思想,還是本世紀初大紅大紫的激進主義學說,這些政治批評話語都在暗示:藝術或文學是個大問題,它們的存在關乎社會正義與人類興衰存亡。在這一語境中,“烏托邦”作為一個符號頻頻出現在各種藝術實踐、理論及批評之中。不僅當代各種藝術展覽尤其熱衷以“烏托邦”(或“異托邦”)為標題,而且在當代藝術的相關研究論著中,關鍵詞“烏托邦”更是屢見不鮮。
自英國的托馬斯·莫爾以來,“烏托邦”這個概念雖然被賦予相對確定的政治內涵,但在歷史的進程中其含義卻不斷得到擴張與延伸。作為政治實踐的烏托邦雖在二十世紀壽終正寢,這卻并未阻礙更多文化層面的烏托邦浮出水面。烏托邦不僅能通過形態上的轉換重獲新生,而且還能通過語言上的改造重構內涵,甚至還有些名存實亡的烏托邦,以空洞的能指方式游蕩在當代文化與藝術的空間之中。因此在今天要給“烏托邦”下定義幾乎是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唯從“家族相似性”的角度看,作為符號或話語的烏托邦在這個世紀藝術文化中的普遍性與活躍度,才讓本文有勇氣以“藝術的烏托邦之維”來統攝歷史與現實中紛繁復雜的藝術實踐。本文討論的藝術烏托邦之維,首先強調其不同于藝術之于個體的“理想性”與“超越性”,旨在強調藝術對社會政治的介入;其次則突出其在疏離、批判甚至顛覆現實中所采取的“完美主義”立場。
在此可以當代藝術家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1981 年的作品“傾斜的弧(Tilted Arc)”為例。這位藝術家曾在紐約聯邦廣場用鋼板打造了長一百二十尺,高十二尺的一面單調形體,像一面墻一樣橫跨廣場中央。由于其妨礙了市民的出行便利而遭到抗議,并最終拆除。這個在生活中備受詬病的藝術作品,卻得到了藝術界的充分肯定。有學者就指出它對公眾的刻意冒犯很好地展示了藝術的批判性與烏托邦沖動:“一方面,藝術試圖創造一個理想的公共空間,一個非場所(nonsite),一個想象性的風景;另一方面,藝術通過打破平靜、烏托邦式的公共空間來揭示沖突,并與它所指涉的公共領域保持一種反諷、叛逆的關系”(Mitchell 3)。該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充分展示了藝術烏托邦之維的兩種主要形態:
一種形態是彼岸的夢想。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藝術思潮為藝術烏托邦提供了理論依據與實踐支持。尤其在德國浪漫派的藝術實踐中,藝術成為脫離此岸,抗拒現實的手段。“世界變成夢,夢變成世界。”在創作層面,諾瓦利斯的“藍花”的烏托邦意味不言自明。在理論層面,席勒的“游戲說”為藝術疏離現實提供思想依據。席勒描繪的審美王國中“人擺脫了一切稱為強制的東西,不論這些強制是物質的,還是道德的”(席勒 235—36)。盡管這種審美王國不具政治性,但對現實的疏離使得“這個信念中存在著藝術家與社會之間矛盾的起源”(巴爾贊 35)。于是審美烏托邦被順理成章地理解為批判現實的理想尺度:藝術的目的就是要克服世俗、譴責財富,其意義就在于向資產階級庸人開戰。
另一種形態則是決絕的反叛。如果說在浪漫主義時代藝術的反叛初見端倪,那么這一反叛在二十世紀則蔚然成風。在藝術實踐上,從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到六十年代的反文化運動將藝術的叛逆推向極致。“亞美利加,你何時才變得像天使那般模樣?/你何時才會脫去身上的衣裳?/你何時才透過墳墓看看自己的尊容?/你何時才不辜負千百萬托洛茨基信徒對你的信仰?”在金斯堡詩句中這種完美主義得到淋漓盡致地呈現。美學理論也給予這種反叛全力支持。從批判理論到國際情境主義,“用想象力奪權”成為當代藝術實踐的政治宣言。與席勒式的夢想不同,這種烏托邦更強調革命與顛覆:有人希望從資本主義的崩潰中,產生出一種“自然的、合乎人類尊嚴的生活”(盧卡奇 11)。還有人則認為只有克服席勒式的夢想,一個新的天地才有機會得以誕生(馬爾庫塞 100)。即便呈現方式不同,但反叛同樣還是烏托邦,它是另一形式的“伊甸園”。
反叛烏托邦甚至會以虛無的形態呈現。在恩斯特·布洛赫看來,“虛無(das Nichts)是一個極端反烏托邦的范疇,它也是一個烏托邦的范疇”(布洛赫 13)。像杜尚的《泉》、安迪·沃霍爾《布里洛的盒子》以及大地藝術等,盡管在表面上并不具備明確政治指向,但在先鋒藝術不斷被消費主義收編的背景下,這些藝術被認為能以更激進的方式來實現其政治潛力,它讓大眾吃驚地發現所謂的藝術竟然是那些他原本就擁有的事物,或是他無法用金錢購買的事物。這種看似幽暗的虛無態度背后依然潛藏巨大的烏托邦沖動。
由此可見,一方面,藝術烏托邦的構建得益于藝術家的個體才華與想象,以及其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孤獨與異化體驗。他們希望通過藝術來尋求一個完美的世界;另一方面,藝術走向烏托邦的進程與各種哲學、政治思潮以及文化批評緊密相連。如果說在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之夢中,藝術家的自身經驗尚有相當言說空間的話(席勒的哲學已經開始影響藝術),那么越到當代,哲學觀點尤其是意識形態理論對藝術的影響也越大,藝術的價值也越來越離不開理論的解釋與評價。“當前誰還不了解女權主義、解構主義、精神分析法、同性戀理論和后殖民理論,他就根本無法進行藝術批評”(埃爾金斯 46)。在藝術與烏托邦聯姻的過程中,理論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覷。
二、藝術烏托邦的價值與迷思
作為藝術實踐的重要維度,烏托邦價值不言而喻。英國作家蕭伯納曾經寫道:“人生有兩大悲劇:一是心里想要的得不到;二是想要的得到了(there are two tragedies in life.One is not to get your heart's desire)”(Bernard Shaw 174)。 后一種悲劇意味著:夢想或者希望對于人類生命的存在論意義。人生需要希望,社會也同樣需要希望。烏托邦作為一種社會希望的象征,像遙遠的星星一樣為社會提供更美好導向。尤其在一個資本主義民主大獲全勝的時代,如何想象與探索一個超越現行體制之外的社會形態是需要的也是必要的。
然而,藝術的超現實之夢或者革命性的反叛并非想象的那么美妙。尤其從當代藝術的現狀看,這種藝術烏托邦要么拒人千里,與日常生活毫無聯系;要么姿態激進,實質空洞,嘩眾取寵的成分大過其他。當“烏托邦”成為這些藝術與文化現象代名詞的時候,我們是否也需要有所反思:烏托邦是否也會導致某種藝術在倫理或政治上誤入歧途,或淪為某種淺薄的時尚。
前文已談到,藝術烏托邦的興盛與當代社會政治理論的介入密切相關。尤其是左翼激進思想對藝術家的社會想象力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從不少二十世紀的前衛藝術運動可見,藝術對“完美”社會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這些帶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學說。在有些情況下,這些學說的理論性、教條性與封閉性造成藝術在理念上的貧乏:常常是這些理論教會了藝術家什么是完美的世界,同樣是它們引導藝術以決絕的方式來敵視社會,這個問題從席勒就已初見端倪,此后的審美烏托邦實踐越來越遠離那種藝術家依據自身體驗而生成的“經驗之夢”,而越來越趨向于淪為意識形態理論制作而成的“觀念之夢”。盡管看似都是夢,但此夢非彼夢,有時連夢都可以變得那樣刻意經營與矯揉造作。
當我們暫時離開這些理論話語,就不難在歷史與現實中發現如下事實:首先,歷史上的藝術并非都以烏托邦式的超越或對抗生活的方式出現的。藝術與社會之間并不如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那樣充滿對抗。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追求均衡與得體,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合宜的位置(埃爾金斯 8)。而透過薩繆爾·約翰遜博士的作品也不難發現在十八世紀,寫作旨在使得讀者能夠更好地享受生活,或者說,能夠更好地忍受生活。在十九世紀,簡·奧斯丁、狄更斯的小說中讀者更能感受到這一點。
其次,盡管藝術對社會采取激烈批判,但其實際效果令人懷疑:藝術是否真正讓社會擺脫庸俗,是否讓社會變得更好。“浪漫派痛恨庸人,但是庸人卻喜歡浪漫派”(卡爾·施密特 94)。盡管卡爾·施密特談到的是十九世紀的德國浪漫派,但這個判斷也同樣適用于當代藝術:再前衛激進的藝術都會成為媚俗藝術。藝術不僅未能克服庸俗,反倒使自己變得庸俗化。烏托邦本身也會被消費主義所馴化。《叛逆國度:為何反主流文化變成消費文化》一書明確指出,反叛的王國隨時都會淪為消費的王國。
再者,烏托邦使得不完美與不完美之間的區別變得毫無意義。在完美主義的尺度前,一切現實缺陷都不可容忍。比如在克里斯特瓦看來,“我們生活在一個低級時代中”,一切都是“景觀,一切都是商品,我們稱為邊緣化的人已經完全變成了被社會摒棄之人”(克里斯特瓦 17)透過這樣的言說,人們感到民主與專制同樣邪惡,資本主義與恐怖主義更是一丘之貉。當代藝術實踐深受此影響。更有甚者,烏托邦還成為意識形態的宣傳借口。在批判一種不完美的同時,卻有意無意地對另一種不完美視而不見。我們常常驚訝地發現,很多藝術家對資本主義的毫不妥協常常吊詭地與對極權主義、恐怖主義的同情同時并存。藝術家訴諸烏托邦式的正義感,有時候存在著某種危險。
最后,烏托邦由于其本質基于主體對世界的想象,容易淪為自我與私人欲望的產物。你的烏托邦并不代表我的烏托邦,在當代理論大肆宣揚“欲望倫理學”與“個體即政治”的氛圍中,烏托邦的公共性正經受考驗。在藝術層面涌現出大量借烏托邦宣泄私人欲望的作品(如安迪·沃霍爾所言:“藝術就是在能被容忍的極限內隨心所欲。”)。與此同時,借談論烏托邦大政治之名來實現名利雙收的小政治,在行內也早已不是公開的秘密。“在一個不斷原子化的世界里,自我實現成為第一美德,甚至烏托邦也已私有化”(迪克斯坦 11)。
藝術烏托邦一方面通過召喚人們批判現實的不完美,為人類社會的未來提供新的想象;但另一方面我們已經看到,藝術烏托邦對理想的追求有時會誤入歧途,這種對完美世界的追求有時常常喪失了人的尺度,以“非人”的完美主義尺度來評判、反叛與逃離現實。當代藝術訴諸理念與意識形態對抗的成分越來越多,訴諸情感與人格教育的成分越來越少。當烏托邦成為“一切政治我都反對”和“一切現實我都摒棄”的代名詞,當現今藝術把這一理念訴諸于這個業已干癟的名詞的時候,我們不禁要問:藝術烏托邦一定能讓這個世界更好嗎?除了烏托邦之外,藝術還有其他可能性嗎?
三、藝術正義論:現實與自我的平衡
探尋一種非烏托邦式的藝術理念,就意味著藝術實踐的目標不再是“完美”,而在于“更好”;不在于“顛覆”,而在于“改進”;藝術與社會的關系不再是你死我活,而在于彼此支持。這種藝術理念的關注點不在于如何達到終極的完美,而更關注如何從現實比較的層面來修繕不完美。用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的話說:“認定世界上最完美的畫是《蒙娜麗莎》,這對于我們在一幅畢加索和一幅達利的畫之間作出選擇并沒有什么幫助”(森 13)。
我們暫且把這種非烏托邦的藝術理念稱為“藝術正義論”。藝術正義論拒絕以烏托邦式的“完美主義”的范式進行思考,烏托邦范式是要么完美,要么摧毀。完美主義常常趨向于非人化的理論思維,而非建立在人性之上的經驗思維。但通過人性的經驗可見,正義的世界不等于完美的世界,但它可以是人類追求幸福之所。就好比健康的飲用水不等于純凈無菌之水那樣,正視世界的不完美并致力于去接近完美,要比厭惡世界的缺陷而試圖逃離或摧毀它要重要的多。藝術的正義論之維的理想建立在人的尺度之上,充分認識到人類生活的脆弱性與復雜性。它對不完美的認可,并不是出于一種對現實的妥協,而是一種關于人類生活的深刻的倫理洞見。正是在對現實不完美的洞見意義上,藝術實踐才能真正深入體察人的生活與命運,才能真正為這個世界的更美好,作出實質的貢獻。
藝術正義論的聚焦對象體現在對現實(不完美)與自我(不完美)的認知之中。于是如何追尋“現實感”與追求更好的“自我”構成了藝術正義論的兩個重要方面。在這方面,當代美國學者萊昂內爾·特里林、韋恩·布斯以及瑪莎·努斯鮑姆在思想與批評實踐上提供了重要支持。
藝術正義論首先體現在對現實感(sense of reality)的追尋。“現實感”一詞出自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他提出“現實感”的初衷針對的是人類的烏托邦迷思。因為這一迷思認為:我們可以通過找到一把打開世界的鑰匙,來抵達完美的烏托邦境界。這一迷思的致命問題在于,它忽略了現實的復雜性與價值沖突的必然性,人類也為此付出了慘痛的教訓。現實感的存在有助于克服這種迷思,因為它是一種對具體性與差異性分外敏感的感受能力。在伯林看來,人們通常能在偉大哲學家、政治家以及藝術家身上發現它。藝術常常因其對細節與復雜性的敏銳度,使其對抽象宏大的理論烏托邦具有先天的免疫力(伯林22)。然而伯林并未想到的是,理論層面的烏托邦話語也能成功收編藝術。從當代藝術的發展看,藝術的“現實感”正不斷走向萎縮。藝術不僅未能對理論的抽象與簡單提出質疑,反倒成為各種主義的膜拜者與應聲蟲。無論是往昔的“革命現實主義”,還是今日的“國際情境主義”,它們賦予藝術的與其說是活生生的現實,不如說是意識形態性的政治綱領。柏拉圖時代詩對哲學所造成的挑戰與壓力,在今日的藝術世界中變得蕩然無存,正所謂“藝術被哲學剝奪”的時代。重申藝術現實感的首要條件就是要把藝術從抽象的理論思考中解放出來,使其回歸到對現實社會生活的認識中去,促使其去追求一種思想意義上的知性(intelligence)。用馬修·阿諾德的話來說,藝術對生活的批評,需要建立在為“看清事物本身的原貌所做的努力”之上(特里林 487)。這就意味著對現實的認識與理解是超越生活的前提,對烏托邦的追求不能以犧牲對現實的理解為代價。
藝術現實感包含了一種對事物復雜性與艱難性的洞察。有很多藝術(尤其是小說)能夠挑戰傳統觀念,“教會我們認識人類多樣化的程度,以及多樣化的價值”(特里林 119)。比如特里林認為俄國作家巴別爾的《騎兵軍》卓越之處就在于其呈現了一種超越刻板意識形態的復雜性。與之相反,貫穿于伊迪斯·華頓的《伊登·弗洛姆》的卻只有一種“惰性的道德”。以中國當代文學為例,余華近些年創作(《兄弟》《第七天》)的失敗之處就在于其故事僅能引起讀者簡單廉價的憐憫,卻提供不了具有悲劇意義的復雜性。與之相反,金宇澄的《繁花》則能突破一些流俗觀念,為理解過去的歷史提供了一個新穎而復雜的視角。同樣,正是在對現實復雜性的認識之中,藝術才具有了免于意識形態腐蝕的政治判斷力與社會想象力。在特里林看來,亨利·詹姆斯在其《卡薩瑪西瑪公主》中展示了一種“有關災難的想象力”,使他“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明白了我們經過戰爭和集中營的嚴厲而痛苦的教訓才明白的道理”(特里林 149)。
現實感是一種克服完美主義幻想的能力。藝術不僅可以打造一種烏托邦式的至善天國,也可以培育一種坦然面對不完美現實的態度。瑪莎·努斯鮑姆以亨利·詹姆斯后期小說的《金碗》為例探討了拋棄“完美”對于人生成長的意義。小說講述了一位女性的成長,講述了主人公麥琪如何從一種拒絕看清人生真相的無辜狀態中擺脫出來的故事。標題“金碗”是一個隱喻,金碗美麗卻有瑕疵。女主人公麥琪的成長即意味著她坦然面對自身的缺陷、不完美以及不安全。詹姆斯另一部作品《使節》則呈現了一個主人公斯特瑞塞如何從安全但封閉的生活走向動蕩而開放人生的心路歷程。對于人的成長而言,“完美”的另一面就是“封閉”,喪失面對世界的被動性與開放性。人生難以逃避悲劇性的沖突,沒有絕對的安全,生活總是如一艘小船那樣海面上隨著洶涌的波濤起起伏伏。
盡管《金碗》《使節》看似聚焦個人家庭主題,但努斯鮑姆在詹姆斯的“想象力的公共使用(the civic use of the imagination)”啟發下看到了個體成長故事背后的社會政治內涵,對生命脆弱性的意識和對價值沖突的理解,對于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發展尤為關鍵。這一洞見在她對古希臘悲劇的解讀中得到充分展示。在她看來,“完美”的自我封閉性暗含了專制主義的意味,對“不完美”的確認則體現出一種開放與民主的立場。古希臘悲劇之所以讓柏拉圖這樣的哲學家倍感焦慮是因為它挑戰了一種和諧完美的世界觀,即“我們完全有可能徹底消除悲劇及其導致的價值沖突”這樣的觀點。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恰恰通過克瑞翁與安提戈涅的悲劇性的命運暗示了試圖化解矛盾無視沖突所付出的代價,因為“沒有沖突的人類生活,比起充滿了沖突可能性的人類生活來講,無論在價值和美感上都有所遜色”(The Fragility ofGoodness 81)。
現實感還是一種低調的理想主義。在此,必須把這種現實感與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所謂的“要現實”區別開來。現實感并不意味著向現實低頭與妥協,它在警惕烏托邦迷思的同時,依然有著超越現實的理想主義沖動。為此特里林用“道德現實主義”來凸顯這種現實感既非簡單的現實觀察,也非本能的道德沖動,因為它是一種“道德想象自由表現的產物”;此外,努斯鮑姆對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的區分同樣頗具啟示(Love's Knowledge 379-80):她反對那種旨在成為天使而徹底無視人性脆弱的那種外在超越,卻并不反對在承認人性有限前提下的內在超越。并非僅有浪漫主義藝術具有超越性,藝術的超越性也可以存在于對現實的肯定之中。
藝術正義論還體現于追尋更好的自我。除了與現實的關系之外,藝術與自我的關系也決定了藝術的精神形態。自進入現代性以來,藝術與自我的關系變得愈加緊密。諸如“真誠”“自白”“向內轉”等關鍵詞凸顯了自我在當代藝術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如果說浪漫主義時代的自我還具有某種普遍性的話,那么在當今時代,要對自我與自戀,真誠(sincere)與本真(authentic)作出區分幾乎喪失可能。在一個“獨自打保齡”的時代,當藝術與私人自我的關系變得愈加密切,對現實的不滿和對完美的烏托邦迷思往往源于“過于膨脹的自我”。如何認識自我的限度,如何去追尋更好的自我成為藝術正義論的另一重要方面。
對自我局限的意識,并維持其與世界之間的平衡成為藝術正義論的追求目標。在這個強調“真我”的時代,藝術先前被賦予的教育內涵早已消耗殆盡。“反叛的自我(opposing self)”在當代藝術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在《我們所交往的朋友》中,文學批評家韋恩·布斯試圖表達這一看法:對不完美世界的徹底反抗是以犧牲“友情”、付出自我成長為代價的:為了確認自我的真實,我們需要不斷地移除異質于自我之物,將真實性從外在的偽裝之中解放出來。于是在文化中形成了一種僵化了的二元對立觀念:“留給自我的只能兩種可能的路徑:要么讓你的個體向某個集體屈服,要么通過反抗來保存自我”(The Company We Keep 240-41)。布斯以詹姆斯·喬伊斯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為例指出,在這部二十世紀現代主義典范之作中,當代讀者很容易把主人公斯蒂芬視為英雄,因為斯蒂芬為了最終成為藝術家,不惜付出與他人以及共同價值決裂的代價,并以形象的語言道出了薩特的那句“他人即地獄”(246)。與之相反,布斯在簡·奧斯丁的小說中(如《愛瑪》)看到的是主人公自我的外在反思和對生活價值的堅守。如果說我們幾乎難以區分喬伊斯與其筆下的斯蒂芬的話,那么在“隱含作者”奧斯丁與愛瑪之間,讀者能夠明顯覺察出一種“距離的控制”,這種控制不僅是技巧層面的,更是道德層面的。
此外瑪莎·努斯鮑姆則發現厭惡感(disgust)常常成為許多當代藝術作品的基調,在她看來,這種情緒與另一種具有倫理感的憤慨(indignation)不同。那些懷著厭惡之情叛離世界的藝術家在那個意義上并非政治意義上的存在,而是作為浪漫式的反社會者而存在(Hiding from Humanities 105)。在當下大眾文化語境中經常出現的“藝術憤青”,它的憤怒并非基于這種倫理意義的憤慨,只是私人意義上的“憤世嫉俗”。因此在她看來,真正的好藝術需要從這種厭惡的情緒中擺脫出來。
除了對自我的局限有所警惕之外,藝術正義論更強調藝術喚起人們追求更好自我的愿望。這一充滿古典意味的訴求在馬修·阿諾德一再得到強調:作為文化的精華,藝術的意義在于“讓每個人變成一個更好的自己”:一是藝術能夠引領人性從普通自我走向優秀自我,二是追求更好,而不是最好才是人生的目標。因為“在人類全體普遍達到完美之前,是不會有真正的完美的”(阿諾德162—63)。 布斯還提示我們,偽善(Hypocrisy)一詞在古代并無貶義,意為“在舞臺上扮演角色”,從一種性格變成另一種性格,而“人格”與“偽善”是一對近義詞:演員通過“hypocrisy”來表演人格;作者通過創造人格來扮演角色,讀者則通過再創造來表演角色。簡而言之,一種特定的人格扮演是我們培養人格的方式。布斯援引桑塔亞納的話指出,重要的不是自我本身,而是自我的成長:“如果我能夠分享那些角色,那要比尋找獨一無二的自我更為重要”(The Company We Keep 259)。但正是當代藝術文化在對偽善文化的大清洗過程中,讓讀者或觀眾在藝術欣賞中越來越喪失角色認同與扮演的機會。如今為了追尋真誠,抗拒偽善,我們執著于一個反叛的自我,不但無法實現自我成長與完善的倫理目標,而且還陷入到難以自拔的自戀境地之中。無論是現代文學對人物的抽象化塑造,還是藝術的“去人性化”,都使藝術失去了人性教育中最重要的途徑,我們也不再能與藝術作品進行“友情”意義上的交流。
綜上所述,藝術的烏托邦與正義論兩種維度代表著對待世界的不同態度。透過藝術烏托邦的視角,人們會認為現實世界是極其糟糕的,人在現實世界中會出現“異化”,人若要回歸完整性就需要逃離或反抗現實。藝術烏托邦的實質在于,它以預言的方式掌握了完美,或認為完美的世界會在反抗與解構的過程中如彌賽亞那般突然降臨。在現實中不可能出現完美,這種完美只能出現在彼岸或革命之后現實的廢墟之上。正義論則有所不同,這種態度以為,世界是存在缺陷的,有的缺陷在于世界本身,有的缺陷則在于人的欲望。人生不可能通過逃離現實獲得幸福,恰恰現實才是幸福的前提。現實的確會導致人性的異化,但克服異化同樣需要站在現實的地平線上。它的理想主義實現于基于現實之上對善的“渴求(aspiration)”;其對完美的理解一直是在“追尋之中”,但在這一追尋中,人們更需要坦然地面對現實的不完美。
需要指出的是,這兩種藝術維度的存在,并不意味著理想與現實的截然二分。對正義的向往本身也是一種理想,在這個意義上,理想同樣也是另一種現實。我們之所以要對烏托邦保持警惕,是因為理想有時候朝著背離現實或否定人性的方向發展,它會站到了現實的對立面。事實上要對此做出有效的辨別需要一種來自于經驗本身的實踐智慧;強行在理論上制定標準,結果恐怕只會是一種刻板的教條主義。
周一,美國市場開市,中國還是假期,看到了雷曼破產,中投風控部工作人員,挨個打電話給自己的分布在全球的投資經理,尤其是幫助中投管理貨幣市場基金的經理,詢問在他們的投資組合里,是否有雷曼的債券?果然,Primary的基金經理回復,他們資產池中有4%的倉位在雷曼債券上。該基金全稱Reserve Primary Fund,在其持有人名單上,中投公司旗下的Stable Investment是最大持有人,持有份額折合市值約54億美元。
結語:“種植我們自己的花園”
與國外相關研究的豐富相比,國內側重于藝術正義論視角的相關研究比較稀缺。不少學者從政治浪漫主義的角度對當代藝術及其理論作過批評,認為問題出在它將完美主義的評判標準用在了并不合適的政治領域,并未對烏托邦維度之外藝術的其他可能性做進一步探討。尤其是在當代藝術如此深入介入政治的情境下,藝術與政治已經難以切割。在批判政治浪漫主義(政治的審美化)的同時,藝術烏托邦問題(審美的政治化)同樣需要反思。在為數不多的研究中,崔衛平與徐賁的相關研究值得重視:比如崔衛平在《世俗世界的美學》等文章中試圖區分出一種與超越性美學不同的世俗美學。徐賁在探討漢娜·阿倫特的思想時,指出阿倫特對悲劇的理解體現了一種面向公民教育的維度。但總體而言相關研究方興未艾,有待學界的共同關注與深入推進。
強調藝術的正義論,并非徹底否定藝術烏托邦的意義,也無意放棄夢想與反抗作為藝術的價值屬性,而是反對以烏托邦的名義放棄對現實世界進行認知與改造。藝術的正義論提示我們:現實社會并非理論家所謂的“牢籠”“監獄”或者“景觀”那樣簡單,由于現實本身的復雜性、困難性和多樣性,對它的改進永遠需要審慎的思考與充滿艱辛的實踐。在此意義上,藝術需要承擔思想與實踐的壓力,而不是滿足于制造“一些認知上的不和諧音,以此表明我們的世界周圍有些事情不對勁”(Heath 7)。而這個時代的藝術,恰恰是把“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天賦的人從思想中趕出來,趕進一個姿態的王國,在那里最任意的就是最真實的”(巴尊 131)。
在此意義上,伏爾泰意義上的“花園”可以彌補“伊甸園”(“黃金國”)的缺失。作為“花園”的藝術既讓我們明白世界的不完善是生活的常態,也讓我們充分警惕自我的局限。“花園的意義可為我們提供一份人生的憂思。放棄這個世界的代價在于放棄我們作為人之為人的價值。在伊甸園中,一切都為他而存在”,而在花園之中,是“他為一切而存在”(哈里森 9—10)。人只有在并不完美的花園中才能真正認識并理解人之為人的的脆弱與責任。
人是生而注定受苦,但也有責任去凌駕這些痛苦。人生是一場船難,但我們仍然可以坐在救生艇上面好好高歌;人生是一片沙漠,但我們仍然可以在自家的角落經營一座花園。高談闊論是怡人的,但只有能把我們導向責任和激進潛能的高談闊論才是有益的。如果我們對責任沒有清晰的概念,行動便會變得不負責任,如果我們對自己的潛能沒有認識清楚,行動就會脫離現實。(蓋伊242)
正如彼得·蓋伊的這段話所說的那樣:除了烏托邦之外,當代藝術及其理論更有理由去“種植我們自己的花園”。
注釋[Notes]
①比如楊絳在作品《洗澡》中就引述過這句話。
②在藝術策展方面光是中國內地就有:2016年3月27日在中國烏鎮舉辦的“烏托邦·異托邦:烏鎮當代國際藝術邀請展”;2014年11月在中國廣州舉辦的“桃花源|反烏托邦:當代國際藝術展”;2014年9月中國南京舉辦的“烏托邦狂想曲”主題展;2015年11月在中國三亞舉辦的“島嶼的烏托邦:三亞當代藝術邀請展”;2015年7月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舉辦的“烏托邦的尺寸:重讀中國當代藝術”等等。相關著作如《當代藝術的危機:烏托邦的終結》《玩藝術:一個人的烏托邦》《搖滾烏托邦》《世俗化與文學烏托邦》等等。
③自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提出“歷史的終結”以來,西方左派重新集結力量來塑造烏托邦的想象。比如拉塞爾·雅各比的《不完美的圖像》旨在從政治烏托邦的廢墟中拯救“烏托邦精神”。在召喚這種烏托邦精神的過程中,藝術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因為藝術能夠把人類從異化或奴役的狀態中拯救出來。參見拉塞爾·雅各比:《不完美的圖像》(姚建斌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
④“異托邦”由米歇爾·福柯提出,它被描述為一個在沒有霸權作為前提下存在著的空間,它既是一個物質意義上,同時也是精神意義上的關于“他者”的空間。美國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沃爾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對此有個很精煉的概括:“在烏托邦中所有一切都是好的;在歹托邦里所有一切都是壞的;在異托邦中所有一切都是不同的。”但這種差異并不能掩蓋“異托邦”與“烏托邦”同樣試圖以逃離或反叛的方式來面對現實世界。參見Mead, Walter Russell.“Trains, Planes, and Automobiles:The End of the Postmodern Moment.” World Policy Journal12(4): 13-31
⑥盡管有不少學者一再指出,當代的藝術實踐早已喪失共通理念,藝術烏托邦也早已終結。比如拉塞爾·雅各比的《烏托邦之死》、米肖的《當代藝術的危機:烏托邦的終結》等。但“烏托邦”仍然可以令人費解的方式得到追捧。
⑦ 參見 Heath, Joseph and Andrew Potter.Nation ofRebels:Why Counterculture Became Consumer Culture.Harpercollins Ltd.2005.
⑧吳亮:“作為自我反諷的批判與朗西埃的不滿”,《書城》9(2013): 59—67。
⑨崔衛平在《海子、王小波與現代性》一文指出:“海子和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是‘鄉愁詩人’、‘鄉愁派’,那么,叫王小波‘地平線詩人’吧。他所站立的那個位置,他所釋放的某種能量,他所提供的新的經驗和視野,正像地平線一樣,代表著這個世界之外的另一個世界,那是更加自由、更加有趣、更加富有可能性,也是同樣優美的世界。”
⑩徐賁指出阿倫特把“故事看成是一種內在過程,人的行為一定會有不理想,不能預期的后果。說故事就是一個學習坦然面對的過程。阿倫特用“reconcile”(妥協)一詞表述“坦然面對”,它不是指被動的接受或妥協,而是指以理解來接受事物的真實性。說故事的道理和政治自由的道理一樣的。政治自由不是指人際關系為人的各自行為設界,而是指人際關系讓不同的人有了“妥協”的機會。:阿倫特把悲劇納入到公民教育的議題之中,(《公民政治和文學的阿倫特》,《人以什么理由來記憶》(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第59頁)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馬修·阿諾德:《文化與無政府狀態》,韓敏中譯。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
[ Arnold, Matthew. Culture and Anarchy. Trans. Han Minzhong.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Press, 2008.]
瑪麗琳·巴特勒:《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動派:1760—1830年間的英國文學及其背景》,黃梅等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 Butler, Marilyn. Romantics, Rebels and Reactionaries:English Literature and Its Background 1760-1830.Trans. Huang Mei.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98.]
雅克·巴爾贊:《我們應有的文化》,嚴忠志等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
[Barzun, Jacques.The Culture We Deserve.Trans.Yan Zhizhong.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2009.]
以賽亞·伯林:《現實感》,潘蓉蓉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1996年。
[Berlin, Isaiah.The Sense ofReality.Trans.Pan Rongrong.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1996.]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原理》(第一卷),夢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
[Bloch, Ernst.The Principle of Hope Vol.1.Trans.Meng Mei.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2.]
Booth, Wayne. The Essential Wayne Booth.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 The Company We Keep: An Ethics of Fiction.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卡爾·施密特:《政治的浪漫派》,劉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Schmitt, Carl.Political Romanticism.Trans.Liu Feng.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方曉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年。
[Dickstein, Morris.Gates of Eden: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Sixties. Trans. Fang Xiaogua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7.]
Shaw, Bernard.Man and Superman: A Comedy and a Philosophy.Westminster: Archibald Constable & Co.,Ltd., 1903.
詹姆斯·埃爾金斯:《繪畫與眼淚》,黃暉譯。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0年。
[ Elkins, James. Pictures&Tears.Trans. Huang Hui.Nanjing: Jiangsu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0.]
彼得·蓋伊:《啟蒙運動》(上),劉森堯等譯。臺北:立緒文化,2008年。
[Peter, Gay.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1.Trans.Liu Senyao, etal.Taipei: Lixu Culture, 2008.]
Heath, Joseph and Potter, Andrew.Nation of Rebels: Why Counterculture Became ConsumerCulture.Harper Collins Ltd., 2005.
羅伯特·波格·哈里森:《花園:談人之為人》,蘇薇星譯,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
[Harrison, Robert Pogue.Gardens: An Essay on the Human Condition.Trans.Su Weixing.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House, 2011.]
盧卡奇:《小說理論》,燕宏遠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Lukacs, Georg.The Theory of the Novel.Trans.Yan Hongyuan,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2012.]
Mitchell, W.J.T., ed.Art and the Public Sphe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赫伯特·馬爾庫塞:《審美之維》,李小兵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
[ Marcuse, Herbert.The Aesthetic Dimension.Trans.Li Xiaobing.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2001.]
Nussbaum, Martha.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Love's Knowledge: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Hiding from Humanity: Disgust, Shame, and the Law.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阿瑪蒂亞·森:《正義的理念》,李磊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
[Sen, Amartya.The Idea of Justice.Trans.Li Lei, et al.Beijing: Chines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2]
弗里德里希·席勒:《審美教育書簡》,馮至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Schiller, Friedrich von.Letters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Trans. Fen Zh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萊昂內爾·特里林:《知性乃道德職責》,嚴志軍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
[Trilling, Lionel.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Trans.Yan Zhijun.Nanjing: Yilin Press, 2011.]
雅克·巴尊:《古典的,浪漫的,現代的》,侯蓓等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
[Barzun, Jacques.Classic, Romantic, and Modern.Trans.Hou Bei, et al.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2005.]
朱麗婭·克里斯特瓦:《反抗的意義和非意義》,林曉等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9年。
[Kristeva, Julia.The Sense and Non-sense of Revolt.Trans.Lin Xiao, et al.Changchun: Jilin Publishing Group,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