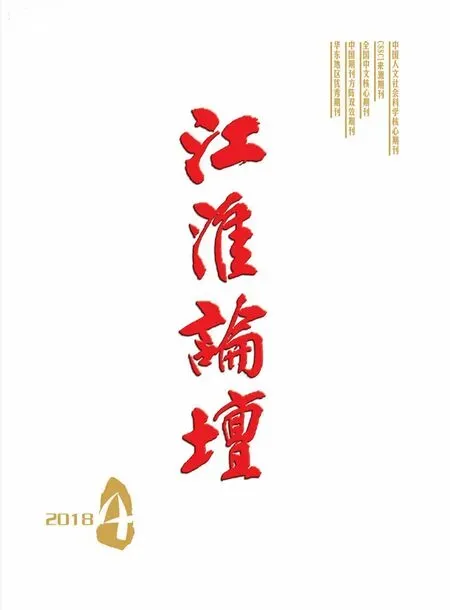荀子“法后王”說續辨*
——兼及其所蘊含的禮治精神
劉 亮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北京 100875)
荀子“法后王”說,見于《荀子》的《不茍》《非相》《儒效》《王制》《成相》等篇。從其文義釋讀到思想闡發,前賢今人之所以高度關注,是因其說實為探究荀子思想中禮法制度與君權關系的一個有效角度、討論荀子禮治思想之基本特征的關鍵切入點。
一、前賢觀點
針對荀子“法后王”說的研討可溯至漢代。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云:“傳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將后王解讀為近世之王,法后王為取法近世之王。楊倞承襲此說,釋《不茍》篇“百王之道,后王是也”云:“后王,當今之王。言后王之道與百王不殊。”釋《非相》篇“欲觀圣王之跡,則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云:“后王,近時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圣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于舊聞。而時人以為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后可,斯惑也。”17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對此多予質疑,并提出新說。新說暫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觀點,試圖通過在歷史過往中探究所“法”之對象,來明確“法后王”含義。依照對象之異,大略區分如許:(一)劉臺拱、汪中、豬飼彥博、王念孫、杜國庠、吳茹寒、李滌生等持“文武”說。論其理據,杜國庠先生列舉《成相》的“文武之道同伏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李滌生先生則稱“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恰與《非相》“后王之跡”粲然可知相一致。 (二)物雙松、錢大昕、久保愛、冢田虎、朝川鼎、郭沫若、馮友蘭、熊公哲等持“周王”或“周道”說。朝川鼎以《非相》“知周道”以及“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作為依據,郭沫若則將“周道”說建立在他對荀子世界秩序思想的理解上,他主張荀子的“宇宙觀或世界觀是一種循環論。一切自然界和人事界的現象雖然是千變萬化,但變來化去卻始終是在兜圈子,結果依然是沒有變”。(三)章太炎先生持“法《春秋》”說,旨在彰顯荀學與孔學的傳承關系,以申“尊荀”旨意。其云“綦文理于新,不能無因近古”,言“法后王”是針對典章制度的創新,大凡創新,對舊制又不免有因循。(四)劉師培倡“守成之主”說。 其言“‘後’、‘后’古通。后,繼體君也(見《說文》);蓋開創為君,守成為后,開創之君立法草創,而成文之法大抵定于守成之君;如周之禮制,定于周公、成王是也。《荀子》所言后王,均指守成之主言,非指文武言也”。(五)韋政通、張亨等學者持“積累”說。張亨先生解釋稱,“經過歷代的累積,當然是后來居上,粲然大備,照理說只要取法后王就夠了”。 (六)梁啟雄、李中生、周群振、陳禮彰等學者,提出以“不變之法”變“可變之法”說。梁先生釋《天論》篇“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云:“荀子法先王,又法后王。大概在道理原則上他是掌握著不變的道貫,這是‘原先王’;可是,在法術和政教上他是隨時靈活地變革的,這是‘法后王’。”李先生認為,荀子主張穩定不變的道貫與某些重要的具體禮法是不可變的,而不重要的具體禮法,則可循道貫而變。周先生提出“以先王所示之價值理念為宗綱,以后王所成之具體實務為榜樣”。陳禮彰先生亦承此說,謂“永恒不變的道理原則以先王為法,與時俱進的文物制度則以后王為法”。此種觀點尚有未盡詳之處,如,為何先王后王分而論之,卻不言徑自依據先王治道而變革當世之法;由此可變的、不可變的規則所組成的結構,可否進一步推知“后王”乃至“法后王”的精確內涵與外延等。(七)廖名春先生提出“成王康王”說。其言“周之禮制,亦即周道,其基本框架成于周公、成王之時”,而成王、康王作為“西周盛世之君的代表”,即荀子所謂“后王”。這一類釋義的具體觀點雖各有異,然綜合而言,皆將“法后王”指向先代圣王的各類治道法度。根據此類師法往昔圣王的釋義,又能夠 (直接或間接地)推出“法后王”說對特定舊制的保守態度、重視歷史經驗等特征。
第二類觀點,釋“后王”為荀子所處時代的天子。如吉聯抗釋《王制》之“后王”為“當代的帝王”等。這類釋義可體現“法后王”對荀子所處時代特殊性的肯定,以及(近于法家諸子的)是今非古、“世異備變”之傾向。
第三類觀點,將“法后王”視作對未來的期許,僅是理想狀態,不存于歷史或當下。章學誠稱“法后王”有“欲來者之興起”之意。羅焌先生援引《正論》“天下歸之之謂王”以及《正名》“后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提出“后王所定禮制,非襲三代之禮…… (后王)非商周之王……乃指后世為天下歸往之王,非謂后世以君位世及之王耳”。趙儷生先生亦主張“荀子的‘法后王’,并不是已經找到哪一個新的崇拜對象,他只是說,過去對周制和文、武、周公的崇拜太過了”,言荀子“后王”之說乃是對周制的否定。根據此類釋義,“法后王”之說有排斥一切舊制度的傾向,而成一種極具革命性的學說。
根據上述聚訟,“法后王”釋義的細微差別,亦將招致其所蘊思想的相為天淵。故針對其說的研討,釋義問題最為基礎,必先予明確。
二、再釋“法后王”
討論“法后王”含義,需留意不同角度:
首先,“法后王”應指向原則、制度層面,如前賢所指出。“法后王”之“法”,意為取法或師法。法,古字有作“灋”者,《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有效的刑法,內容須具備概括性,針對的定是一類具備某些構成要件的行為、事態,而非特定的、獨一無二的行為或事態。循著這一特征,“法”字引申為取法、師法之意,表示按照某種原則處置某一類事態。如《孟子·公孫丑上》云“則文王不足法與”,《韓非子·五蠹》云“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等。《荀子》文中各處“法后王”之“法”,即屬此種含義。取法、師法的對象,為適用于某一類事態的概括性原則,即使面對“后王”的任何特定的舉措,也只有從中提取出能夠適用于具有相同特征的事態的概括性原則,方可言取法、師法;反之,純粹特殊的、完全無法提取概括性原則的特定舉措,則無取法的價值。亦即“法后王”所“法”之對象,是針對處理具體事態所循的成文或不成文(慣例性)的,抑或在具體事例中提煉出的具有概括性的原則 (如典章制度等),而不論這些原則處于政治、經濟、文化等人類社會的哪一方面。《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后王”中,“道”與“法”互文修辭,即在強調(此處用作名詞的)“法”所處的原則、制度層面,及其所具有的概括性。
其次,對《荀子》而言,“后王”的禮法制度粲然可知。《非相》云:
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故曰:欲觀圣王之跡,則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
其明言“后王”之跡為“圣王之跡”(圣王的禮法制度、政治舉措)中能夠清楚知悉的部分。“先王”的禮法制度,則處于久而息絕的狀態,無法詳知。因此,對《荀子》而言,后王、先王的區別在文物制度是否可知。
再次,“先王”治道可經由“后王”禮法制度推知。對“后王”“法后王”的研討不得不論及“先王”“法先王”的含義,因《荀子》提及“后王”的文本,明里暗里皆相對“先王”而言。“先王”即歷史上那些文物事跡湮滅無聞的圣王,有如前述。其跡湮滅無聞,如何“法先王”?《荀子》的回應,是通過后王粲然之跡推知先王治道,然后再予取法。《不茍》云:
故君子……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審后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
其言有“術”,可由已知信息推求未知信息:后王的禮法制度即屬已知,且是探究先王等往昔圣王的途徑。具體方法,可透過《荀子》的相關表述窺見。《不茍》《儒效》與《天論》各篇,均將此推知術建立在荀子學派變貫并舉的史觀上:一方面承認歷史具體情勢的變化,如《儒效》言及“萬變”、《天論》言及“應變”等;一方面指出歷史流變過程中有一以貫之的內容,亦即人類社會某些更為深層的、更為基本的秩序與原則,如《儒效》所謂“百王之道,一是”中的“一”。因而,推知之術就是在歷代后王粲然可知的禮文制度中考求此類穩定的內容,再將后者推至先王的時代。此法頗為粗疏武斷,其推得的先王禮法,僅限“百王之所同”領域內的少許重要原則。與上述推測相符的是,《儒效》云“法先王,統禮義,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是大儒者也”,其以能持博之“淺”、能持萬之“一”等形容可探究而得的先王治道,彰顯后者地位緊要而篇幅簡短。
最后,后王的禮法制度,不僅可據以推知先王之跡,且可徑自指導當下各類政治舉措。“法后王”的具體方法,頗似推知先王之法。《天論》云:“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引文(基于前述變貫并舉的史觀)指出,文物制度中應對具體情勢的內容需隨具體情勢的變動而變動。人類更為基本的秩序——保持高度穩定的“貫”,則需堅持。統攬《荀子》各篇,“貫”以其(在禮法制度的結構中所處)地位的不同,又可分為兩種:一為“變”(隨時勢變動)的部分在變動過程中所遵循的更高級的、穩定的原則,如《禮論》“給人之欲”等;一為不同時代文物制度中始終穩定的具體內容,如《禮論》云“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此喪禮即屬“貫”中的一項具體內容而非指導禮法變革的高級原則。面對變、貫二者,“理貫應變”是荀子因循損益各類既有禮法、原則的方法。理貫,是指考察、梳理禮法歷時性流變中一以貫之的穩定內容;應變,是指禮法損益等應對當下具體事務之舉;理貫以應變,即以穩定不變的高級原則指導當下具體舉措,以應對新的具體情勢。面對那些“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的具體條目,新舉措亦應謹慎遵循——這就是“法后王”的具體方法。“法后王”的含義,則為從后王粲然可知的禮法制度中探尋穩定不變的部分,進而以后者為依據,指導當下各類舉措。反之,違背或無視此一原則,托名先王而炮新規,非變更禮法制度的正確方法。如《非十二子》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韋政通先生釋曰:“荀子并不以法先王為非,只是嫌其只知‘案往舊造說’,不能就先王之遺緒而知其統類,以充分發揮其功能。 ”韋先生所言“知其統類”,即指向此種以貫統變的結構。
根據上述討論,可進一步明確“法后王”的某些特征:
其一,“后王”是過往的圣王,不是當代或未來的圣王。《非相》所謂后王之跡的“粲然”,是“以貫應變”的方法所決定的。具體言之,以貫應變首先需要明辨貫、變,貫、變僅能從歷史上粲然可知的禮法制度中察見。《天論》明言“貫”的探求方法:“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郝懿行釋 “道”為“禮”,道貫即禮法制度之“貫”。“貫”既為歷經漫長的時代流變而保持高度穩定的禮法制度或原則,那么,只有通過圣王那些清晰可辨的禮法制度,或因革典章的舉措,后人才有分辨變、貫的可能。在此可知性的角度上,“后王”須是過往或當下的圣王。然,荀子卻不認為其所處“當下”存在“圣王”——由《正名》所云“今圣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可證,故“后王”僅限于往昔圣王:蓋(相對前儒所謂唐虞)禮法制度可知者多在近古,故言“后王”。前賢以“未來之王”界定“后王”,難點正在可知性上:未來圣王的禮法制度無從知悉,“法后王”與《荀子》所指責的“誣欺”(語出《非相》)、“造說”(虛構無事實根據的主張,語出《非十二子》)本質上又有何差異?而以“當代之王”釋“后王”,又與前引《正名》之文正相抵牾。
其二,“后王”泛指故事粲然的列位圣王。該詞有似西文的復數形式,而不以特定朝代或個人為界限。以貫應變的主張是將“禮法如何因革”這一重大問題,訴諸對歷史流變過程的篩選:在這一有待考察的歷史過程中,不同時期的典章與舉措,內容愈充分、愈詳細,“貫”也就越有可能被發現;在往昔圣王禮法制度可知可考的前提下,時間的跨度越大,“貫”也就越有可能被發現。是以,一個承載諸多禮法制度的時間縱深,是考求貫、變的必要條件。而“后王”的外延,應將禮法制度粲然可知的列位圣王悉數囊括:在禮法制度可知可考的情況下,放棄取法某一歷史時段的圣王,是違背常理的。而《儒效》“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后王謂之不雅”與《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后王”中,“三代”與“后王”皆文義互足,可印證此說:其泛言“三代”而不言“周”,蓋慮及“后王”的時間界限未必狹如后者。他篇稱美周制,可證周制屬“后王”范圍,卻不足證“后王”僅限周制。如前引“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觀千歲,則數今日”等,是為解釋“以近知遠”而列舉極端,打出形象的比方。又如《正名》云“后王之成名,刑名從商”,“刑名從商”為“法后王”不限于周制的明證。“后王”不受特定朝代限制,更非特定人物,其限定因素應僅有王跡能夠知悉。故如“本朝圣王”說、“周王”說、“周初列王”說、“文武”說、“周公”說等,以特定王朝或個人作界限,有將“后王”(在未有充足證據的情況下)拘于狹小外延的風險。
其三,“法后王”兼具因、革兩方面意義。“法后王”的具體方法既為“以貫應變”,“貫”自屬于對舊制舊物的因循,循舊的目的,卻在于應對新問題。《儒效》云:“法后王而一制度。 ”“法后王”與“一制度”對舉,以二者皆強調禮法制度的修建。立法改制(就其性質而言)既為創建新規則,又需取法舊制度,有如上述。此即章太炎先生“綦文理于新,不能無因近古”,以及牟宗三先生“就禮憲發展之跡,本其粲然明備者以條貫之,以運用于當時”所強調:若對舊制度全無因循,則應排斥師先圣、法先王后王;若現實無異于舊情勢,則沿襲舊制即可,“法后王”同樣失去價值。此亦前賢僅言革不言因,與只言因不言革諸說的難點:如趙儷生先生之“理想說”,是將“法后王”置于作為一個整體的舊制度(“周道”)的對立面上,“法后王”對“貫”的探求、對舊例的因循,在其解釋中全然無法體現。
綜上,“后王”泛指禮法制度或統治舉措可供察考的往昔圣王;“法后王”是主張從這些圣王的舊制中發現穩定不變的原則,再以這些原則指導當下的行動。如果說荀子學派試圖創建一學說系統,以為變動不居的各個時代始終如一地遵循,那么,“法后王”因其超越特定時代的普遍價值,或可成為此系統的一項重要內容。
三、“法后王”所蘊含的禮治精神
本文所謂“禮治精神”,是指(在今天看來)《荀子》禮治思想中那些具有超越特定時代之價值的原則與宗旨;所謂《荀子》禮治思想,是指《荀子》文本所彰示或蘊含的以禮義為價值評判基礎的政治思想。
某種意義上,“法后王”一說所蘊含的禮治精神,突出表現為針對統治者損益禮法、頒布命令等一切統治舉措而樹立的“更高的原則”。與那些主張統治者 “不和于俗”、“不謀與眾”(《商君書·更法》)的原則相比,荀子學派強調各類政治舉措師法歷代圣王,自含有以前述“更高的原則”約束統治者的意圖。首先表現在力求“變外之貫”(歷史上長期穩定的禮法內容)立于統治者支配權之外,使某些基本的社會秩序不因統治者變換不居的命令而損毀。此類不可改動的禮法所編織起來的規則、慣例系統,不論內容是否細致完備,(較全無此類規則而言)皆可于一定程度上為人民設置一相對穩定的、可供預期的規則框架,人民可據此框架規劃生活。其次,探究“變中之貫”(具體禮法損益所循的高級原則)以指導各類統治舉措,以求統治者能夠遵循此類原則,而非全然放縱一己私意。這一為統治者樹立更高原則的創舉,蓋因彼時代各國所流行的“變法”運動而起,以防傳統禮法所貫徹的“仁愛”等基本宗旨于此一時代凋零。合此兩點,“法后王”之說以歷史過程對文物制度的篩選,來約束統治者依照己意篡換禮法制度;力求禮法基本的框架與精神獨立于統治者意志之外,力避片面強調變法而無視變法行為本身亦應予規范,防止(一如法家諸子所倡的學說那般)使禮法制度淪為統治者弄權的工具。
進而言之,如何責成統治者在各類行動中遵循此種更高的原則?《荀子》將此問題置諸責成統治者遵循禮義的整體框架,此框架先以統治者是否遵循禮義來評判其統治的正當性,進而鼓吹對失去正當性的統治者予以征誅。
就前一步驟而言,《不茍》宣稱“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統治的正當性僅源于遵循禮義,不符合禮義的統治,即使維持著某種秩序,仍當劃歸“亂”。此一判斷標準,非對即錯、非治即亂,無中間地帶,與《慎子·威德》所謂“法雖不善,猶愈于無法”正相對立。在這一點上,荀子竟稍有近于西方自然法學“惡法非法”的性格。而慎子之說,流于無原則的推崇“法”(實為統治者的命令)的效力,使“法”瀕于人主支配臣民的工具。
就后一步驟而言,《荀子》主張武力攘除喪失正當性的統治,意在以外部威脅迫使統治者遵循禮義秩序。如《正論》云:“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兇,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以桀紂與湯武為例,言桀紂之流喪失統治的正當性而成獨夫,自宜誅滅。以武力摧滅背離禮義的統治,成為荀子之說維護禮義秩序、責成君主遵循禮法的終極主張。
于是,荀子學派以“法后王”責成統治者守禮,以合乎禮義與否評判統治的正當性,以湯武革命除亂復治,勾勒出一幅禮義至上的秩序圖景,成為其政治思想的精神所在。然而,這一思想構造遠非綿密無缺:首先,“貫”的內容尚未清晰具體,招致那些“穩定的高級規則”在實際操作中易于為統治者隨意剪裁取舍,而旁人難以判斷監督。此種剪裁取舍,將使禮義成為統治者的粉飾而非約束,如梁啟超先生所言“禮之名義為人所盜用,飾貌而無實者,吾儕可以觸目而舉證矣”。其次,除將湯武革命作為外部的責成因素脅迫統治者就范之外,在和平的政治運作中未能設置有效的制約力量。牟宗三先生評曰:“位愈高,控制之外力愈微,一旦將此超越之者拆穿而無睹,則君即成全無限制者;禍亂即從此生;而革命、獨夫、自然天命之競爭,亦隨之必然來矣。故古人對君除責之以自律外,蓋無他道。”其言包含荀學在內的中國古代各派思想,終不能以和平方式責成君主遵守禮法,故不得不依靠自下而上的革命,或可遇不可求的王者之兵。傳統社會是以無從逃脫和平與戰亂相互交迭,陷于“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治亂循環。
總之,古今學者聚訟紛紜的荀子“法后王”說,實是主張以歷史上高度穩定的禮義原則指導當下各類政治舉措。其所蘊含的禮治精神,突出展現在為統治者的行為制定更高的規則上。其至關重要的價值,在于以遵循禮義評價統治的正當性、以武力攘除不正當的統治者等觀點,共同建立起荀子學派禮義至上、君權須遵循禮義的思想結構。這一禮義至上的秩序圖景,為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精華所在。
注釋:
(1)觀點轉引自陳禮彰《荀子“法后王”說究辨》。
(2)《章太炎全集》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6-7。 “《春秋》約而不速” ,鄙意法《春秋》與《勸學》抵牾。
(3)韋政通:《荀子與古代哲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14-15。 韋先生雖與前文“周道”說重疊,然其強調“周道乃是百王之法累積損益而成,故后王足以代表百王之道”。他對積累的強調與單純“法周道”說有所差異,故將其列入此處。
(4)丁福保主編《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臺北:鼎文書局,1983,“法”字條目。
(5)“三年之喪”等具體條目能夠穩定不變,是因有“不變易”的統貫精神。《禮論》對此多有說明。如“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