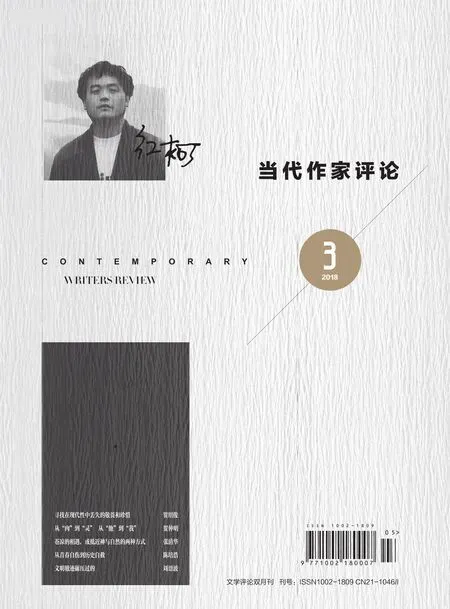文明轍跡碾壓過的
——陳昌平小說世界管窺
2018-11-12 22:01:02劉恩波
當代作家評論
2018年3期
劉恩波
人是文明的產物,也是它的祭品。每一種文明的形成、裂變和拓展,都是以犧牲或者打磨砥礪無數人的生命或者煎熬榨取無數人的血淚為代價的。而觸痛文明肌體上的任何一根神經,都會是歷史敘述或者文學敘事的強大的生命場。你是站在一代人的立場上審視一個人的命運,還是站在一個人的立場上反思一代人的生活,這里面的界限好像永遠難以厘定裁奪。尤其是小說,雖然屬于個體敘事,但其內核卻是歷史的發聲,帶著歷史的表情和音域,帶著歷史的喉結的蠕動抑或脈息,換而言之,小說家通過個體這一通道,從而找到了歷史不規則的心跳。當我走進陳昌平的小說世界,幾乎為他筆下觸摸到的人性傷痕、倫理失衡、情感崩潰、靈魂墮落……而獲得一種類似騷動的由衷回饋。但這種騷動,不屬于淚水,不屬于一聲嘆息,而是屬于那再也無法抑制的類似精神缺氧的窒息般的存在感。的確,他不再做道義上的審判,他撕碎了溫情脈脈的修辭學的偽裝,他讓我們看到了深淵,文明斷裂、精神不自由、非理性戰勝了理智、幻覺的美感抵押了嚴酷的生活實質。那是一個人的悲喜劇,還是一代人的荒誕劇,那是入骨痛徹的黑色幽默,還是根源于無法抗拒的命運本身而隨之帶來的靈魂抽搐、扭曲和變形?
這里我想首先指明,寫小說的人不見得會構筑一個屬于自己的小說世界。有的人寫了一輩子小說,但還是沒有形成個體性的目光、視角、立場、風格、形式感。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銀潮(2021年8期)2021-09-10 09:05:58
農村百事通(2020年11期)2020-06-27 14:05:13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作文周刊·小學一年級版(2016年42期)2017-06-06 22:20:27
全體育(2016年4期)2016-11-02 18:57:28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16年5期)2016-05-14 12:21:05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6期)2015-10-13 07:2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