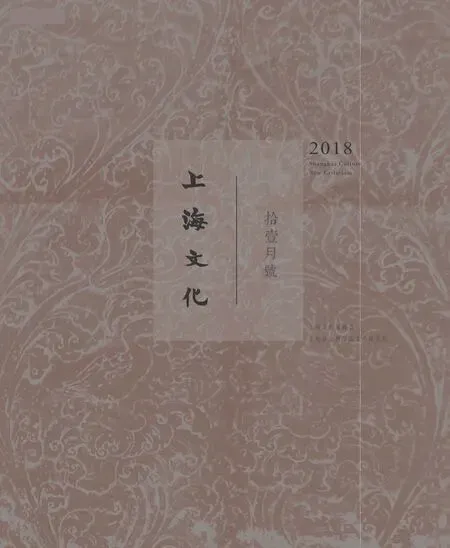今晚我是所有的人李浩《你和我》
許仁浩
術語乃思想的詩意時刻。這并不意味著哲學家必須不斷地對他們的專門術語做出界定。
——吉奧喬·阿甘本《什么是裝置?》
1
閱讀李浩,幾乎是一個涉險的過程,他的文本保有持續的緊張、顫栗,高強度的撕扯、絞殺、擠壓,以及沐浴在“光”(Light)中的祥和、純凈和豐盈,一旦被其拉入,你就無法逃逸那些詩行間迸生的引力。你能做的,就是繼續閱讀,繼續走上那條轉身即是深淵的山羊小道。所幸,當閱讀成為一種危險時,它也是最接近“透明的晶體”的時刻。
正如引語中阿甘本的那句話:術語乃思想的詩意時刻。但是哲學家并沒有義務不斷地對他們的術語做出界定。在詩人身上,這句話也有一定的共通性——如果我們把一本詩文集的名字稱為“術語”的話——詩人也沒有義務、甚至根本就沒有必要對自己的術語做出太多界定。但是,談論李浩的這本集子,我還是想從“你和我”這個“術語”介入。甚至,我們可以將“你和我”這樣一個聯合結構視為原點,而圍繞于其周圍的詩就是一個又一個的坐標,它們如同漫天星辰向同一個圓心反射著光。
顯然,“你和我”是帶有策略性的。通過“你和我”,李浩向讀者打開了萬象的內部,也呈現出“松軟的釘孔”。
李浩喜歡丹麥人說的一句話:“我的墓碑上只需刻上四個字,那個個人”。這可視為李浩精神圖譜的一幀投射,但就是這樣一個“向絕對靠近”的意志詩人,卻在使用“你和我”(一個看起來極為簡單的句法)勾勒自己詩文集的版圖,這著實是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李浩喜歡丹麥人說的一句話:“我的墓碑上只需刻上四個字,那個個人”
2
今晚我是所有的人
今晚我和大風雌雄同體
……
今晚我和北風一起與北風為敵
今晚我在甘蔗林里
娶閃電為妻
——李浩《今晚我是所有的人》
與《哀歌》和《還鄉》所受到的重視程度不同,談論李浩的人很少談及這首詩。這段經過我處理后的《今晚我是所有的人》,看起來就像一灣積蓄已久的湖水打開堤壩,隨之傾瀉出來的還有怒吼和嚎叫,但詩的原樣不是這樣的。原詩在情緒上有多處迂回,統合起來也就節制許多。我這么處理是想將“今晚我是所有的人”單獨擰出,并在“今晚我—— ”這樣一個大結構的統攝下,進入李浩。
昆鳥說,李浩是一個力量型的詩人,當然他的指向可能是內外多個層面。而我所看重的李浩的力量,主要有兩種:一者是主動進擊的覆蓋之力,再者是抽離過后的投射之力。
首先來看主動型的力量維面,和《今晚我是所有的人》類似,詩人的聲音總是在文本中占據絕對地位,而且從不易幟。不過大多數時候,李浩都做得相對隱忍(其實《今晚我是所有的人》也是),他內心深處拒斥“飛奔、狂叫、燃燒”式的武斷,因此他在處理主體力量的進擊時,會揉進多樣性元素,或是經驗的提純,或是沉思后的錘煉,進而賦予詩歌較強的綿延特質,以區別于引吭高歌。比如《雪》、《大雪》、《作品》、《挽歌》《個人史》、《困境》、《在詩里》、《書信》,都可以劃歸到這一序列,這些作品屬于李浩比較早期的作品。
長詩《消解之梯》是這一類型中的扛鼎之作。李浩在這首長詩中熔鑄了——我,“我”,吾——的三副面孔,這首長詩大多數片段語速迅疾,而作為動能主體的“我”則是這首詩得以推進的重要砝碼,這個代詞從起句就開口了—— “我的身上含著一滴人血,并且僅有一滴”,經由“感謝”,再經過七彎八拐的世間瑣屑,最終變為“這是注定的”的結果,“你完成/了我。我成為你寫作中那片失蹤的/荒漠。”顯然,這是一首“我之舞”的詩作,雖然節與節之間的邏輯、突然飛至的問句以及句群背后的具體所指都不那么透明,但是借由“我”的控制,以及語言和形式的左右護法,使這首詩得以成功續航。
再看一首《舌根》:
必須從雪開始。劃破長空的流星
已經回到黑暗的膠囊中。
日光下是歸鄉的茫茫雪景。
懸崖上的驚訝之樹,必須
豎起額頭。必須和一個雷,細數
荒漠中的手鐲,沙丘上的皮膚。
風中的血液,河流的唾沫,
必須在舌根的喑啞區域蔓延。
必須靜靜地說話。當你聽她時,
你必須仰望,雁陣也必須飛起。
“舌根”被詩人解讀為“語言之根”。但更引我注意的是,詩人主體在這首詩中所展示出的覆蓋之力。從擇定“必須”這個詞開始,詩人就明白自己將要抵達哪里,換句話說,李浩是在勘透了“舌根”之后才進行這首詩的寫作的。“必須”帶有基督教精神強大的統治力,也正是因為這個詞,《舌根》獲得了自己的溫度和顏色。“我”在這首詩中雖然沒有露面,但通過“必須”,他覆蓋了主體要言說的所有意義。即使面對“必須仰望”的“她”,詩人在敘述的語勢上依舊沒有易轍,而是從容不迫、一以貫之,最后佐以果決的尾音。
如果說這種顯見的主動進擊,只能在李浩的一部分詩中窺見端倪,那么抽離過后的投射之力則是李浩詩歌生產的主要范型,而且這種抽離后的超拔,正得益于主體底座的不竭動能。
李浩的 《挖鱔魚》、《花冠》、《引入記憶》、《情歌》、《時間之思》、《一再地》、《一個人》等一批詩作,都屬于在抽離過后再度將力量投射回去的類型,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做法可能在寫詩之初是有預謀的,久而久之它就會內化為一個詩人的習慣。《引入記憶》一詩是詩人的切身經歷,通過“計劃生育罰款”打開的切口,這“記憶”大多數時候都是“躺在棺材里,/淚流滿面”。借由“引入”一詞,我們能清晰地觸碰到作者的回望姿態,這是一種從此在觀測過去的視角,但是只有抽離能讓詩人將諸多事物厘清,并將兒時的常態性動作探明,詩中那句揪心的“我臉上的耳光,紅紅的,可以擋住/狗嘴”又可說是平地驚雷。至于結尾手心“燃燒的竹簽”則更添鋒利,力的傳遞也通過疼痛感的調度得以延續。
他們,土地的情種,上半身伸進深深的
泥坑中,向外拋出鱔魚,終日吸取日月
精華的鱔魚,脊背青得發黑的鱔魚……
他們踩著地上的樹影,呼吸冰涼的空氣,
手提著蛇皮袋的欣喜,他們的臉上凸出的
是過年的心事;那些只懂得挖掘和泥土的人
腦子里時不時地浮出一些深淺不一的坑。
—— 《挖鱔魚》
這是一首經驗之詩。詩人的處理能看到希尼的影子,很顯然,在這種地方性場景的寫作中,很多人容易陷入故土的挽歌,或者一種更直接的書寫以求成為“這一個”。但在《挖鱔魚》中,我們看不到任何方言和地方俗語(和后期的《消解之梯》、《還鄉》差別很大),整首詩都在使用現代漢語的書面語,比如“精華”、“樹影”、“欣喜”等詞,這跟希尼放棄“做活兒”而選用“勞作”非常相似。希尼曾指出,語言也許是我們的全部世界,但寫作不同,它不可能像語言那么遼闊。因此,李浩在抽離過后會使用打量過的語言再度挖掘,而非停留在原生態的口語和原始的表層經驗上(《消解之梯》和《還鄉》是另一種可待討論的議題)。這首詩中“土地的情種”、“坑”、“過年的心事”也是不能輕易滑過的詞,它們提供了一種理解詩的向度:勞作除了勞作本身,還有來自家庭倫理的套索和負擔。所以,這首詩投射進去的內容遠不是單純的農事,還有苦難、悲傷與反思。
其實,李浩給出了獲得這種力量的原因:“在生活中,那些無數的事件與它們相互檢驗之后,它們讓我懂得了相信,相信它們不會出賣自我,漸漸地,我把保留下來的感覺和經驗,自然地轉化進了詩歌里。”注意,這種“轉化”,是“檢驗之后的保留”,這中間暗含了一個“抽離”的過程。但是,李浩也敏銳地指出,在一個絕對相信的環境中,“背叛”和“謊言”出現了,所以我們又重新回來審視、篩選,這是“對一個人智力的真正考驗”,這也是李浩自己所言的“你對你的工作(寫作)得反復檢驗”。當然,在這種日復一日的修煉中,加之李浩“今晚我是所有的人”的內驅力,使得他成為一個真正的力量型詩人。
3
“今晚我是所有的人”,除了上述“力”之飛揚外,我們還可以做一點擴充—— “今晚我是(你們)所有的人”。引入一個“你們”,加上詩文集的名字“你和我”,不難看出:這句詩和這個句法結構顯示出某種“對話”的訴求。
不過這種對話訴求在李浩的詩中,既沒有表現為強烈的日常癥候(如多多《蜜周·第六天》),也不是嚴格意義的獨白(Monologue)或者復調(Polyphony)。簡單來說,李浩的對話訴求是朝著多個面向的,這也是其寫作駁雜的一個呈現。所以,“你和我”中的“你”,以及“今晚我是(你們)所有的人”的“你們”,是需要查探的。但可以肯定,“你”不是單一而是多個或者復數的。
再回到李浩身上,除卻他不無奇崛的實地經驗外,最不能忽視的一點就是他的精神背景:2008年左右,他受洗為天主教徒。2007年7月,李浩寫下了《相信上帝》,這首詩被榮光啟(詩人的老師、朋友)預感為一個“轉折點”,而李浩自己也曾如是說:
從2007年7月開始……我的詩中也隨之出現了一個非常核心、持久、穩定,并使我激情劇增的言說對象,那個對象可以精確到“圣三一體”,即上帝。這也成為我詩歌的語言、節奏、音域、氣息、對話、形式中的,最為“隱晦”的質地與聲響。……在這長達七年的閱讀、寫作、訓練、生活、思考中,我感覺我在詩歌內部行遍了千山萬水、經歷了人世百態與靈界的各種奇象。我與之言說的那個對象,也在不斷地探視我的性格、呼吸和血氣。
面對上帝,詩人與他的溝通是建立在“信、望、愛”三德的基礎上的,李浩說:“人在面對上帝祈禱時,他對上帝所說的話,上帝自有他的美意和安排。”而在《你與我》這本集子中,很大一部分的“你”都是“圣三一體”(上帝)。不過,李浩并未將這些詩寫成單一的布道詩,這些詩中除了虔誠,還有悲憫和自明。
我們渴望你走進我們。
我們渴望穿過藍色的樹蔭
躺在紫色的樹林下
仰望你,愛你,歌頌你。
——《晨禱》
以及每一個我,如同海水,
聚集在礁石上,盼望你在繁盛的園中復活。
——《練時日》
這么多樹葉,在銀光里閃耀。
這么多光芒,你看如此盛大。
——《在基督里》
我知道你是我的生命。
——《主啊,求你俯聽》
你讓死水中的枯木,露出新芽。你的憐憫,使土地生育。
是你的光明,喂養著所有的生靈。
——《贊美詩》
隨上帝而來的,還有“天使”——“我過早地將你們邀請到我的/城市里來,因為我想和你們/生活在一起,因為我想//從你們的歌聲里,獲得來自/上主的能力和愛情。因為我想/知道你們如何愛神”,這些“從光明中飛來”的“天使”(你們)的身體里,有天父恩賜給詩人的“語言”。在這種和天使的對話中,李浩也證實了信仰能帶領他進入到一種“自明”。
在與“你”(上帝)相關的寫作中,李浩的詩還出現了一些獨特意象和敘述方式,例如“這是地上的平安”(《我沉浸在金子的目光里》),“等待著那張/銀色的大網,從天而降”(《十字路口》),“你讓他肉中,那個擴大的零安息”(《日光之下》)。這些意象和敘述方式是李浩所接收到的上帝恩賜的“語言”,也是在獲得信仰后的一種表征,通過和上帝的對話、溝通,詩人更新著自己的思考、寫作和生活,并辨認出“新鮮、帶刺的詞”。
你我之間,公路
背向云中升起。
你仰望,就會出現
更多的公路。
它們通往的,
任何一個地方。
都有大片的密林
和空曠的草地,
都有向你我涌動著
深淵的窗口。
——《你和我》
《你和我》的名字就取自這首詩。和這本詩文集一樣,在眾多的詩中拈出一朵花作為一本集子的總標題是許多詩人的慣常做法,李浩自己也是,他的另外兩本詩集《風暴》和《還鄉》就是如此。此前,我將“你和我”作為詩人的“術語”加以拆解,在邏輯起點上可能會被質疑,然而,副文本(比如標題、插畫、注釋、封面等)也是非常重要的透視窗口。正所謂,一部作品的任何細節都能成為進入它的切口,某個單篇、某種重復、甚至分行和標點都暗含了巨大的漩渦與潛流。
再回到《你和我》這首詩,詩人雷武鈴認為即使在這樣的愛情詩中,李浩仍展示了“渾然的力量”,并指出這種力量不可能來自單一的源頭。確實,《你和我》并沒有顯示出一般愛情詩的質素,比如誓言,比如甜蜜的意象和語詞,比如溫婉柔情的敘述。李浩延續了自己一慣的力道,將“你和我”置于更闊大的背景,即使有了“公路”、“云中”,他還不甘心,非得做得更絕,于是就有了“仰望”,有了“任何一個地方”。在這一層的鋪墊推動下,“大片的密林”和“空曠的草地”就不再是僅存于地面的事物,它們也獲得了飛升的能力,獲得了一種神秘性和崇高感。詩的最后—— “都有向你我涌動著/深淵的窗口”——既給出了充滿無限可能的“窗口”,卻又附加了“涌動著深淵的”定語,其中的張力自不消說。顯見的是,這一組合帶給愛情力的質感,并使之獲得了超然和躍越。
在李浩寫給友人的詩中,《悼馬雁》是一首值得深入閱讀的作品。在《蟄居安寧莊西路》一文中,李浩有回憶自己在北京的生活以及那時與北京青年詩人的來往,馬雁是其中一位,李浩說他和這些詩人、朋友“因為寫詩而相遇在同一片天空下交往的神秘地圖”,他也因此和馬雁結下了友誼。2010年,馬雁在上海永遠地離開了我們。身后,她留下了不少的散文和詩歌,其中包括《北中國》、《北京城》、《清潔工》、《櫻桃》等優秀作品。
李浩的《悼馬雁》以“這不是冬天,這是一塊大石。/這塊倏然飛來的大石,拍住我的腦門”將自己的感覺具象化,從“冬天”到“大石”,那種聽到消息后的沉悶、郁結以及阻隔在心底的感受得到準確闡明。“這不是冬天,這是一塊大石。/這塊倏然飛來的大石,拍住我的腦門”在詩中回環了三次,以它為標志可以把這首詩看成三部分(雖然我本心拒絕這樣做),第一部分還原詩人失去朋友后的感受:“我再也無法聽見任何動靜,/任何耳語,/任何詩句”;第二部分渡入到“你跨出我們的路”,然后將馬雁的詩句以及詩人和馬雁交往的日常細節慢慢披露,其中有一句“小心地不吃出聲”的詩句,原本是寫吃粥的樣子,但放在這個“悼”的場景中,必然會死死地戳進讀者的內心;第三部分詩人開始學會“忍受”和“傾聽”,“強迫自己/安靜,禱告無詞”,但朋友離開已經成為寫定的事實,唯有說出“風暴中你全部的隱痛,/已進駐冬日的星辰”,才好受些。以“這不是冬天,這是一塊大石”為標志的三次回環,讓這首詩得以續力并完成,但李浩并未以它為尺度進行分節。《悼馬雁》是一首完整順暢且不分節的“磚塊詩”,我想這還是跟“大石”有關。這樣的一個詩歌形態,不正像一塊“大石”,拍住了詩人的“腦門”嗎?
在李浩的其他詩中,也能看到他與馬雁隱隱對話的身影,比如:
縱橫交織的圖譜,
與六樓的所有窗口,
與“北中國”的
另一個隆起的建筑群體,
神秘呼應。
——李浩:《西山》
北中國,是這樣一個簡單
準確的命名,幸福宏大得
如同天干地支,不可摧毀。
——馬雁:《北中國》
再比如:
我站在警燈里,冬夜的
北京,正在滲水,
正在墜落磚石。
——李浩:《世紀》
……這城市
熱衷于責任而毫無辦法。
不敢再有人來這里,因為
它已經被毀壞。
——馬雁:《北京城》
其他的這個類型的詩,如《天橋下的歌手》,“你”既是特指,也可以視為泛指。這首詩在“都市—鄉村”的鏡像關系中把一代青年人的漂泊、放逐和疏離表達出來,這個“你”既是那位歌手,也是千千萬萬如他如李浩的年輕人。再比如《島》,這個文本在我看來也是指涉愛情的,“你”就是示愛的對象,但李浩引入的“火焰”、“繁星”、“野獸”、“星光”、“橄欖林”卻帶來一種異域的、宗教的、不無神秘的觸感,所以這個“你”的身份也可能是多重的。正如詩人李建春指出的那樣,李浩的有些詩是“理想主義和語感,與生活中的真實場景強行焊接。因此有這么多的時空糾結,心境與主張的糾結。沒有必要去理清”。
人稱和指代的糾結在李浩的詩中是非常顯見的現象。
誠如王辰龍所言,如何運用人稱代詞,在新文學發生伊始,便成為亟待實踐的語言問題。僅就現代漢詩而言,時至今日,人稱使用已復雜多變,有些作品成功的奧秘也在于此。確實,一個好的詩人能夠通過人稱的轉換、迭變、穿行達到詩歌技藝的進階。在運用人稱代詞行進的過程中,基于人稱變化致使的一系列美學效果,諸如指涉的模糊化、施事與受事的迷藏、因人稱跳躍而生的音樂感等等,都能為詩歌的藝術帶去增值。
4
李浩的《你和我》沒有自序,文選和附錄也對這本詩文集的命名只字未提,但我仍固執地認為“你和我”就是他的一個重要術語,至少對于這本集子而言是如此。
“你和我”伙同“今晚我是所有的人”,向讀者展示了李浩的力量:一種主動型力量和一種抽離型力量的完成體,它既有主動出擊的籠蓋四野,也有抽離出來的復歸與投射;同時,“你和我”伙同“今晚我是(你們)所有的人”還向讀者展示了李浩高超的詩歌手藝,即人稱使用的縱橫捭闔,而其中的“你”必定是進入李浩詩歌內部一個重要通風口。
馬克·斯特蘭德(Mark Strand,1934-2014)曾指出:“某些知識之外的東西,會驅使我們以自己的興趣和能力去追隨一首詩。”其實追隨一個詩人,很多時候也倚賴追隨者的興趣和能力。我不敢說自己有能力讀懂李浩,但是對他的興趣,我是持續的。從《階梯》到《風暴》,從《還鄉》到《你和我》,李浩的詩對我來說總是挑戰,又是新鮮。
“詩歌是想象性文學的桂冠”,而我正在《你和我》的美學形式下繼續延展著自己的想象。成為“那個個人”的路還很長,期待李浩能提供給我們繼續想象的可能;對于他目前正在伏案創作的詩劇,我也正翹首以待——真誠地希望他能“打出真鐵,讓風箱發出吼聲”。
“你和我”伙同“今晚我是所有的人”,向讀者展示了李浩的力量
? 轉引自阿西《風暴的形成》,《上海文化》,2015年第11期,第79頁。“那個個人”被李浩的朋友提煉為一種個人意識,他們認為一個有宗教背景的人容易陷入“反個性化”的詩學,而李浩卻在個性和反個性的動態結構中,建構和升華了自我,他也因此變得更加寬廣。
? 據李浩的朋友蘇豐雷回憶,“燃燒的竹簽”原稿是“燃燒的汗”。從“汗”變為“竹簽”,李浩造出了震撼和陌生感,這可能是出于詩歌寫作上的考量,但也在無形之中嶄露了詩人主體的“力”。
? 參見希尼:《約翰·克萊爾的Prog》,《讀詩的藝術》,王敖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 李浩:《詩集〈風暴〉自序》,《你和我》,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40頁。
? 陳家坪、李浩:《讀書、寫詩、工作,在廣闊的生活內運動——詩人李浩訪談錄》,《還鄉》,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6-157頁。
? 李浩:《蟄居安寧莊西路》,《你和我》,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23頁。
? 根據李浩在訪談中的回憶。
? 引自王辰龍關于李浩“詩歌中的人稱代詞”的發言。參見《天通苑:會飲篇——李浩詩集〈風暴〉研討會》,《你和我》,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89-190頁。
? 馬克·斯特蘭德:《論成為一個詩人》,《讀詩的藝術》,王敖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04頁。
? 哈羅德·布魯姆:《如何讀,為什么讀》,黃燦然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