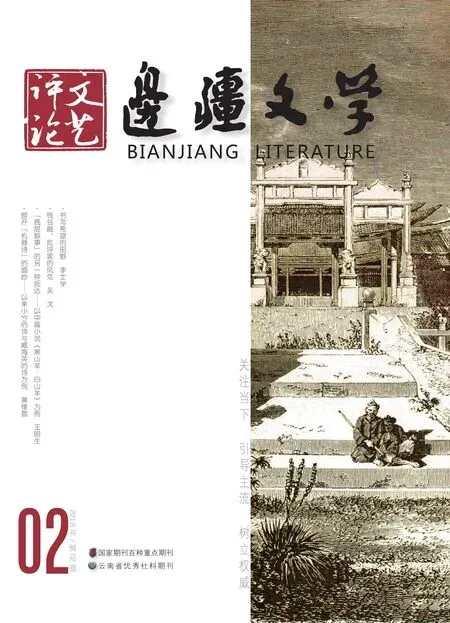木祥小說里的鄉愁
尹曉燕
木祥是云南比較有實力的小說家之一,也是麗江為數不多的小說家之一。他的小說集《束河啊束河》和長篇小說《紅燈記外傳》我都認真拜讀過,受益匪淺。
在閱讀過程中,我覺得,木祥的大部分小說都流露出濃厚的鄉愁,他的小說總是讓人讀到懷鄉的情感,眷念故土的思鄉情緒。
其實,對童年的回憶,對故土的眷念,一直是我們創作的動力或源泉,是我們銘記歷史的精神蘊藉。從我國文學發展的歷史來看,鄉愁或對故土的眷念一直是漫長的文學傳統中的重要主題。我們在閱讀古典文學作品時,就常常讀到許多優秀的表達鄉愁的作品。我國最早的文學作品《詩經》中,就已經有不少表達鄉愁的作品(如《君子于役 》《采薇》等),唐詩宋詞就更不用說了,表現鄉愁主題的詩篇更是不可勝數。李白的《靜夜思》、杜甫的《春望》、范仲淹的《塞下秋來》等等詩詞,思鄉情感,鄉愁情節在詩詞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到了20世紀,我喜歡的魯迅、沈從文、蕭紅等作家,他們書寫鄉村記憶的作品,讓我們讀到了鄉愁鄉情的同時,還讓我讀到了對鄉村陷入現代困境的深切關懷。
在中國當代文學中,中國鄉村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這種變化,同時造就了一大批以鄉村鄉愁為主要寫作對象的作家,如莫言、賈平凹、陳忠實、路遙、張煒、阿來等,他們或者以鄉土敘事為主導,或者以個人親歷的角度書寫鄉村,使讀者對20世紀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進步與轉折有了深刻的了解和深摯的記憶。
當然,以鄉村題材為主要書寫對象,記錄鄉村,塑造新型農民形象,表達鄉愁的作品,肯定會有作家的鄉村生活經歷,有他們獨自的情感世界。木祥小說的鄉愁,可能與他的人生經歷和文學素養有關。木祥出生在20世紀50年代,當過農民,當過民工,在西藏當過兵,退伍后當過汽車駕駛員,然后走上了創作道路。他豐富的生活閱歷,見證了新中國六十多年翻天覆地的變遷,可以說,這是一個小說家的重要財富。人生的閱歷對一個作家的小說創作十分重要,豐富的經歷,難免產生不少人生的磨難,悲歡離合,這些,往往會決定著一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思想深度,同時,會自覺不自覺地決定著作家的寫作方向。所以,我們閱讀木祥的鄉愁小說,可以從題材的選擇,故事的編織,語言的表達和情感的傾訴等等方面找到亮點。
一、題材選擇決定了木祥小說的鄉愁情節。
寫小說的作家都知道,我們在選擇寫作方向,即題材選擇的時候,都得明白自己的長處在哪里,自己的局限在哪里。比如,昭通的夏天敏就沒有嘗試寫麗江東巴文化情死題材,麗江的和曉梅也不會輕易選擇寫西藏,同樣,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木祥,也不可能選擇寫現代青春校園文學。他們都知道自己寫作的優勢在哪里,同時也明白自己的盲區在哪里。他們在寫作技巧上作大膽的嘗試,但在素材的選擇上都盡量避開局限,選擇自己熟悉的,感興趣的題材。木祥的小說,大多都以滇西北一個叫“妃子村”的村莊為地理坐標,他的長篇小說《紅燈記外傳》,中短篇小說《束河啊束河》等一大批鄉土小說,都是以自已經歷和生活過的時代故事為背景,表達屬于他自己獨特的鄉愁。
到了近幾年,木祥的小說也沒有走出鄉村鄉情這個主題,他的《童年三題》《走陰》《洪水中的村長》《村長也用蘋果5》等中短篇小說,依然與鄉村有關,與故鄉有關,其故事情節,都來自他的體驗和感悟。他的這些小說,都有自己生活的原型,再就是來自他對大量的鄉村素材采訪記錄,用心捕捉,嚴格篩選,然后進入小說題材。通過多年的實踐,木祥似乎明白了,小說不是照搬生活,他總是能通過細致的觀察,體驗,分析素材在小說中對主題和人物性格有何作用,然后才做出最后的選擇。
比如短篇小說《走陰》,講述的是一個巫師通過走到“陰間”,與去世后的人對話的老故事,充滿迷信色彩。如果就事寫事,這個故事就失去了意義,木祥通過思考,把“走陰”的故事嫁接到爺爺奶奶身上。小說中,奶奶一直懷疑爺爺與“風擺柳”有染,然而,生前從來沒有得到印證。爺爺死后,奶奶去為“風擺柳”家“走陰”。“走陰”到最后時刻,奶奶說有一個“身穿綠緞子長衫,頭戴紅頂瓜皮帽的人”進了“風擺柳”家。“風擺柳”家的人,誰也猜不出這個人是誰,“風擺柳”卻是淚流滿面了。因為奶奶“走陰”時設置的這個人,就是“爺爺”的“陰魂”。木祥就是用這種隱喻,通過爺爺的靈魂回到“風擺柳”家的過程,表達生死之愛的真摯情感,給人留下想象的空間,讓我們從老故事里讀到新的觀念,濃烈的鄉愁撲面而來。
類似這樣對故事巧妙設置的例子還很多,這樣的小說,不但讓我們讀到現代情感,同時能讓我們在老故事中讀到濃烈的鄉愁情緒。
二、在現代鄉村故事敘述中植入古老的鄉村情節,讓小說增加了懷舊情緒,讓人感到溫暖。
木祥近兩年的小說,以現代鄉村故事為主,但他在寫好現代鄉村故事的同時,融入鄉村故事和人物的懷舊情結,表達鄉村變遷和鄉愁,取得了較好的效果。要寫現代題材的小說,要深入生活,拮起新的生命力的故事和人物。木祥不斷地深入生活,尋找到反映新農村的新變化的題材后,不是盲目地寫作,而是觀察,體驗,分析。他知道自己的情感在哪里,他明白,自己想表達的,最能讓讀者和他自己心動的,是鄉村人物的感情,還有在現代生活中的懷舊情緒。我們都知道,現在的鄉村,是生產關系、思想觀念都變化了的鄉村,鄉村經濟發展了,人們的思想觀念也變了,物質突飛猛進,精神生活卻往往處于游離狀態,如何通過小說反映這一命題,木祥作了一些嘗試。他最近兩年的鄉村題材小說的可貴之處,就是在如何寫出現代村民的歷史與現實交融,從而達到對鄉村、農民的多重解讀,使小說具有思想力度。
我們讀到的《洪水中的村長》,是2017年他發表在《民族文學》“建黨九十周年專輯”的作品,小說寫的是滇西北鄉村的一個洪水搶險故事。小說中的楊大武和楊大才,是兩個出生不同階級成分的兄弟,他們經歷了階級斗爭為綱的時期,改革開放以后,通過奮斗事業有成,又回鄉為自己的家鄉做出貢獻。特別是楊大才,為了賺錢,在發展自己的磚廠時不小心生殖器被皮帶輪絞掉,而在關系到自己的村莊被洪水淹沒的時候,義無反顧地決堤把多年艱辛創建起來的葡萄園沖毀了,一種鄉愁,通過理想中的人物,得到了淋漓盡致地表現,讀來讓人感動。
在同一篇小說中,主要人物楊大武是新時期鄉村干部的典型,他是在通過艱難的創業發家致富以后才回鄉當村長的。楊大武回鄉當村長,為村民服務是大方向,但他也不是高、大、全的典型,其中,也包含著他復雜的情感。楊大武是地主子女,小時候受了許多凌辱,回鄉當村長,也是想爭氣,在楊家村去證明自己。但木祥塑造的楊大武,回鄉當村長也不完全是私心,最終還是被服務村民這個大局所征服。比如楊大武當村長時五保戶的安葬,搶險救災,美化村莊,拒絕回扣等等,都塑造了一個完整的村干部形象。
這些鄉村人物的塑造,來源于木祥對現代鄉村的正確解讀。鄉村農民,在經過物資匱乏的年代以后,他們在賺錢的時候想盡千方百計,這也符合客觀規律,楊家村的人窮怕了,沒有錢的滋味他們嘗夠了。但是,但們并沒有被錢所打倒,通過勤勞富裕起來以后,他們依然懷念家鄉,他們覺得,保住自己的村莊,人生價值才能得到真實的體現,這與近年來許多在外務工的村民回鄉建房,富裕起來的村民回鄉發展產業等等情形是多么的相同。
木祥就是通過深入了解新農村,再通過對自己的鄉愁情感進行梳理,寫出鄉村農民的多面性,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增加了小說的層次感。正因為如此,才能立體地反映鄉村,表達自己的鄉愁,讓主題多元和模糊,讓小說不再是單一的故事,單一的人,讓小說中的生活的多重性,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從而增加小說的容量。
三、鄉愁情節讓小說具有濃厚的個人情緒。
讀木祥的鄉愁小說,我們總是能讀到一種復雜的情緒,一種淡淡的純樸的韻味。我在談自己的小說創作的時候說到過,我的小說是有自己的情緒的。我的小說里,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表達著自己的情緒。我始終覺得,小說里有了自己的情緒,才可能讀出一點兒韻味。后來發現,作者的情緒是會直接影響到小說的基調、韻味的,是明快還是纏綿,是悲壯還是詼諧,都產生于作者對材料的把握,然后決定了作者的情緒,韻味,然后,這種情緒或韻味,又決定了作者的敘述方式,語言的運用。
仔細讀木祥的小說,小說里的情緒和韻味不是生硬的,而是從小說的故事和人物中自然地體現出來的,讀他的小說后,有時會會心一笑,感同身受。
我們在閱讀過程中可以感覺到,小說中的情緒與韻味,并不是簡單的問題,它關系到小說的可讀性,感染力和作者的態度。一個優秀的作家,總是能很好地控制小說的情緒,調動情感。小說當然要有思想深度,但是,我們更期待思想性與作者的精神氣質融和在一起,讓作品有瑰麗的想象,詼諧,機智,生動,趣妙氣橫生的作品。
木祥的小說,在人物故事中自然地融進自己的情感或情緒上,作了很大的努力。讀他的小說,總是能讓我們讀到他的感情,有時候,我們會猜他作品里的哪個人物是他。連他自己都說,他寫的小說,差不多要用現實中的人名才過癮。我不知道對小說里的故事人物放入了太多的感情好不好,但是,沒有作者情緒的小說,我不知道是什么樣子。
木祥的許多小說,用的是第一人稱,這樣,更能表達出他的情感世界。如《妃子村片斷》《童年三題》類似自敘的方式。當然,小說故事不可能全部是作者的,但是,都是注入了作者情感的,是經過他思考,篩選過的,這樣的書寫,小說就有了韻味,就容易產生共鳴。
如此的表達方式,使木祥的小說具有濃厚鄉愁情緒的同時,也讓他的小說具有散文韻味。他的小說,我們有時候無法分辨是小說還是散文。從文學理論上說,散文是自我的,小說是客觀的。但在他的小說里,既是自我的,又是客觀的。如果認真分析,里面小說元素是主體。比如他在《走陰》里這樣寫道:
大門老舊了,頭上蓋著的瓦越發黑了,松木的門板和門墩、門檻都成了棕黑的顏色。兩旁的土坯墻也斑斑駁駁。門頭上的瓦溝里長了一些石簾花。
每到有人開門,“吱呀”聲慵懶沉重。門里的巷道只有二三米寬,比較深,都鋪了瓦磚。開門聲在深深的巷子里緩慢的流淌。
巷道里有一口老井,井檻上寫著“龍泉清”三個字(木祥:《走陰》)。
這樣的表達,散文味道撲面而來。但是,后面的故事情節,人物的塑造的戲劇效果,依然讓我們感覺到小說構架。比如在《走陰》的結尾處,木祥這樣寫道:
紙錢燒得差不多了,奶奶的臉色好像回轉了一些。然而,時間不長,奶奶馬上又抖動起來,嘶啞著聲音問道:怎么了,這個時辰了,又進來了個瘦高個的,穿藍色緞長衫的,頭戴瓜皮帽的?
“風擺柳”家的人都吃驚,想站起來的又跪下了。然而,都猜不出這個人,想不起自家有這么個人。
奶奶說:想不起來啊,真沒有啊?但真是進來了啊,瓜皮帽上,還有個紅頂子的——有點像個秀才呢。
“風擺柳”眼里卻是噙著淚花了。她知道是我爺爺的靈魂去她家了。
“風擺柳”只是什么也不說。
奶奶說:是不是我家那老鬼走火入魔走錯了門,我把他趕出去!
然后搖了一會磬鈴,說道:出去出去,回家去,我給你燒油茶。
說著說著奶奶就醒了。奶奶醒了,用枯瘦的手指揉了揉眼睛,然后對“風擺柳”家的人說,這個人回去了,可能是走錯門了……
在小說中表達自我情緒,難免使用散文語言。有人說,小說是客觀性的語言,作者有什么思想感情,作者并不站出來說,而是讓人物、讓情節代作者說;而散文則是主觀性的語言,作者不站出來說,還不行,作者可以直抒胸臆。我覺得,木祥是善于用散文語言寫小說的作家,在他的小說中,他是在場的,又能客觀地講述故事,刻畫人物的,并且能讓小說語言具有獨特的意境。
由于是真誠的情緒,木祥的小說是聊天式的,不是高高在上的。這需要建立在扎實的生活功底和語言駕馭能力上,這種舉重若輕的表達方式,可以看出作家對小說里的人物故事充滿了自信,才能從容不迫,娓娓道來。如果沒有對事物把握,沒的對家鄉對生活的熱愛,我們是不可能在小說敘述中感受到作者情緒的。
總之,木祥的小說對鄉愁小說作了難能可貴的探討,他小說里的鄉愁是真誠的,表達著他的靈魂。我們期待著木祥有更多更好的反映鄉情鄉愁的小說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