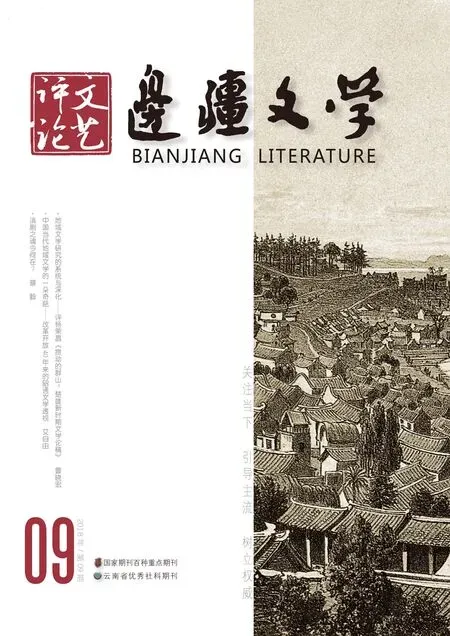梳理文脈填空白
——讀《楊繼中文選》
楊繼淵
楊繼中生于1935年,是新時期楚雄文學的開拓者之一,于1990年因病英年早逝。在他去世23年之際,其文友及親屬編選了《楊繼中文選》,由云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
《楊繼中文選》收入了楊繼中為《楚雄彝族文學簡史》一書撰著的緒論、上古文學、中古文學三編,楚雄文廟碑文,紅軍長征過武定、祿勸的路線、史料;根據祿勸殺人搶劫案而作,1981年在《春城晚報》連載7期的報告文學《金沙迷夢》;致力于楚雄地方文化研究的《梅紹農和他的詩作》《畢摩和彝文、彝文典籍》《有趣的彝族神話》《游洱海、看蒼山》等文稿;尚未完稿的《鳳氏土官箋注》手稿;為彝族文學討論會準備的油印文稿《試論楚雄彝族文學發展的特點和規律》;評論文章《致吉狄馬加》;未刊散文手稿《雨不灑花花不紅》《藕》;《編者寄語》,盡述對作者、刊物的文風與期望等20余篇。縱觀全書,但最具功力和代表性的作品是《楚雄彝族文學簡史》中的緒論、上古文學、中古文學三編,10余萬字,把流傳在楚雄地區的彝族民間文學作品和書面文學作品作了較為詳盡的介紹,并對從遠古直到近代的楚雄彝族文學發展脈絡作了較為系統的勾勒和論述。這是第一部較為全面地研究楚雄彝族文學的文學史,它的編著出版不僅是楚雄彝族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整個彝族文化界乃至民族文學界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對于它的學術價值與引領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將有更深刻的認識。
文學是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反映,是民族文化的脈絡主線。楚雄彝族人民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創作了數量繁多的文學作品。楚雄彝族文學起源于開天辟地的上古時代,崛起于現當代,這是一個楚雄彝族由口頭民間文學自然過渡到書面文學的時代,文人隊伍逐漸形成,產生了一大批用漢文創作的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之類的作品,以濃郁的地域色彩、深厚人文底蘊的創作成就,成為中國文學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楊繼中先生《楚雄彝族文學簡史》的緒論、上古文學、中古文學三編對楚雄彝族文學的起源、發展和重要文學現象、基本特點進行了條分縷析的論述和理論概括,梳理了楚雄彝族文學文脈,確立了從遠古楚雄彝族先民在開天辟地的斗爭中創造的神話到明代“改土歸流”時期楚雄彝族文學在全國大格局中的基本地位。
楚雄,是世界人類發祥地,世界恐龍之鄉,東方文明搖籃。170萬年前的“元謀人”誕生于此,距今約1400萬年到800萬年之間的祿豐臘瑪古猿活動于此,2400多年前的萬家壩銅鼓發現于此,有著非常引人注目的遠古文化。在悠久漫長的歷史歲月里,楚雄彝族人民創造了自己豐富的民族文學,為豐富中國文學寶庫作了積極的貢獻。根據楚雄彝族社會歷史發展和重大政治更替以及文學自身的發展狀況,以公元748年哀牢蒙氏家族建立南詔政權為標志。之前,為楚雄彝族文學的上古時期。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楚雄彝族先民經歷了原始社會,進入了奴隸社會的初期,文學創作從“不自覺的意識加工”到有明顯的功利目的,文學作品的內容,主要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代表作品主要有把原始神話集中起來的創世史詩《查姆》《梅葛》以及歌頌祖先的英雄史詩《阿魯舉熱》。這是一個神話的時代、史詩的時代。從南詔政權的建立至明末“改土歸流”,為楚雄彝族文學發展的中古時代。這個時期,楚雄彝族社會從奴隸制上升時期過渡到了衰落,開始向封建社會過渡。奴隸制上升時期,楚雄彝族文人——畢摩創作比較活躍,用彝文創作了大量的書面文學,代表作有史傳文學《六祖分支》和直面人生的《指路經》之類的書面文學。同時,民間口頭創作的各種歌謠日趨繁榮,為后來抒情長詩和敘事長詩的誕生,創造了條件。這是彝文書面文學的繁榮時代,也是楚雄彝族歌謠的活躍時代。楊繼中先生主撰《楚雄彝族文學簡史》的上古文學、中古文學以時代為序、以作品為綱,從縱的方面對楚雄彝族文學的特點和發展規律,進行了全面、立體、嚴謹的梳理,確立了上古、中古時代的楚雄彝族文學在全國大格局中的基本地位,具有梳理古代楚雄彝族文脈、填補地方文學研究空白的意義。
這部書為楚雄彝族文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在楊繼中先生等編著的《楚雄彝族文學簡史》出版之前,楚雄彝族傳統文學的研究卻相對薄弱。雖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了楚雄地區的《彝族文學史》,但研究則顯得比較粗略,對于理清某一時間段的文學脈絡,給讀者介紹各具代表性的作品來說,則明顯不足。楊繼中先生等編著的《楚雄彝族文學簡史》的出版,則有力地彌補了這一缺憾,為系統對楚雄彝族傳統文學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是一部厚積薄發之力作。作為楚雄彝族文學研究的專家,楊繼中先生長期生活在楚雄彝族地區,熱心收集和關注楚雄彝族文學,站在全國文學研究前沿,以全局的視野和一位云南學人的赤子情懷加入到本土文學的研究中,對楚雄彝族文學進行了大量文本賞析、史料考辨和理論概括等方面的工作,有力地填補了楚雄彝族古代文學研究之闕。《楚雄彝族文學簡史》中的上古文學、中古文學,從楚雄彝族文學的特點和實際出發,以時代為序 ,以作品為綱,從縱向對楚雄彝族文學發展特點和規律進行認真研究梳理。在具體表述上,則把個案研究與綜合闡述、歷史語境與文學發展、傳統內涵與當代視角、文學交流與地域特色等多個角度結合起來,始終把握楚雄彝族文學的本體;在縱向和橫向交錯的態勢中,觀現象、看發展、識本質,立體地描述楚雄彝族文學的獨特風貌,最終創立出比較能夠揭示其主要內涵的敘述體例和基本理論,進而為楚雄彝族文學發展狀況合理定位。
第一,對楚雄彝族文學上古、中古時代傳統文學的研究全面、深入、自成體系。
楚雄彝族傳統文學崛起于現當代,并以詩文的繁榮為標志,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學的主流。楚雄彝族在創造和發展自己民族形式的同時,也注意創造和發展自己的文學。長期在人民群眾中廣泛流傳的民間口頭創作和文人書面文學,是楚雄彝族文學中的兩種文學成分。這兩種文學成分,雖然有著不同的階級屬性,但長期以來,正是這兩種文學成分的互相滲透、互相促進,推動著楚雄彝族文學的發展。楊繼中先生主撰的《楚雄彝族文學簡史》上古文學、中古文學,在認真梳理楚雄彝族文脈上可謂貢獻卓著。它對傳統楚雄彝族文學的民間口頭創作和文人書面文學資料收羅較全,著重加強對作品的研究,進行填補空白工作,并對現有成果進行了提煉,提出了合理的見解。總的來看,楊繼中先生主撰的《楚雄彝族文學簡史》上古文學、中古文學,對楚雄彝族文學的總結是至今為止包容量最大、解決了目前我們對該時期楚雄彝族文學深入和整合研究的相對滯后,可謂全面、較為深入的研究。論作品細致入微,既看到作品主流——直抒胸臆,又看到作品感情表達的變化。既有對作品的概括總結,又一一辨析評議,最終從實際出發,得出較有說服力的結論。由基礎性的實證研究,進而深入到理論概括和總結,整合楚雄彝族文學的成就,彰顯楚雄彝族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對推進具有當代前沿學術水平的楚雄彝族文學研究,無疑具有其理論意義、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可謂深入。在“上古、中古楚雄彝族文學”這個歷史地域的概念下,作者這樣的論述結構,楚雄彝族主流文學的這一狀態,不是任何人的主觀意圖所能改變的,而這正是楚雄彝族文學的重要特點。作者的研究思路來自對上古、中古楚雄彝族文學的實際考察,符合文學史實,也理清了楚雄彝族文學的發展脈絡。由此,楊繼中先生主撰的《楚雄彝族文學簡史》上古文學、中古文學,可謂自成體系。第二,追本溯源,考證翔實,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楊繼中先生主撰的《楚雄彝族文學簡史》上古文學、中古文學,對楚雄彝族文學起源、古歌謠、神話、彝文典籍、文學作品的研究,都以專章對這些文學作品做了細致的分析。以原文研究為立足點、出發點,分析研究作品的地位和影響。這些分析研究為理論總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楚雄彝族文學史研究提供了珍貴史料。撰著分為兩編,提綱挈領、要言不煩地呈現每一階段文學成長歷程和文學活動,避免了不加辨析、旁征博引、排比羅列。在大量史料中抽繹出簡單明了的“年”“事”條文,每一個條文下列舉典型性的作品,均以事實為基礎,使每一款條文抽繹和每一作品資料的采用,都體現了史料的客觀真實性。每個創作系年在勾勒彝族文學發展軌跡的同時,亦關注橫向聯系,從而較為全面地呈現楚雄彝族文學發展的實際。如,古老的神說,先進行概述后,再分類,并進行特征分析,再以《查姆》《梅葛》《阿魯舉熱》等代表性的作品列為專章,進行條分縷析,印證楚雄彝族文學在上古、中古時期的發展。這些均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第三,對深入研究楚雄彝族文學有很大的啟發。
作為對楚雄彝族上古文學、中古文學創新性的研究,楊繼中先生重在辨析和評議。其作品合理的理論建構、新穎的研究角度和頗具創新意識的觀點,對同行所起到的啟迪作用,也是對學術界的不菲貢獻。楊繼中先生對上古、中古楚雄彝族文學的分類,給邊疆民族文學的類型學研究提供了較好的思路。同時,給同行帶來的啟發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這種啟發性、思辨性,奠定了學術專章的精彩和厚重。民間的口頭創作是楚雄彝族文學的主體。楚雄彝族的民間口頭創作樣式和內容十分豐富,有遠古的神話,也有鴻篇巨制的史書;也有成千上萬的歌謠,也有動人的抒情長詩;有各種各樣的傳說故事,還有眾多的諺語和寓言。文人書面文學,是楚雄彝族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楚雄彝族文人“畢摩”曾經用彝文寫下了一批包括文學作品在內的各種著作;一批接受漢文化的彝族文人用漢文和漢文學形式寫了一些作品。民間口頭創作是楚雄彝族文學的主體。作者采用兩大基本類型分類研究的方法梳理了楚雄彝族文學,這是楊繼中先生主撰楚雄彝族上古、中古文學的亮點之一。但復雜多元的文學發展狀況,很難由一個標準界定清楚而不出現重復交叉,作者在行文中也關注到了這問題。楚雄彝族文學的崛起在當代,一代文學家以地域色彩濃郁、人文底蘊深厚的創作成就,成為中國文學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昭示著楚雄彝族文學富有希望的未來。楊繼中先生主撰的《楚雄彝族文學簡史》的緒論、上古文學、中古文學三編,是對楚雄彝族文學研究的開創性佳作。它通過具體論述和理論概括,讓人們從中感受到傳統楚雄彝族文學曾經以怎樣的態勢在西南邊陲開花結果,形成了一個地域文學的獨特風貌,進而推動云南文學乃至中國文學的發展,堪稱古代邊疆民族文學研究的上乘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