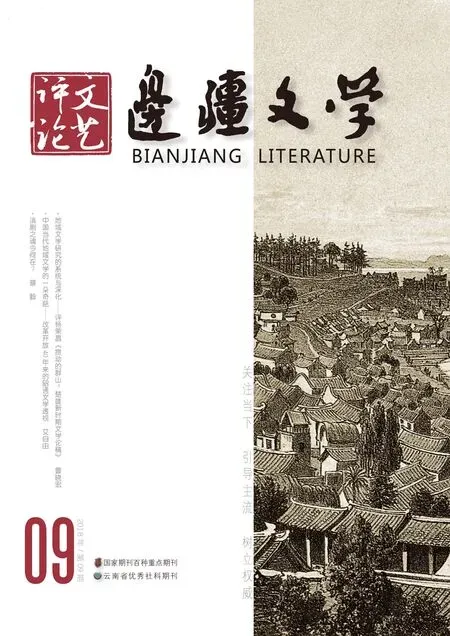古道風云繪滄桑
——析繆遠洋的油畫意蘊
朱思睿
一個如風的少年,總會被歲月吹白黑發,帥氣如繆遠洋這樣的青年才俊也不例外,長年的才情揮灑已讓他染上幾許風霜。看他的畫,有些如風的快意,如云的凝重與飄逸,黑白灰黃褐是他的基調,如天上風云之奇變,有不可預知的神秘灑脫,也有時空變遷的滄桑與深邃。也看過一些人對他作品的闡釋,或詩性的解讀或學術的推理,筆者自忖寫不出那樣的文質,但評論不是文學,姑且妄言,以下還是從一個油畫實踐者的角度去感觀。
一
對繆遠洋的印象,仍然停留在若干年前,第十一屆全國美術作品展的時候。他一幅具有“博特羅風格”的作品,膨化的人物造型與孤寂冷灰的背景,令人眼前一亮,與南美洲哥倫比亞大師博特羅詼諧幽默,色彩明快的胖畫風格有很大的異趣。前者是戲謔的愉悅的,而后者卻有些嚴肅和憂傷,人物沉思的表情中隱藏著故事,童年面孔而心事重重。這種膨化與國內宮立龍的陶土味鄉土表現不同,與韋爾申白日夢式的充氣感知識分子形象也不一樣。他畫上的人兼具童話與現實的雙重糾纏,具有成熟與稚拙的混合氣質。直至看了他的畫冊《冥想中的自我造像》,才知道那是他持續了五六年的創作系列,幾十幅作品都在一米六以上,幾乎由一個總標題——《頭都大了》貫穿整個創作系列,題材內容包羅萬象。荒誕、玩世、反諷、游戲、戲謔、幽默等情緒特征皆有涉獵,成人世界兒童世界都有觸及,技巧高,造型清晰,制作精良,畫面構造極富想象張力,其象征性,寓意性,情節性在天馬行空的想象力支配下,閃爍著理性的智慧光芒,將現實世界中人們生存所面對的焦慮、緊張、孤獨、壓抑通過卡通式的繪畫語言冷靜輕松地呈現出來,色調是灰的,畫面情緒也是灰色的,其間也動用了挪用拼貼等當代繪畫的處理手段。
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的卡通第一代亮相,當代繪畫中的卡通化敘事形成,是繼玩世、艷俗、波普之后的又一波創作傾向,許多70后及80后藝術家參以其中,既是那一代人的成長環境鑄就,也是一種時代癥候,其創作動機依然是對現實的變異式反映,只是自覺回避了60后的藝術家們,那種基于現代藝術影響之下鋒芒畢露的批判藝術樣式。其虛擬的具有超現實傾向的文化訴求,其實是對現實的困感與發問。而新世紀初的繆遠洋,剛從川美畢業,其藝術選擇與自幼對連環畫及卡通消費的成長經歷、四川美院的學習環境、改革開放后的時代文化背景相諧。
繆遠洋的藝術第二次觸動筆者,是一批面對云南景觀的寫生作品,尤其與滇西南和西雙版納白塔為題材的一批圓型畫作。這批畫與室內創作的嚴謹細致不同,極盡任情任性之酣暢與寫意。他自認初入云南時,在寫生中面對這邊熾烈的陽光,色彩濃重的自然環境有些無所適從。還好,他有前期亮灰色的創作經驗,漸漸在白色的建筑中發現了自己的力點,這是一種必然。當然藝術的獨特性并不在于廣博才能的釋放,也不全賴豐富的表現方法設置與展示,而在于藝術家由物會心的心靈感悟與神秘體驗,在于作者高尚的靈性與激情及精神含量,只有這樣才能產生出比預想更多更深更發自靈魂深處的獨特性。那些白色的建筑與塔,在普通游客眼里只是干凈的風光,而在藝術家眼中則賦予了神性、圣潔、安寧、虛靜等精神指向,因此,這些畫把表象中不可見的東西創造了出來。接下來的一段時間,白色成了繆遠洋筆下游刃有條的存在,無論是山東《峨莊記》系列,還是其他地方的寫生,他把白用得如珍珠、白玉、如林青霞的牙齒,珍貴怡人。但他還是不滿足于成為一個寫生畫家,靠幾個駕輕就熟的題材與色系慰藉永不安分的內心。
二
今日畫壇,寫生創作已成潮流,但塔尖上晨星廖廖。而一個優秀的藝術家與大學教師,須室內室外都能拿得起放得下,須各種題材各種媒介都得有所嘗試,這種高要求把繆遠洋磨煉成了一個多面手。本文重點要談的,正是他以“茶馬古道”國家藝術基金項目為題的系列創作。
在眾多大師中,繆遠洋更喜歡文藝復興前后的一批畫家,比如講究媒材的凡艾克兄弟,魔幻而想象奇詭的包西,具有人文精神且觸覺敏銳的丟勒等。他來到云南快10年了,還沒有像樣的云南題材作品,于2009年開始的馬幫題材的創作,彌補了這個遺憾。
天道酬勤,《風雪夜·前行中的馬幫》一畫,沉郁單純的色調。恍若隔世的人物形象樸素而凝重,略為夸張變形的造型特征,荒蠻古意的山河背景,神秘莫測的風云變幻,拉開了藝術與現實的距離,將人們的想象帶入深沉的歷史記憶中。該畫一面世便引起關注,引領他在崎嶇的藝途中獨辟蹊徑,持續前進,于2015年獲得國家藝術基金“茶馬古道”的資助項目。
茶馬古道是以馬幫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間國際商貿通道,也是物資交流、進行貿易的南方絲綢之路。茶馬貿易始于南北朝時期,至隋唐時期,經西亞、北亞和阿拉伯,最終抵達俄國及歐洲各國。茶馬交易治邊制度從此開始,至清代止。茶馬古道的線路主要有兩條:一條從四川雅安至印度,另一條路線從今天的云南普洱市、西雙版納等地出發,經西藏至緬甸、尼泊爾、印度,國內路線全長3800多公里。兩條線將滇、藏、川“大三角”地區緊密聯結在一起。
從十年前田壯壯拍攝的紀錄片《德拉姆》、繆遠洋的大量速寫與圖像資料中,可以感受其山川之雄奇,道路之艱險,可以窺見沿途各民族的生存習俗,以及對佛教、天主教的信仰。可以發現不少前人留下的石刻、巖畫、寺廟建筑等藝術遺跡。也可以想象千余年來,成千上萬的馬幫人,在雪域高原奔波謀生的特殊經歷與各種傳奇。他們的群體精神,道義互助,與自然的抗爭意志,愛馬如同生命的慈悲,造就了他們講信用、重義氣的性格,鍛煉了他們明辨是非的勇氣與能力。他們既是生意人,也是開辟茶馬古道的探險家。
他們憑借自己的剛毅、勇敢和智慧,用心血和汗水澆灌了一條通往域外的生存之路,探險之路和人生之路,也是一條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其偉大不亞于河西走廊。馬幫人在生與死的體驗之旅中,既飽嘗風餐露宿的艱辛,也飽覽了沿途壯麗的自然景觀,從中所激發出的潛在勇氣,力量和忍耐,使他們的靈魂得到升華,從而襯托出人生的真正意義和偉大。
茶馬古道沿途自然傳播的漢文化與藏傳佛教,也促進了滇西北各民族之間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增進了民族之間的團結和友誼。直至20世紀50至60年代,滇藏、川藏公路通車,馬幫的身影才縮小規模,但清脆悠揚的鈴聲依然響亮在中華民族的記憶里,遠古的茶草香氣依然飄蕩在古道沿途。
道上的足跡和蹄痕還在,歷史的記憶已幻化成今天崇高的民族創業精神。這種拼搏奮斗精神將會鑄成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永恒豐碑,是民族的榮耀與光輝。在今天“一帶一路”的時代背景下,為宣傳保護茶馬古道上的文化資源,樹立旅游品牌,國家把這一文化重任交給了畫家,攝影師,詩人,讓他們的才情與古道風云相激蕩,為歷史留下珍貴的紀念。繆遠洋的茶馬古道系列創作,讓古道重現視覺圖景,延伸和賦予了茶馬古道的新文化意義。
三
繆遠洋在歷時近2年的調研和創作中,經過對茶馬古道人文歷史的分析研究,結合自己的創作特色,很快確立了“古意之美,荒寒之境,表現性繪畫語言”的創作思路。并于2016年2月起展開了玉溪至臨滄、香格里拉、怒江丙中洛三條線路的田野調研及考察。在與中央民族大學和云南大學的專家們共同探討之后,他最終以點帶面,選定大理沙溪作為形象素材的源點。該地有茶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有相對完整的戲臺,馬廄,寺廟,城門,四方街等古跡。他三訪沙溪,通過采風,錄音采訪,寫生,影像及文字記錄等方式對當地的生活狀態,宗教文化做了全面了解與研究,先后完成油畫寫生50余幅,近百幅水彩畫稿和大量速寫,數十小時錄音及幾萬字的筆記,終于成就了《守望的馬幫》和《古道風云》的系列創作。
維特根斯坦在談到自己的哲學思想時說過:“我的原創性是一種屬于土壤的、而不是屬于種子的獨創性。在我的土壤上撒下一粒種子,它會成長起來,而且,它的成長將與它在其他土壤上的成長不同。”丹納也強調民族社會環境和歷史時代是決定藝術的重要條件。而在藝術創造的活動中,純粹精神與心靈的介入并非萬能和強力的,只有與歷史、民族、地緣及現實傾向結合時,它才能獲得動力和被實現的可能。在茶馬古道上,繆遠洋面對的一方面是相對恒定的自然環境,一方面是已經逝去或即將消失的歷史記憶。
歷史記憶的模糊和神秘性,必須以超出經驗的感覺去把握,能與他審美體驗中的神秘性相接通的,是深達人類精神與意識底層的原初意象或幻象。借助對幻覺的感悟與想象還原,才能將眼前的形象從現實抽取并超升出來,使之接近歷史,并擺脫已被別人實踐過的歷史畫創作模式。因此,馬幫系列作品所呈現的視覺形象,首先是被主觀改造過的客觀,是知覺的創造;第二是對日常經驗的疏離與規避,顯示出難以言喻的神秘性;第三是畫者給觀者帶來審美陌生感的同時,也帶來愉悅的滿足與沉思。此時的馬幫群像,與繆遠洋是一種全新的構成關系,他把自已對茶馬文化的理解,深邃而明確地滲透在人物造型之中,也融合在天地間的背景之上。
歷史畫的表現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也不等同于紀實照片和影像,他是藝術家對歷史的感悟與判斷,是其審美經驗與技藝的心靈投射。歷史畫如果沒有個人及活著的文化介入,那就不是藝術。歷史題材作品需要作者能代歷史言說人類的尊嚴與偉大,否則,還不如一張老照片。歷史畫的創作不僅意味著時代的聚焦,社會責任和意義的顯影,也意味著生命流程的精神滋潤與人文寄托和關懷。作為深受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影響的新時代畫家,其具像寫實語言與以往的現實主義美術必有一定的差異,如同馬幫人面對前方沒路的困境一樣,必須去探險與超越。
四
在繆遠洋之前,我還沒見過有人將茶馬古道當做一個持續的油畫創作主題,不斷發現與挖掘,這對他來說是一個缺少借鑒的挑戰,也考驗他形成作品獨特性的才能。因此,他在繪畫語言上的運用是多向的,寫實,寫意,抽象等各種表現手段,他都通過學習滲化而為己所用了。其畫面結構和諧,古意色彩濃重,形成具有魔幻現實主義傾向的具像表現風格。
魔幻現實主義一直處于小眾、邊緣、非主流狀態。早期有魔幻傾向的西班牙畫家洛佩茲也認識到,世界因存在著看不見看不透的神秘事物而難以把握,但眼前能見的東西卻可以抓住,于是后期轉入具象寫實。具有魔幻氣質的繪畫的出現與一個地區存在大量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宗教典故相關。其總體特征是對理性與現實世界的反叛,具有象征性,寓意性與夸張的特點,往往打破時空界限,人神界限,主客觀界限,追求對真實的深層次探索與發現,看起來似真非真,處于既具體又模糊的虛實交界,常常抽象意境與具象實體相搭配,它注重細節又不同于日常經驗所認識到的世界,給人神秘怪異的陌生感。
正如該派當紅藝術家彼德·多伊格所說,作畫時,會習慣性地重溫現實中的一切,尋找自然和它本身的不真實之間那個有心理意義的地方。但它本質還是現實主義,是物質世界,現實的“真實性”依然是標準。只是規則不見了,荒誕的,不合情理的,不可能的想象突兀地出現了,其更高的層面是結構上,時空上的反常規。如此看來,繆遠洋在云南這塊神秘之地借鑒這種意識創作是可行的,但也是艱辛的,能走到什么程度還要往后看。
繆遠洋的早期大頭系列明顯有此傾向,而寫生中畫面的各種真實法則同樣存在打破重組。馬幫系列作品因面對的是一個時空跨度很大的題材,與事件性的歷史題材也不同,設置固定的場景情節或選取某個戲劇性的黃金分割點創作并不足以呈現其神秘復雜,而借鑒魔幻現實主義的某些創作手段倒也明智,但把握其中的度很關鍵。
他畫中單個的馬幫人物造像,頂天立地的構成中,人與景就是兩個現實的重組,特定服飾及原型的選擇,只是為了表現特定民族的特質與精神。氣勢恢宏開闊的長卷式構圖則數易其稿,在起承轉合的復雜結構中,人物,馬匹,山體道路甚至貨物的色彩及面、形構成整體上是渾然一體的,并未全部遵循常識中準確的空間位置關系,比例,透視,色彩則是靈活處理的,包括畫面橫向上的切斷組合也不影響各形象與全局的同構關系,而時間上的暗示則是陰晴晨昏并置的,人物設定涵蓋了趕馬人、探險家、僧人、旅人等,他們的表情既虛幻也真實,展現出群體精神的豐富結構,喚起所謂的“人民記憶”。
按福柯對“人民記憶”的理解,這是一種“意識的歷史運動”,是民族語言的文化生存的核心因素,是普遍的文化底層中的選擇與構造,是歷史記憶的無意識的書寫話動。而藝術是不同文化民族中可以自由交流的視覺語言,是可以把握的歷史話語。畫面上的古意即使采用歷史感的灰暗色,古典式的嚴謹線條,也代入了中國傳統審美中注重情態情韻的寫意思想,體現王維“寫像求形,或皆暗識”的時間意識。
從繆遠洋2016年12月結題的“茶馬古道”項目系列作品中,他所提供給我們的信息是豐富的。他的10件作品,創作構成完整,抓住了典型的人物與場景,不僅呈現遙遠、神秘、荒涼、艱險,也畫出了滄桑背后的莊嚴,堅韌、勇氣和力量。從他另一些具有歷史情節的作品比如《關索古意》《1938年》系列中,也可以看到他駕馭歷史題材的才能是充盈,看待歷史人物的態度平實,創作時沒有拔高和美化,與司馬遷著史一樣,這是一種可貴的品質。盡管筆下的形象大多源自民間的平凡人,但他們何嘗不是英雄。英雄不問出處,更何況他們是從沒有路的地方踏出了路。
云南的歷史主題創作,之前有趙力中等少數幾位老畫家涉獵,平時很少見青年畫家去碰。故與北方省份相比,云南這一類別的創作面貌略顯弱勢,其原因多樣,不是本文要說的話題。只是看今天,有像繆遠洋這樣正值壯年的70后在創作研究,便覺珍貴,也心存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