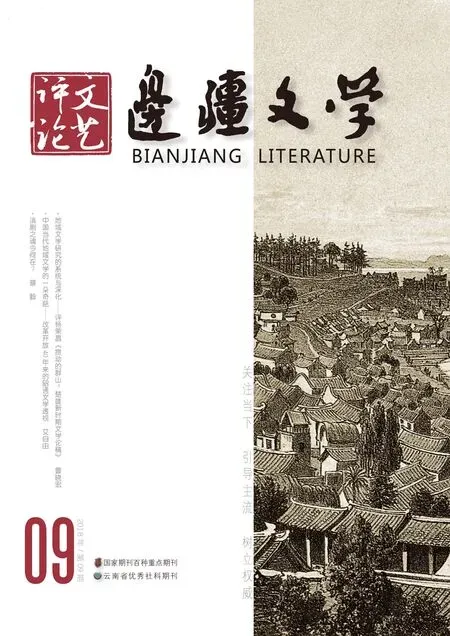第十二屆全國舞蹈展演作品短評三則
劉 麗
1.評舞蹈《靈·境》
舞蹈《靈·境》是一個關注人類環境保護的現實題材舞蹈作品。舞蹈響應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云南時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保護理念,以哈尼族民間舞蹈“棕扇舞”為素材,提煉出舞蹈形象,表現了哈尼族人在白鷴鳥的指引下捍衛青山,堅守家園,再現一方靈境的情景。舞蹈編導是云南省新銳青年編導、云南藝術學院舞蹈學院教師鄧鈺瑩。
看完這個作品,我首先想到了著名舞蹈編導家張繼鋼在其《〈侗寨人家〉導演手記》中談到的一段話:“藝術家面對民族題材首先看到的是風貌,但不能最終還是風貌。持續沉醉于民族風貌最容易使民族藝術表面化、類型化,是淺層次的‘像不像、是不是’的徘徊,區間也狹小,很難有高層次的突破和提升。學會民族的語言,目的不是作繭自縛,而是破繭成蝶。”
實際上,少數民族舞蹈創作如何“破繭成蝶”,突破民族題材的風貌原型,避免舞蹈作品表面化、類型化的風俗再現,一直是云南民族舞蹈創作在探索的現實問題。舞蹈編導在面對熟悉的少數民族題材和舞蹈素材時,不能只是沉醉于民俗原型或舞蹈動作形態的提煉,還要賦予民族舞蹈素材以新的語言內涵和藝術形象,要把握傳統與時代的融合延展,豐富民族傳統舞蹈藝術的文化內涵與當代意義。這樣,我們的少數民族舞蹈創作才能真正做到“破繭成蝶”,延續民間傳統舞蹈的文化生命,提升其當代審美價值。
從這一層面來說,青年編導鄧鈺瑩創作的《靈·境》應是找到了“破繭成蝶”之路。在我看來,這個作品的“繭”便是“棕扇舞”作為哈尼族民間舞蹈固有的傳統內涵和風格樣貌。“棕扇舞”原是哈尼族獨具特色的祭祀性舞蹈,哈尼族視白鷴鳥為吉祥、靈性的鳥,相傳是白鷴鳥帶著哈尼族祖先找到了美麗富饒的居住地。老人去世后,白鷴鳥能夠把消息傳遞給天神和先祖,帶領死者的靈魂回到祖先的故居地。“棕扇舞”的核心動作形象是白鷴鳥,人們手持棕扇模擬白鷴鳥飛翔、漫步等形態,舞蹈節奏緩慢,氣氛莊重肅穆。在這個傳統舞蹈中,白鷴鳥與哈尼族的家園意識構成了一種內在的文化邏輯關系,是一個民族強化根脈記憶、維系民族情感歸屬的重要文化意象。對于《靈·境》而言,這個文化意象便是意義深厚的“繭”。
那么,如何在哈尼族民間舞蹈的傳統形態和文化意象中“破繭而出”,既尊重民間舞蹈的傳統文化特性,又不拘泥于原有舞蹈語言的限定性?編導鄧鈺瑩抓住了“‘棕扇舞’—白鷴鳥—家園”在哈尼族文化中的內在關聯,提煉出白鷴鳥這一鮮明生動的“靈”,從哈尼族的家園意識中引申出保護自然生態的新語境,在動態形象上突破民間傳統舞蹈的風格限制,做到了在傳統與時代的融合延展中創造新的藝術形象,是為“蝶”。
記得張繼鋼還說過:“……我們創作少數民族的藝術不能用‘少數民族’的心態,不能手里拿著盾牌,不能讓大山擋住視野,靠狹隘守護不了家園……如果是擔負起責任的民族,就不要總是在自家門口觀望。要議事就要站在寨門口,要思考就要站在山頂,站在更遠更高的地方……”在舞蹈《靈·境》中,我們看到了云南新生代舞蹈編導在少數民族舞蹈創作中的新視野和新探索。
當然,從舞蹈本身的編排來說,《靈·境》以哈尼族民間傳統“棕扇舞”為素材,大膽開發身體語言,道具運用變化豐富,隊形畫面大開大合、行進流暢。但若能在白鷴鳥的形象塑造上更加突出“靈”的意象,舞蹈意境中加強“靜”的遐思,整體節奏再把握好張弛有度,舞臺上的形象便也不是那么“喧鬧”了。在云南省入選第十二屆全國舞蹈展演的7個優秀劇目中,《靈·境》是唯一一個選自專業藝術院校的舞蹈作品。鄧鈺瑩是一個勤奮、有靈氣的編導。
2.評舞劇《杜甫》
“一個人筆下的唐朝”,這是舞劇《杜甫》開端與尾聲反復強調的一個意象。這個人便是唐朝著名的“詩圣”、現實主義詩人杜甫,他的詩也被稱為“詩史”。杜甫所處的年代,恰是唐朝由盛轉衰之時,他氣節高遠,卻命運多舛;仕途不順,又經戰亂之苦;顛沛流離,仍憂國憂民。了解了杜甫生活的時代和多舛的經歷,我們便也讀懂了他“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憂思心境。他的詩情,在于國,在于家,在于民;他的詩意仁民愛物、悲天憫人……
舞劇《杜甫》正是在這深厚的人格基調中,以杜甫的“詩”為意境,以“詩”構“舞”,以“舞”敘“事”,以“事”抒“情”,寫意式地為我們呈現了杜甫的人生境遇和家國情懷,鋪敘了杜甫筆下的唐朝往事。
無疑,該劇的編導韓真和周莉亞對舞劇的結構布局和人物的性格刻畫有著深厚的創作功力。首先,舞劇的結構定位為“塊狀結構”,這一“塊狀結構”不同于傳統舞劇的“戲劇性結構”模式,不刻意強調人物事件發展的線性情節,而是以一個個獨立的舞段織構出不同的場景,連接起國運民生的跌宕起伏與杜甫的人生起落。舞劇以杜甫的追憶為線索,一虛一實兩個杜甫貫穿全劇。上半場主要描寫“長安十載,求官謀事為蒼生”,下半場主要描寫“棄官歸隱,筆底波瀾驚風雨”。舞蹈評論家于平觀看舞劇后,將上半場的舞段歸納為“求仕行”“麗人行”“兵車行”和“難民行”,下半場的舞段歸納為“亂世行”“長恨行”“別離行”和“農樂行”。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舞段分別塑造了杜甫、仕、權、妃、兵、妻、民等形象,勾勒出當時的時事政局和人間百態,表達了杜甫的政治抱負和憂國傷民的心境。舞劇用“塊狀結構”的設計,避免了人物故事情節的繁瑣鋪陳,空間轉換節奏快。舞段之間雖無必然的故事情節關聯,但卻表現出清晰的邏輯關聯,以詩敘史、以情述史,最終達到“史詩”般的效果,讓觀眾在強烈的視覺效果和心理呼應中感悟“一個人筆下的唐朝”。
編導韓真和周莉亞在這部舞劇中表現出的另一個深厚的創作功力,便是舞蹈語言的建構和舞蹈形象的塑造。甚至可以說,編導對舞蹈語言的把握能力很強,刻畫人物形象也入木三分。例如,在“求仕行”“兵車行”“難民行”等舞段中,為了刻畫杜甫的性格,編導緊緊抓住“作揖”的動作大做文章,在“作揖”的身形舞態上進行語言構建。“求仕行”中,眾士子為求官職,深躬作揖、匍匐在地,極盡所能討好權相;官員們的“揖”卻做出反勢,以仰身向上的動作路線在舞臺上穿梭行進。士子與官員“作揖”的動作形成巨大的反差,意喻這官場丑態。杜甫則得意于自己的才華,不屑于深恭作揖討好權相,顯得與眾士子格格不入,似乎成為杜甫仕途不順的前因。而在“兵車行”和“難民行”中的杜甫目睹戰亂之苦,焦慮萬分,向權相求愿不成,無奈之下竟也學起了士子們“深恭作揖”的奴態,百般苦求。接著,編導通過動機的發展,不斷強化“作揖”這一舞蹈語言,傳神地深化了杜甫的人物性格和憂國憂民的仁愛精神。此外,“麗人行”中慵懶華貴的貴妃之舞、“兵車行”中的弓箭舞、“農樂行”中杜甫與鄉親們的率性之舞等舞段,都對應著杜甫詩中所述的情景,舞蹈編排流暢,意境綿長,豐滿著舞劇的“塊狀結構”,使整個舞劇有血有肉,引人深思。
遠在唐朝的杜甫以儒家仁愛思想感時撫事,以同情之心關注社會最下層,表現出極大的人文關懷,以至于魯迅這樣評價:“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里似的……”。從這個角度說,編導能選擇杜甫作為創作題材,以杜甫的“詩史”人生來觀照現實,強調藝術創作要扎根人民,是難能可貴的。舞劇《杜甫》不是現實題材的舞蹈作品,但卻蘊含著濃厚的現實主義精神。
3.評哈薩克族舞蹈《水草·逐》
《水草·逐》是一個哈薩克族舞蹈。作品以一個女人對逝去年華的追憶和追逐,娓娓道來“往事尤可追,未來更可逐”的生命感悟。作品的文化基因源自哈薩克族歷史久遠的草原文明和生存態度。在他們的生命體驗中,有水就有生命、有草就有生活。逐水草而居,實質就是追尋著生命的方向詩意前行。一代又一代,一生又一生,依山傍水、逐水牧草,這是所有草原文明對時間的適應,這是所有草原智慧對歷史的適合。舞蹈力圖通過塑造一個哈薩克女人追憶青春的形象,隱喻哈薩克人對自己文化記憶的回眸和對草原智慧的回溯。流動的舞蹈畫面如同哈薩克人穿梭于歷史時空、游走于大草原上般自由、奔放。
在與《水草·逐》的編導、新疆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舞蹈系主任戴虎交流時,我發現這個作品除了在主題上強調宏闊的審美建構,在創作旨趣上更有一種“實驗”的科學品質:他們試圖在以風情見長、情緒為上的新疆地區民族民間舞蹈創作的歷史主流中,嘗試性地將人生況味的哲思融匯進舞蹈構圖中,平添一份從舞蹈形式引申出的思考意味,令平面化的審美更有一絲“閱讀”的愉悅。
有關新時代中國民族舞蹈創作新范式的討論,是一個開放的話題。就《水草·逐》這個作品的服裝設計、音樂制作、動作設計、舞段構圖、形式意味和主題思想上來看,都能感受到編導對傳統舞蹈文化資源進行“陌生化”創作的自覺。應該說,《水草·逐》是沿著“傳統舞蹈的現代表述”的創作思路展開的,在動作設計上強調哈薩克族傳統舞蹈風格的準確,而在文化表述和情感象征上,卻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風格性表達,讓我們感受到編導“民族的更是現代的才會是世界的”文化創新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