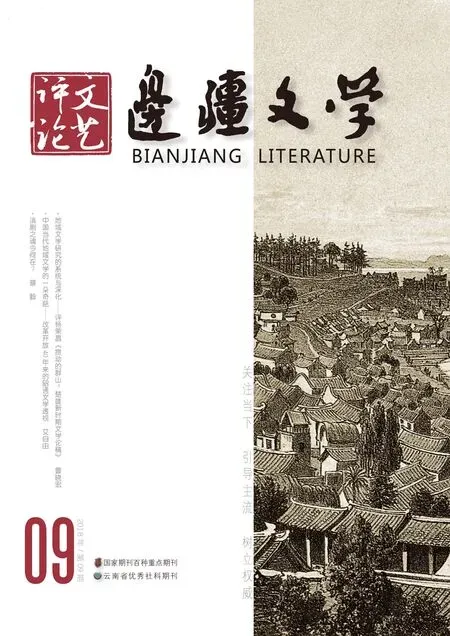讀萬吉星近作小小說十篇
蔡 挺
云南寫小小說的不多,寫好小小說的更少,而且,云南文學寫作群體、評論群體乃至文學評媒,似乎都小看小小說,覺得小小說分量輕,不入“法眼”。事實上,文學無卑微,寫好了就了不得。小小說體微,質卻不輕。阿根廷著名作家胡里奧·科塔薩爾說:“在一個使人激動的文本和其讀者之間進行的那種較量中,長篇小說總是以點數取勝,而短篇小說則必須擊到對方才能取勝。”(見《大益文學》公眾號文章《胡里奧·科塔薩爾指南》)科塔薩爾的短篇小說就包含眾多可以劃歸小小說范疇的作品(甚至有不少可以劃歸600字內篇幅的閃小說范疇的作品)。
以字數論“英雄”,本來就大謬,白居易詩《問劉十九》僅20字: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
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長恨歌》卻達840字,誰說《長恨歌》勝于《問劉十九》?
閑話少說,還說云南小小說。云南小小說寫作領域,目前看也許尚未有大家出見,但萬吉星是一匹勁頭正足的“黑馬”,就目前的寫作狀況看,他也臨寫作佳境之中,后續的爆發足以讓人期待。
閱讀他近來發表的十篇小小說:《愛心墻》《百花嶺》《拾荒》《還差一條路》《朋友圈》《最好的禮物》《名人》《遺產》《希望》《無為》。我發現,這些小說莫不是與現實零接觸,選材大多涉及普通人生活,他或沙里淘金,找到普通人身上美好的質品,真誠點贊,或肉中挑刺,尋找到社會肌體的痛點,加以貶置。說他的小說承載著作者的情感、期許、關懷,還有其獨到的發現,當無不當。
《愛心墻》首發于《時代文學》,被多家選刊先后轉載,寫小王兩口子搬到小區居住,將土雞蛋送樓上樓下鄰居們,但鄰居們各種拒絕,讓小王“感覺心里很冷”,小王的孩子夜哭,又攪得樓上樓下鄰居不得安寧,小王借單元樓前的空墻貼張小紙條,請鄰居們理解和包容,于是,鄰居們紛紛獻策,后來空墻成了“愛心墻”,鄰居們也熟起來,友好起來。
《愛心墻》讓我想起了所謂“鯰魚效應”:有人遠距離販賣沙丁魚,因為沙丁魚性冷懶,不喜游動,死亡率極高,后來販賣者在里面加了幾條鯰魚,他們在沙丁魚中串來串去,沙丁魚跟著動起來,死亡率降到幾乎為零。
小王貼小紙條之舉,營造了一個小區的“鯰魚效應”,當然,人們并非冷懶的沙丁魚,他們是裝成沙丁魚的鯰魚,愛心墻即鯰魚本性的喚醒。
總是看起來“芊芊渣渣”的小事,出現在萬吉星的小小說中,必擁有“以小見大”的功效。《拾荒》:王婆婆拾垃圾,扮到一個先天心臟病嬰兒,因不得兒子兒媳的理解,他帶著嬰兒寄住別人家,并為嬰兒治病拿出“棺材本”,也引起了社會的關注,捐款30余萬元,但嬰兒仍然“走了”。王婆婆手里尚余十幾萬元,兒子兒媳又來打主意。王婆婆果斷與“親情”決裂,將余款捐出去,自己仍用破舊的垃圾袋拾著垃圾。窮且益堅,守住善良,也守住我們內心的感動。
《最好的禮物》:莞兒就要生日,但爸媽一個眼盯電腦,一個眼盯手機,都“忙”著。爸爸雖然承諾買禮品,卻不愿在女兒生日花費時間。莞兒于是用自己存錢罐里的錢給爸爸“買”時間,讓爸爸陪自己半天,是的,當我們說人與人之間的心理距離變大起來人與人之間關系疏冷起來,想沒想過,我們是不是助了“一臂之力”?
《遺產》:牛二恨父親,少小離家,在“里面”蹲了三年,出來后蒙遠房表親德山叔收留,在其手下干起了民工,其父卻訴諸法律,要他支付每月800元的贍養費。父親去世,他因為有“遺產”繼承,回家奔喪。德山叔卻將他六年間給父親的贍養費交還他。原來,父親是因為他亂花,有意為他存著,而且,因為他入獄,父親為他哭瞎了眼睛,他出獄,德山叔的出現,也是父親的有意安排。真的是父愛如山,山沉默,山豐贍。
萬吉星對社會的洞悉,總體現在普通人身上,他既關注弱勢群體,情感同樣游驛在作為普通人的小官員身上。
《還差一條路》 :兩任鄉長,前任李鄉長修的是“看不見的民心路”,繼任秦鄉長修的是“看得見的政績路”。秦鄉長終于咎由自取,副縣長的官帽得而復失,恰恰相反,李鄉長升為副縣長,他們都“還差一條路”沒“修”,讓“看不見的民心路”的筑造者終于勝出,也貼合了時下的政局民意。
《朋友圈》:領導秘書陸文軒疏于交際,不能解決孩子上全市最好小學“師大附小”的問題,在妻子的催促下,他找了在教育局當科長的老同學王浩宇,并將自己珍藏的價值七八千元的畫作送給王浩宇;王浩宇幫不成忙(師大附小是民辦小學),故而委托建筑公司陳總,陳總又委托秘書小王,因為小王有個姐夫在市政府“當領導”,小王的姐夫就是陸文軒……像一則笑話,卻并不“無厘頭”,點出作者隱隱的擔憂,不走正當門徑,跑“關系”,這種世風幾時休啊,利用手段搶灘教育資源,這種狀況又幾時才能肅清?
此外,因為“在縣長旁邊作報告”而成為“名人”,帶給老鄭“名人”的憂郁(《名人》)。自己“渾身是勁兒”干工作,受到上級領導的賞識而被提拔使用,秦楓還以為得到了市里副書記的提攜(《希望》)。有意疏忽工作得到領導對部門的重視,撥款改建破舊的辦公樓(《無為》)。幾篇作品,都從一個側面表現了社會的某種亂象和作者的思考。
《百花嶺》這篇小小說在整組小小說中頗顯另類,若非要給個名目,我以為是生態小小說,雖寫人(我、鄉長、旅游局長、縣長、幾個老鄉),相較卻是次要的,外面鮮知時百花嶺美侖美奐,名聲在外引來接蹱而至的參觀者,為了接待參觀者,各種服務設施緊緊跟上,連高爾夫球場也落駐了,百花嶺變成了有名無實之處。
通覽全部小小說可知:萬吉星的小小說取向,正是見微知著的建立。其人在云南,其旨所立卻并不囿于云南,帶著我們時代的征兆,有無奈,有痛楚,同時,又讓我們看到希望。
取平實的語言,蘊胸襟中的真情,棄煩頊之蔓枝,作精致的小幀。給予其小說耐讀、耐嚼、可品,讀罷,不由得不思索——此正是小小說寫作之道:在有限的文字終結以后,有漫延的回味撲面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