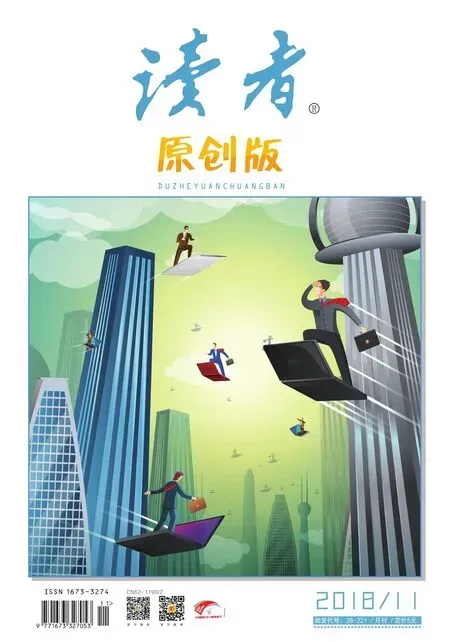跟番茄有關的事兒
文|李 子

美國大部分的番茄都是在加州種出來的。溫暖的加州中央山谷,沿著99號公路一望無際的番茄田,每年夏秋之際為全美國產出1400萬噸番茄,運到超市、餐廳以及每個人的沙拉碗里。
規模為什么這么大?產量為什么這么多?這跟20世紀60年代的幾件事情有關—不一定都是好事兒。
曾經,番茄種植是一個勞動力密集的事。在收獲季節,農場需要雇用大量的工人將一顆顆柔軟脆弱的番茄用手摘下來,然后在它們壞掉之前,沒日沒夜地往卡車上裝箱。
20世紀50年代,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別名“加州農大”)的兩位科學家兼工程師 Jack Hanna和 Coby Lorenzen 聯合發明了一種收番茄的機器。這種機器能夠將番茄整株拔起,除掉枝葉,直接進入清潔和運輸環節,省下大量的人力成本。
見過這種機械的人都會驚嘆其效率,這幾乎可以改變整個番茄行業的生產邏輯。然而問題在于,機器實在太貴了。
這時候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美國的《墨西哥勞工法案》剛好在1962年走到了盡頭。因為這個法案,美國在二戰時期從墨西哥引入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用于補充戰時經濟,然而在戰后,這變成了一個社會問題。國會經歷了十幾年的扯皮和拖延,總算讓它壽終正寢。
這件事對于番茄農場而言,意味著即將面臨勞動力的嚴重短缺。
這時候,大型農場首先行動了起來。他們和當地金融機構合作,引進了這種剛剛發明的大型機械。戴維斯分校的科學家也很開心—發明投入了應用,研究經費也滾滾而來。
改變幾乎發生在一夜間。勞力被大大節省下來,成本的降低是肉眼可見的。只花了5年,番茄收割機的普及率就達到了90%以上。
然而,這卻帶來了十分嚴重的社會代價—只有大農場才買得起機器;沒有機器的小農場,在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根本無法與大農場競爭,只有關門或者被并購的份兒。5年時間,原本5000多個農場,消失了4500個。多少農民好幾代積累的事業煙消云散,3萬多名農場工人被迫失業,甚至流離失所。
或許讀到這里你會說:“這不就是資本主義嗎?有什么好稀奇的。”
但是還有另外一件你可能沒想到的事情,那就是番茄本身的改變。
為了讓番茄能夠更好地被機器收割,不至于變成“番茄醬”,戴維斯分校的農業專家研究培育出了一種硬番茄。這種番茄的表皮更厚、汁水更少,更適合這種大規模、低成本的種植。
然而育種的代價,就是番茄的味道變得平淡無奇。(當然,番茄變難吃也有另外一些原因,這是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這種收割方法需要將番茄整株拔起,同一植株上的番茄,其成熟程度并不同步。沒熟的只好使用乙烯催熟,這更讓番茄失去了原本的風味。
這樣的番茄也改變了美國人民的餐桌。鮮嫩多汁的番茄沒有了,使用大量作料和油的沙拉成為主流;而番茄醬里只好加入大量的人工添加糖—這讓美國人民的腰圍漸長。而那種曾經“正常”的番茄,只有在大城市昂貴的有機超市才能買到了。
沒錯,這就是技術進步,這就是資本主義。可是,有的東西,是技術、資本和錢買不來的吧。比如許多人兒時記憶里那一口香甜的番茄。
這件事情還有一個有趣的后續。1979年,加州農業行動項目(California Agrarian Action Project,一個小農聯合機構)將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告上了法庭。
理由是,戴維斯作為公立大學,使用的是所有納稅人的錢,然而研究的結果卻讓少數幾個大資本集團獲益。這對大部分人來說并不公平。
漫長的官司持續了10年,最后以農民敗訴告終。不過,戴維斯在經歷了這場公關危機之后開始反思,什么樣的技術能夠惠及更多的人。他們后來也投入了一些研究力量,希望用技術去改變那些被資本邊緣化的人群的生產境況。
番茄收割機的誕生是歷史推動的,而它也以一種人們或許未能料到的方式改變了歷史。技術從來都不是簡單地將科學進步變成機器而已,沒有一項發明創造可以從社會剝離開去,所有的一切都在于,你從技術當中看到了什么。
我希望以后的技術,可以更多地看見“人”。不管是算法、人工智能還是智慧城市,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