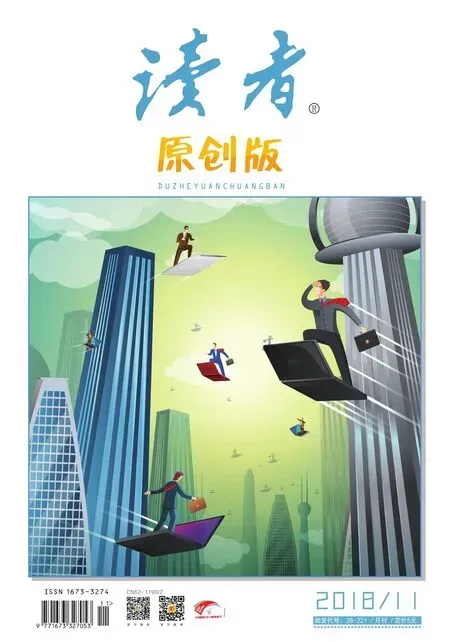當日本進入第四消費時代
文|李 停

最近一個學市場學的研究生朋友推薦我看三浦展的《第四消費時代》。我看完有兩個感受:一是很有意思,二是我現在就生活在第四消費時代,就是現在的日本。
按照三浦展的劃分,日本共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
第一消費時代是從大正時代起到二戰前(1912年-1941年),西式的商業社會逐步形成,人口向大城市流動,都市建設日新月異,日本開始有了電燈、百貨公司、劇院、寫字樓、公寓,街上經常可以看到打扮時尚的“摩登女郎”。不過,當時能享受這種消費的僅限于東京、大阪這些城市里的中等以上階層。
第二消費時代是從戰后到石油危機(1945年-1974年)。隨著城市化進程在全國推進,日本迎來了經濟大發展。這個時代消費的最大特征就是家用電器開始批量生產,進入尋常百姓家庭。由于經歷著“從無到有”的轉變,這一代消費者的需求是大眾化、標準化的,廠家只要生產大量產品,不需要太多營銷手段就能順利地賣掉。而大家對“好東西”的認識還處于“大就是好”的階段,要買更大的彩電、更大的車子,擁有比別人更大的商品就更幸福。在這個時代,消費被認為是美德。日本經歷了連續18年年平均經濟增長9.1%的繁榮時代,直到1973年石油危機,次年變成負增長。第二消費時代戛然而止。
第三和第四消費時代的更替是模糊的,并沒有一條明顯的分界。三浦展把每個消費時代大致定為30年,第三消費時代是1975年-2004年,第四消費時代預計是2005年-2034年。由于第四消費時代的興起與第三消費時代密切相關,這兩個時代被放在一起討論。
第三消費時代是追求個性的時代,人們對標準化的、重量不重質的消費觀念嗤之以鼻,希望通過購買特色商品體現與眾不同的自我。據此,廠商也提出了新的營銷策略。本來,在第二消費時代,電視機這種家電已經實現了一家一臺。于是廠家開始推廣一人一臺、一屋一臺的戰略。比如手表,不同的場合穿不同的衣服、配不同的手表是常識吧,你不能只有一塊……通過這種方式,人們的消費欲望被成功激起。
第四消費時代的苗頭是沒有經歷過泡沫經濟的年輕人開始進入社會。在他們的成長歲月里,整個日本經濟都處在一種微溫的狀態,“華麗麗花錢”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另一方面,托早年高速發展的福,家里該有的都有了,那種“好想要”的心情比起前一代人大大跌落了。
從技術背景上看,信息社會的發展也進一步深化。信息這種東西和物質不同,只有通過傳播、交換、與他人共享,才能體會到擁有信息的樂趣。由此,人們獲得幸福感的思維方式就發生了變化:原來同他人建立關系就是一種快樂。大家開始感到,把大量的金錢花在與人攀比的消費上真是沒有意義,真正難得而有意義的是“美好的時間”。拿錢購買體驗是值得的。比起物質,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感會帶來更大且持續的滿足感。
我和身邊的朋友都感受到自己正身處第四消費時代。
我的一位朋友,38歲的企業中高層,日本人,他的內衣內褲都是定期去GU買。GU是什么?是優衣庫的年輕副線品牌。優衣庫一件T恤80元人民幣,GU才40塊,是比優衣庫還便宜一半的那種便宜地方。可他年收入完全是中上層的。他根本不介意別人知道他買GU,因為“以你的消費水平而評價你”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了。
同樣階層的日本人,不僅平時在優衣庫和GU買衣服,在nitori(比宜家還便宜的日式家具店)買家裝,買車也傾向于便宜的日產、豐田等。在東京,除了六本木和港區之類的明星聚集區,很少看得到奔馳、寶馬和奧迪。
要知道這些人的收入真的已經很高了,負擔更高的消費完全綽綽有余。那他們愿意把錢花到哪兒?
我寫過一個在工地做監工的60歲的日本人來學中文的故事。他自費來學中文,只為了能更好地給游客指路—中文學費并不便宜。這一點,很多中國人不會理解,但這就是日本人的花錢之處。
在日本,書籍很貴,看電影很貴—沒有盜版,快遞費很貴,很多服務項目都比中國的同等水平消費要貴上幾倍。但日本人在這些方面花錢,仿佛毫無知覺似的。
而換個角度來看,這樣各個行業的人都不會過得太差。只要你愿意工作,打工賺時薪也能過上好日子,也能休假去旅游。大富豪吃得起的,只要不是每天吃,普通人也可以吃得起。在日本,有個說法是“一億中流”—日本國民一億人,一億人都是中流。
日本人的錢不再用于買名牌、買大件,那花到哪兒去了?
我認識一位30歲的日本單身男性,大學的普通職員。老家是京都的,一個人在東京。他租房、坐電車,但半年會出去旅游一次,平時買書(日本的書一本少說1600日元左右,約合100元人民幣),買電子產品,買男士護膚品,夏天沖浪,冬天滑雪,還跟朋友去釣魚、露營。
這是很普通的單身生活。大家都有自己的興趣愛好,尤其是運動和旅行方面,幾乎每個日本人都定期做。這很花錢,也很健康。
在這樣一個社會,人們不再追求經濟飛速發展和效益最大化,而是享受簡約的生活方式;不再終日奔波、蝸居在大城市,而是重新發現地方的特色和自然的力量;不再努力工作、拼命掙錢,苦心鉆營求升遷,而是幫助他人、共享快樂,獲得內心的平靜與幸福。在這個社會,環保節約成為一種文化,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自然而溫暖。這就是第四消費時代,告別了“物質使人幸福”的時代,人們開始追問“除了物質之外,什么才能讓人感到真正的幸福”。
我寫過日本人的戀愛故事,人們給我反饋最多的就是“溫柔、溫暖、甜”,還有個讀者說“在充滿戾氣的社會看到這樣的愛情故事使人振作”。我看到“戾氣”這個詞才恍然大悟:我離那個詞已經很遠。在第四消費時代里,沒有戾氣。溫暖、溫柔,是我最常感覺到的,自然也是我最常發散和回饋出去的。
用心地對待每個服務業的人,想象他們是自己的朋友或親人,想象他們在服務業之外的喜怒哀樂。在街頭采訪里,問到單身日本男女在選擇另一半時最看重的品質的時候,竟然有一大半的人回答“要看他(她)對服務員的態度,因為這最能反映他(她)本性是否溫柔”。對不相干的人溫柔,是種高貴的品質。
這是經歷了社會環境變遷之后的結果,也是因為人們對精神層面的重視而得來的自發性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