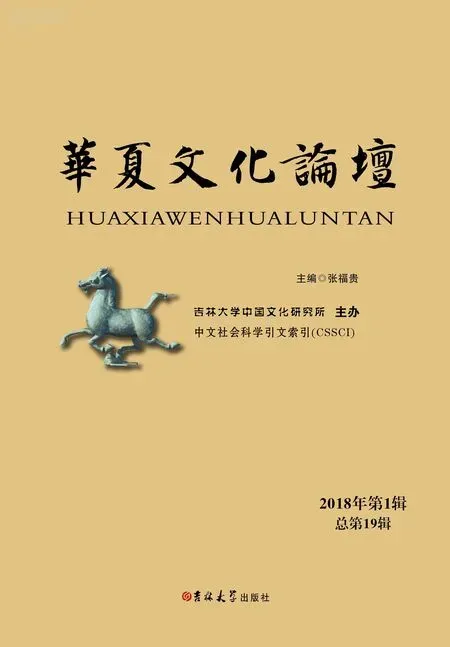釋智猛及其《游行外國傳》鉤沉
呂 蔚 陽 清
【內(nèi)容提要】東晉末期,雍州沙門釋智猛巡禮佛國,后撰有行記《游行外國傳》。智猛《游行外國傳》雖已亡佚,但為多家史志著錄,歷代類書以及總集亦有征引,足見此書曾別部自行。僧祐《出三藏記集》智猛附傳,實(shí)以智猛行記為材料依據(jù)并經(jīng)刪改而成。附傳多處敘及智猛經(jīng)行路線以及異域風(fēng)光、釋迦遺跡、佛教見聞等,必為《游行外國傳》之應(yīng)有內(nèi)容。與晉唐其他僧人行記類似,《游行外國傳》呈現(xiàn)出了多學(xué)科交叉研究的獨(dú)特價(jià)值。智猛抑有赍經(jīng)翻譯之舉,其所譯《泥洹經(jīng)》二十卷,隋唐經(jīng)錄多有著錄,同樣表現(xiàn)出一代高僧為弘揚(yáng)佛教所做出的犧牲和努力。
佛教?hào)|傳之際,中土僧人行記應(yīng)運(yùn)而生。究其產(chǎn)生機(jī)制,一是緣于漢地“宗派未圓,典籍多闕,懷疑莫決”,二是因?yàn)楦呱畬?duì)佛國心向往之,渴望親歷其境,由此“發(fā)憤忘食,履險(xiǎn)若夷。輕萬死以涉蔥河,重一言而之柰苑”。而一般情況下,高僧自撰行記與赍經(jīng)翻譯并行不悖,兩種文獻(xiàn)類型均產(chǎn)生于其歸國之后。向達(dá)指出:“魏晉以降,佛教傳入中國,西域大德,絡(luò)繹東來;東土釋子,連袂西去。歷游所至,著之篇章。法顯《佛國記》與玄奘《西域記》后先輝映,為言竺史者之雙寶,治斯學(xué)者莫不知之。”事實(shí)上,中古佛教行記不止《佛國記》《大唐西域記》兩種,六朝佛教行記“別行于世者曾有十種,惜其大多亡佚不存”,唐朝佛教行記別行于世者亦應(yīng)有多種,歷代史志、經(jīng)錄屢有著錄,某些古注、類書多有征引,某些大藏經(jīng)或亦收錄,釋智猛撰著《游行外國傳》即其中之一。此書雖存吉光片羽,卻在古代史學(xué)、中亞地理以及交通等方面頗具參考價(jià)值,同時(shí)有利于佛教僧傳的時(shí)代建構(gòu),故而值得我們考究。
釋智猛生年不詳。其生平相關(guān)資料,主要為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智猛法師傳》、慧皎《高僧傳》卷三《宋京兆釋智猛》以及唐釋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四附傳。檢讀這三種傳記文獻(xiàn),其內(nèi)容詳略不等。相較而言,僧祐經(jīng)錄智猛本傳時(shí)代最早,《高僧傳》智猛本傳有意刪略僧祐經(jīng)錄中的景色描繪,并且考證謹(jǐn)嚴(yán)、敘事精簡,《開元釋教錄》附傳則同時(shí)吸收僧祐、慧皎所撰之優(yōu)長,內(nèi)容翔實(shí),最為完備。據(jù)智升《開元釋教錄》,沙門釋智猛乃“京兆新豐人。稟性端明,厲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yè)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續(xù)晝。每見外國道人說釋迦遺跡,又聞方等眾經(jīng)布在西域,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為萬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姚秦弘始六年,甲辰之歲,招結(jié)同志十有五人,發(fā)跡長安”,“至涼州城”,“入于流沙”,“歷鄯鄯、龜茲、于闐諸國”,其后六人“始登蔥嶺,而同侶九人退還”,“至波淪國,同旅竺道嵩又復(fù)無常”,猛遂與余四人“三度雪山”,“至罽賓國,再渡辛頭河”,后至奇沙國、迦維羅衛(wèi)國、華氏城,“于是便反,以甲子歲發(fā)天竺,同行四僧于路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涼州”,“以宋元嘉末(453年)卒”。綜上,可見釋智猛為漢地沙門,他之所以誓死親往天竺巡禮,正是因?yàn)閷?duì)佛國心弛神往,試圖瞻仰佛跡,目睹真經(jīng)。智猛大體遵循前代行僧已經(jīng)實(shí)踐過的陸路求法路線,于404年從長安出發(fā),424年才開始回國,前后長達(dá)20余年,可謂備嘗艱苦。
據(jù)僧祐《出三藏記集》和慧皎《高僧傳》,智猛以元嘉十四年(437)入蜀。抑又,唐釋道宣《釋迦方志》記載:“東晉后秦姚興弘始年,京兆沙門釋智猛,與同志十五人,西自涼州鄯鄯諸國至罽賓,見五百羅漢問顯方俗。經(jīng)二十年至甲子歲,與伴一人還東,達(dá)涼入蜀,宋元嘉末卒成都。游西有傳,大有明據(jù),題云沙門智猛《游行外國傳》,曾于蜀部見之。”宋釋法云《翻譯名義集》亦云:“智猛,雍州人。稟性端厲,明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yè)專誠,志度宏邈,情深佛法,西尋靈跡。北涼永和年中,西還翻譯。”這里兩則材料,可與前述三種傳記文獻(xiàn)相互印證。而檢讀《高僧傳》卷十一《宋荊州長沙寺釋法期》,有蜀郡陴人釋法期“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yè),與靈期寺法林同共習(xí)觀。猛所諳知,皆已證得”,可見智猛歸國入蜀之后,在劉宋王朝的佛教界頗具聲名,培養(yǎng)了佛教人才,其高足亦即釋法期,后卒于荊州長沙寺。
明人胡應(yīng)麟指出,高僧智猛乃“釋之博于經(jīng)典,且富辯才者”。這里所謂博學(xué)善辯,實(shí)為大多數(shù)西行求法僧人的基本素養(yǎng)。不僅如此,釋智猛在回歸漢地之后,亦有赍經(jīng)翻譯之舉。據(jù)《出三藏記集》本傳,沙門智猛“后至華氏城,是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宗,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沙門法顯先于其家已得六卷《泥洹》。及見猛,問云:‘秦地有大乘學(xué)不?’答曰:‘悉大乘學(xué)。’羅閱驚嘆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就其家得《泥洹》胡本一部,又尋得《摩訶僧祇律》一部,及余經(jīng)胡本,誓愿流通”。《出三藏記集》《高僧傳》又記載智猛于涼州譯出《泥洹》本二十卷。《開元釋教錄》則言智猛于涼州“以虔承和年中譯出《泥洹》成二十卷”。考“虔承和”文義,疑為北涼沮渠牧犍(茂虔)年號(hào)“承和”,亦即437年,智昇經(jīng)錄可能因《出三藏記集》《高僧傳》云智猛“以元嘉十四年(437年)入蜀”而誤記。又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釋家類序:“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jīng)》及《僧祗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為二十卷。后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fù)赍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yàn),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為三十卷。”此說因?yàn)闀r(shí)間秩序紊亂,遂而引起學(xué)者質(zhì)疑。但無論如何,智猛于元嘉十四年(437年)之前,在北涼高昌譯出《泥洹》二十卷,則是學(xué)界不爭的事實(shí)。
因?yàn)槿绱耍瑫x唐佛教專科目錄大多著錄有智猛《泥洹經(jīng)》二十卷。《泥洹經(jīng)》或云《般泥洹經(jīng)》《大般泥洹經(jīng)》《涅槃經(jīng)》等。根據(jù)《出三藏記集》卷二,“宋文帝時(shí),沙門釋智猛游西域還,以元嘉中于西涼州譯出《泥洹經(jīng)》一部,至十四年赍還京都”,又云《般泥洹經(jīng)》“一經(jīng)七人異出”,其中“釋智猛出《泥洹經(jīng)》二十卷”,今闕。同書卷八《大湼槃經(jīng)記》則云:“此《大湼槃經(jīng)》,初十卷有五品。其梵本是東方道人智猛從天竺將來,暫憩高昌”,河西王“遣使高昌,取此梵本”,命天竺沙門曇無讖譯出。無獨(dú)有偶,隋費(fèi)長房《歷代三寶紀(jì)》卷九著錄《般泥洹經(jīng)》二十卷,亦云“宋文帝世,雍州沙門釋智猛,游歷西域?qū)ぴL異經(jīng),從天竺國赍梵本來,道經(jīng)玉門于涼州譯,元嘉十四年流至楊都,與法顯同見宋齊錄”。唐道宣《大唐內(nèi)典錄》卷四著錄《般泥洹經(jīng)》二十卷,其相關(guān)記載與長房錄相同。唐明佺《大周刊定眾經(jīng)目錄》卷二著錄《泥洹經(jīng)》二十卷,云“宋元嘉年中沙門智猛于西涼州譯,出竺慧宋齊錄”。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四著錄智猛《般泥洹經(jīng)》二十卷,云“見道慧宋齊錄及僧祐錄第六,譯與無讖《大般涅槃經(jīng)》等同本”。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二十四著錄《大般泥洹經(jīng)》二卷,云“北涼雍州沙門智猛于涼州譯”。令人遺憾的是,智猛所譯《泥洹經(jīng)》在南梁時(shí)已闕,唐代僅有記錄痕跡。
抑又,據(jù)前述《出三藏記集》智猛本傳,智猛曾于華氏城大智婆羅門家“尋得《摩訶僧祇律》一部,及余經(jīng)胡本,誓愿流通”。今檢讀《出三藏記集》,其中卷二《新集條解異出經(jīng)錄》亦著錄有《摩訶僧祇律》,云“一經(jīng)二人異出”,譯者分別為釋法顯、釋智猛。抑又,《歷代三寶紀(jì)》卷六還著錄《普曜經(jīng)》八卷,下注:“永嘉二年,于天水寺出,是第三譯,沙門康殊白,法巨等筆受,與蜀《普曜》及智猛、寶云所出六卷者小異,見聶道真及古錄。”可見,智猛除了翻譯《泥洹》二十卷之外,或譯有《摩訶僧祇律》《普曜經(jīng)》等,或僅為尋得兩經(jīng)梵本而已,因無其他證據(jù)可尋,卒難考究。
前述智猛回歸漢地之后,另撰有僧人行記《游行外國傳》。《游行外國傳》或曰《外國傳》《游外國傳》《智猛傳》。《隋書·經(jīng)籍志》以及宋歐陽修《新唐書·藝文志》、鄭樵《通志·藝文略》、明焦竑《國史經(jīng)籍志》等,均著錄智猛《游行外國傳》一卷;五代劉昫《舊唐書·經(jīng)籍志》則著錄智猛《外國傳》一卷;同屬史部地理類。此后公私書目罕有著錄。抑又,《出三藏記集》卷八引及智猛《游外國傳》《智猛傳》,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一附注、宋董逌撰《廣川畫跋》卷三、元馬端臨《文獻(xiàn)通考》卷三三六等,均提及智猛《外國傳》。唐徐堅(jiān)《初學(xué)記》卷二十七、明梅鼎祚《釋文紀(jì)》卷四十五、清張英等《御定淵鑒類函》卷三百六十二亦曾征引智猛《游外國傳》佚文。毋庸置疑,該書曾在中古時(shí)代別部自行并且傳播久遠(yuǎn)。
按前述《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智猛法師傳》,釋智猛“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七日于鐘山定林寺造傳”,則《游行外國傳》始作于439年。與此不同的是,清人秦榮光《補(bǔ)晉書藝文志》卷二、吳士鑒《補(bǔ)晉書經(jīng)籍志》卷二亦曾補(bǔ)錄《游行外國傳》。秦氏據(jù)《隋志》釋家類序云“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遂認(rèn)為“元熙,漢劉淵年號(hào)也,書當(dāng)作于西晉時(shí)”,顯然屬于判斷失誤。據(jù)筆者考察,唐前年號(hào)曰“元熙”者,既有前趙劉淵(304-305)時(shí)段,亦有晉恭帝司馬德文(419-420)時(shí)段,秦氏顯然將兩種年號(hào)混同,故而不足為據(jù)。
從歷代著錄情況看,智猛《游行外國傳》大致亡于宋后,其佚文亦不多見。清人儲(chǔ)大文《存研樓文集》卷八即指出:“僧智猛、法盛,遺聞盡闕。”盡管如此,《出三藏記集》智猛附傳,實(shí)以智猛行記為材料依據(jù)并經(jīng)刪改而成。附傳多處敘及智猛經(jīng)行路線以及異域風(fēng)光、釋迦遺跡、佛教見聞等,必為《游行外國傳》之應(yīng)有內(nèi)容。相關(guān)證據(jù)有:其一,《出三藏記集》附傳云:“既至罽賓城,恒有五百羅漢住此國中,而常往反阿耨達(dá)池。有大德羅漢見猛至止,歡喜贊嘆。猛諮問方土,為說四天下事,具在其傳。”這里所謂“具在其傳”,可見僧祐之簡略敘述,實(shí)據(jù)《游行外國傳》而縮寫。其二,《出三藏記集》卷八收錄《二十卷泥洹經(jīng)記》,云“出智猛《游外國傳》”,其內(nèi)容則是征引《智猛傳》云:“毗耶離國有大小乘學(xué)不同。帝利城次華氏邑有婆羅門,氏族甚多。其稟性敏悟,歸心大乘,博覽眾典,無不通達(dá)。家有銀塔,縱廣八尺,高三丈,四龕,銀像高三尺余。多有大乘經(jīng),種種供養(yǎng)。婆羅門問猛言:‘從何來?’答言:‘秦地來。’又問:‘秦地有大乘學(xué)否?’即答:‘皆大乘學(xué)。’其乃驚愕雅嘆云:‘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智猛即就其家得《泥洹》胡本,還于涼州,出得二十卷。”此《智猛傳》疑即《游行外國傳》,其具體文字內(nèi)容與《出三藏記集》附傳大致相同。蘇晉仁認(rèn)為,《出三藏記集》卷八“有《二十卷泥洹記》,即注出智猛《游外國傳》,其內(nèi)容與卷十五之傳所云相同,則二者均出于《游外國傳》”。蘇氏又在《出三藏記集》卷八《校勘記》中指出:“《法經(jīng)錄》六著錄《二十卷泥洹記》一卷,注云:見《智猛傳》”,“《梁傳》三《智猛傳》,記猛以元嘉‘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游歷。’即此傳,早佚。則此記為智猛所撰。”由此,檢讀僧祐所撰附傳,即可知《游行外國傳》之基本內(nèi)容。
抑又,《出三藏記集》附傳云智猛“歷鄯鄯、龜茲、于闐諸國,備觀風(fēng)俗”,而唐人徐堅(jiān)《初學(xué)記》卷二十七征引釋智孟《游外國傳》云:“龜茲國髙樓層閣,金銀雕飾”,清人張英等《御定淵鑒類函》卷三百六十二亦有征引。此條佚文,明顯源于智猛行記。
與晉唐其他僧人行記一樣,智猛《游行外國傳》明顯呈現(xiàn)出了多學(xué)科交叉研究的獨(dú)特價(jià)值。檢讀《出三藏記集》智猛附傳,其學(xué)術(shù)價(jià)值首先表現(xiàn)為《游行外國傳》與其他僧人行記和西域文獻(xiàn)的相互參證之用。譬如,附傳云智猛“復(fù)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惟羅衛(wèi)國,見佛發(fā)、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跡,炳然具在”;而楊衒之《洛陽伽藍(lán)記》引《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發(fā),并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yǎng)。至瞿波羅窟,見佛影。入山窟,去十五步,西面向戶遙望,則眾相炳然;近看則瞑然不見。以手摩之,唯有石壁,漸漸卻行,始見其相。容顏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有方石,石上有佛跡。”又如,附傳云智猛先于奇沙國見“佛缽,光色紫紺,四邊燦然”;而東晉支僧載《外國事》云:“佛缽在大月氏國,一名佛律婆越國,是天子之都也,起浮圖。浮圖高四丈,七層,四壁里有金銀佛像,像悉如人高。缽處中央,在第二層上,作金絡(luò),絡(luò)缽錬懸缽,缽是石也,其色青。”諸如此類,因?yàn)閮煞N文獻(xiàn)及其撰者時(shí)代各異,文本內(nèi)容亦不盡相同,從而有助于學(xué)者研究古代印度歷史和佛教文化傳播情況。毋庸置疑,《游行外國傳》正是與諸種西域相關(guān)文獻(xiàn)緊密關(guān)聯(lián),才能彰顯出其學(xué)術(shù)意義。向達(dá)指出:“智猛歷游西域諸國,途經(jīng)龜茲時(shí)距呂光之伐西域尚未三十年”,龜茲宮室猶得面見,故曰“龜茲國髙樓層閣,金銀雕飾”,“頗足以證《晉書》之言。惜乎全書不傳,現(xiàn)存者亦只寥寥數(shù)條,否則其可以補(bǔ)正西域史地者當(dāng)不尠也。”要之,智猛《游行外國傳》有助于促進(jìn)以西域和佛教為主題的中古學(xué)術(shù)研究。
如果說,《游行外國傳》給后世學(xué)者考察古代西域和佛教留下了重要線索;那么,該著還因?yàn)殛P(guān)注經(jīng)行路線和山川地理,敘述簡略而且清晰有序,足見其使用史傳文學(xué)的寫作手法非但較為明顯,可謂自成體系。史傳或注重時(shí)間,或注重人物,或注重事件。圍繞著智猛在佛國巡禮求經(jīng),《游行外國傳》之主體部分,往往以地理距離來取代時(shí)間的延續(xù),在時(shí)間的推移中,間以描寫自然、風(fēng)情、佛跡等,如此充分發(fā)揚(yáng)了史傳文學(xué)的書寫模式,形成了較為獨(dú)特的行記風(fēng)格。
依據(jù)僧祐《出三藏記集》智猛附傳和后世類書征引佚文,可見《游行外國傳》應(yīng)與同時(shí)代前后大多數(shù)佛教行記的文本風(fēng)格類似。檢讀智猛附傳,書中描寫流沙則云:“西出陽關(guān),入流沙,二千余里,地?zé)o水草,路絕行人。冬則嚴(yán)厲,夏則瘴熱。人死,聚骨以標(biāo)行路。驝駞負(fù)糧,理極辛阻”;描寫雪山則云:“冰崖皓然,百千余仞,飛緪為橋,乘虛而過,窺不見底,仰不見天,寒氣慘酷,影戰(zhàn)魂慄。漢之張騫、甘英所不至也”,足見其寫景狀物,簡練傳神,與法顯、玄奘之佛教行記異曲同工,如此證實(shí)西行求法著實(shí)不易。不僅如此,附傳又云:“猛先于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于此國見佛缽,光色紫紺,四際盡然。猛香華供養(yǎng),頂戴發(fā)愿:‘缽若有應(yīng),能輕能重。’既而轉(zhuǎn)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shí),復(fù)不覺重”,足見原書亦善于講述佛跡感應(yīng),語言干凈,文筆老到,往往婉轉(zhuǎn)有致。此外,智猛附傳普遍使用表示承接的關(guān)聯(lián)詞,文中亦謂“(猛)又游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shù)”,“猛誠心冥徹,履險(xiǎn)能濟(jì)”等等,可見《游行外國傳》對(duì)求法路線的有序記錄,對(duì)佛國遺跡和風(fēng)物的描述,對(duì)人物接遇、現(xiàn)世靈驗(yàn)以及古代傳說的敘述,一方面應(yīng)為六朝綜合性僧傳的撰寫提供了文本基礎(chǔ),最終促進(jìn)了這個(gè)時(shí)代僧傳文學(xué)的建構(gòu);另一方面應(yīng)與六朝其他佛教行記諸如支僧載《外國事》、竺法維《佛國記》、釋法盛《歷國傳》以及記載慧生等人西行求法的《慧生行傳》《宋云家記》《道榮傳》等著作一道,為唐朝佛教行記的時(shí)代演繹提供了敘事摹本。唐朝佛教行記正是一方面吸收前賦創(chuàng)作傳統(tǒng),“另一方面憑借其文獻(xiàn)形態(tài)之彌繁、寫作意圖之迎合、生活廣度之拓展、文學(xué)手段之更新等進(jìn)行綜合演繹”,借此“表現(xiàn)出了某種時(shí)代趨向和功能強(qiáng)化,并且昭示出較為顯著的文學(xué)意義”。
要之,釋智猛親歷佛國求經(jīng)巡禮,譯有《泥洹經(jīng)》二十卷等,撰有行記《游行外國傳》,由此表現(xiàn)出一代高僧為弘揚(yáng)佛教所做出的犧牲和努力。慧皎《高僧傳》卷三論曰:“竊惟正法淵廣,數(shù)盈八億,傳譯所得,卷止千余。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絕,或望煙渡險(xiǎn),或附杙前身,及相會(huì)推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法顯、智猛、智嚴(yán)、法勇等,發(fā)趾則結(jié)旅成群,還至則顧影唯一,實(shí)足傷哉。當(dāng)知一經(jīng)達(dá)此,豈非更賜壽命,而頃世學(xué)徒,唯慕鑚求一典,謂言廣讀多惑,斯蓋墮學(xué)之辭,匪曰通方之訓(xùn)。”事實(shí)上,晉唐高僧正是以一種類似屈子“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精神求經(jīng)說法,為佛教在我國的順利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xiàn)。誠然,中世古書題如《外國傳》者甚多,除正史著作專門設(shè)有“外國傳”,尚有釋曇景《外國傳》、曇無竭《外國傳》等僧人行記,以及《吳時(shí)外國傳》《交州以南外國傳》《大隋翻經(jīng)婆羅門法師外國傳》等同名異實(shí)之文獻(xiàn)多種。釋智猛《游行外國傳》與其他諸種僧人行記類似,一方面印證了中古時(shí)代佛教文化發(fā)展的盛況,另一方面亦表明西域和南海相關(guān)研究文獻(xiàn)亟待鉤沉,其學(xué)術(shù)價(jià)值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