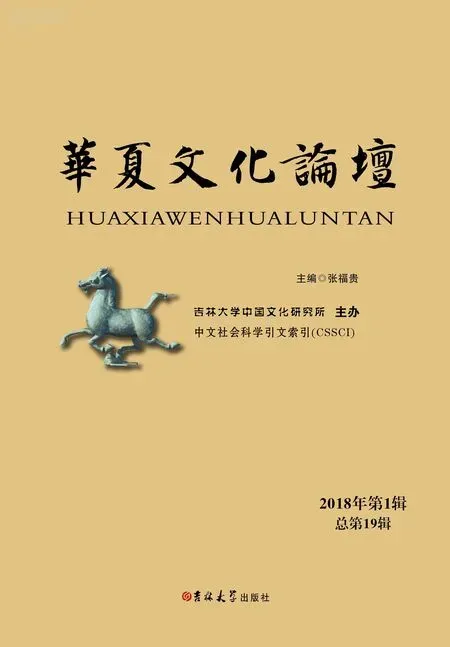進化論與中日近現(xiàn)代的新小說
楊文昌 蘇芊芊
【內(nèi)容提要】進化論對近現(xiàn)代中日兩國小說文體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小說觀念的更新上。中日近現(xiàn)代的啟蒙主義文學(xué)家都在用進化論為小說正名,并對小說作為一種文體的特性進行了近代意義上的規(guī)約,由此,使得傳統(tǒng)意義上的小說變成了適應(yīng)新的時代要求的尊貴、獨立的新小說。這既是歷史進化觀念下對小說歷史使命的重新定位,也是社會有機體論中的個性意識所帶來的小說文體意識的覺醒。
進化文學(xué)觀之下的文學(xué)是隨著歷史前進的步伐而不斷發(fā)展變化的,這種認(rèn)識是在歷史進化觀念下把文學(xué)置于時間的維度中進行考察的理論歸趨,因此,歷史范疇中的新與舊便自然地被移植到文學(xué)中來,于是,“新文學(xué)”觀就成了中日近現(xiàn)代文學(xué)的首要理論問題。
“新文學(xué)”觀中的“新”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首先,新文學(xué)應(yīng)該是獨立的。文學(xué)要進化,就必須擺脫對一切外在之政治、思想的依附,從“文以載道”的舊模式中徹底解放出來,取得文學(xué)應(yīng)有之位置和尊嚴(yán)。這也是對文學(xué)與人的關(guān)系的重新定位,是對“一般社會對于文學(xué)者身分的誤認(rèn)”的校正。“‘裝飾品’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文學(xué)者現(xiàn)在是站在文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分子;文學(xué)作品不是消遣品了;是勾通人類感情代全人類呼吁的唯一工具,從此,世界上不同色的人種可以融化可以調(diào)和。”這方面,雖然坪內(nèi)逍遙表現(xiàn)出了義無反顧的姿態(tài),但因為其本質(zhì)上是改良主義的,所以他概括的近代小說的四大裨益中,既有可以導(dǎo)向啟蒙的“提高人的品格”,又有指向道德說教的“勸獎懲戒”;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先覺者的態(tài)度雖然不如坪內(nèi)那般決然,但因其思想精神是激進民主主義的,故而在啟蒙的文學(xué)道路上并未表現(xiàn)出對舊勢力的真正妥協(xié)。其次,新文學(xué)應(yīng)該是在言文一致的語言背景下的白話文學(xué)。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言文不一致嚴(yán)重限制了文體的選擇,文言已無法表現(xiàn)復(fù)雜多樣的社會現(xiàn)實內(nèi)容,已構(gòu)成文學(xué)表達(dá)的桎梏。第三,新文學(xué)應(yīng)該是關(guān)注現(xiàn)世生活的。根據(jù)進化的文學(xué)觀的推理,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xué),現(xiàn)世的現(xiàn)實生活即是文學(xué)內(nèi)容的根源或表現(xiàn)對象,因而文學(xué)與現(xiàn)世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很好地表現(xiàn)現(xiàn)實生活的文學(xué)才能進化。人是社會生活的主體,所以,新文學(xué)應(yīng)該是“人的文學(xué)”,是以存在于群體中的個體的人為對象的,而不是為政治及倫理道德等服務(wù)的。
近現(xiàn)代的中日兩國,通過對西方進化論的改造與吸納并進而用于文體變革之中,不僅實現(xiàn)了文學(xué)語言的近代轉(zhuǎn)變,同時也大大促進了兩國國語的統(tǒng)一與定型。小說作為文體的一種,在中日兩國歷來是以茶余閑資甚至是奇技淫巧的面目出現(xiàn)的,同樣是因為借重了進化論的力量,兩國的小說都在各自的發(fā)展歷程中實現(xiàn)了質(zhì)的飛躍。可以說,白話文體和小說體裁的興起,代表了兩國近現(xiàn)代文學(xué)文體演進的突出成就,也是進化論對近現(xiàn)代中日兩國文體演進影響最顯著的方面。
進化論對近現(xiàn)代中日兩國小說文體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小說觀念的更新上。這種更新,既表現(xiàn)在處于同一社會整體中的作者及讀者的文學(xué)思想中,也表現(xiàn)在當(dāng)時社會的文化意識中;既包含著小說文體主體性的確立過程,也包含著小說文體意義空間的近代轉(zhuǎn)型。眾所周知,“小說”一詞最早見于《莊子》,但與目下小說概念的內(nèi)涵、外延及所涵蓋的文體意義相去甚遠(yuǎn)。真正對現(xiàn)代小說產(chǎn)生影響的言論來自歷史學(xué)家班固,他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的一段話,壓制了小說文體幾乎兩千年:“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yuǎn)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此文中“小說”的概念是很寬泛的,后世的“小說”概念也各有其時代性,但是,小說“淺薄”“鄙陋”的品性以及作為小道旁枝、奇技淫巧的面目還有作為底層文體的定位,無不是從班固而來。當(dāng)然,班固的言論不是孤立的一己之見,它代表的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聲音。兩千年來的中國文學(xué)進程中,也曾出現(xiàn)過反對正統(tǒng)觀念的聲音,而真正具有顛覆之功的應(yīng)首推嚴(yán)復(fù)。可以說,其與夏曾佑合作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對中國小說文體的近代轉(zhuǎn)型具有規(guī)范性價值和指導(dǎo)性意義。從其后梁啟超倡導(dǎo)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到五四文學(xué)先驅(qū)發(fā)動的“文學(xué)革命”,從這些運動的理論主張,到其中邏輯論證的思維特征,都能發(fā)現(xiàn)嚴(yán)復(fù)思想的深刻印記。該文中,嚴(yán)、夏二人從進化論出發(fā),對小說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二人認(rèn)為,書籍對于傳承或者說一個民族的延續(xù)是至關(guān)重要的,而其中的記事之書“為甲”。記事類書籍之所以能發(fā)揮第一等的作用,就是因為其易傳性。他們總結(jié)了記事之書易傳的五大優(yōu)點:第一,“書中所用之語言文字,必為此種人所行用,則其書易傳。其語言文字為此族人所不行者,則其書不傳。”第二,“故書傳之界之大小,即以其與口說之語言相去之遠(yuǎn)近為比例。”第三,“繁法之語言易傳,簡法之語言難傳。”第四,“言日習(xí)之事者易傳,而言不習(xí)之事者不易傳。”第五,“故書之言實事者不易傳,而書之言虛事者易傳。”二人由此得出結(jié)論,國史不易傳,小說易傳,所以,“夫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yuǎn),幾幾出于經(jīng)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風(fēng)俗,遂不免為說部之所持。”于是,小說乃至文學(xué)就成了種族延續(xù)以及社會文明進步的依托:“文章事實,萬有不同,不能預(yù)擬;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則在乎使民開化。”如果說這還只是對小說與社會文明進步相始終的地位的理論論證的話,歐美以及日本的開化歷史則為他們提供了有力的例證:“且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所以,二人“不憚辛勤,廣為采輯,附紙分送。或譯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他們把小說看作優(yōu)勢文體,而這種“優(yōu)勢”又是歷史進化的結(jié)果和民族進步的必要前提。二人甚至由此把小說的地位置于正史之上:“抑又聞之: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構(gòu)之史,而今日人心之營構(gòu),即為他日人身之所作。則小說者又為正史之根矣。若因其虛而薄之,則古之號為經(jīng)史者,豈盡實哉!豈盡實哉!”從以上分析可見,這篇文章不僅涉及小說地位的問題,同時也關(guān)涉到文學(xué)內(nèi)部規(guī)律問題以及對中國文學(xué)近代轉(zhuǎn)型的預(yù)期。既然文學(xué)及文學(xué)實踐是文明開化的必由之路,那么,在當(dāng)時的民族生存困境中,文字的通用性問題,書寫語言的口語化問題,文學(xué)語言的繁簡即具體與概括、形象與抽象問題,文學(xué)題材的大眾化問題,文學(xué)寫作中的主客觀關(guān)系問題,翻譯與創(chuàng)作的問題等,都是必須盡快解決的問題。嚴(yán)、夏二人在《本館附印說部緣起》中雖然對此沒有具體的闡述與論證,但其中有關(guān)小說、文學(xué)的論斷或體會,對后繼者有著強烈的或明指或暗示的作用。“由《春秋》以致小說,又不可謂之非文體一進化”“使孔子生于今日,吾知其必不作《春秋》,必作一最良之小說,以鞭辟人類也。”所以,“小說,小說,誠文學(xué)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吾以為吾濟今日,不欲救國也則已,今日誠欲救國,不可不自小說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說始。”于是,“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這里,小說的地位已經(jīng)遠(yuǎn)出于經(jīng)史之上。由此,嚴(yán)、夏二人以社會有機體論為小說張目的思路已經(jīng)完全清晰,小說從此也由娛樂、游戲之低俗走向思想啟蒙之尊貴以致崇高。如果說此時梁啟超等人的文學(xué)主張忽視了先前嚴(yán)、夏二人對文學(xué)主體性及內(nèi)部規(guī)律的謹(jǐn)慎態(tài)度,從而導(dǎo)致文學(xué)主體性被政治使命所綁架的話,那么,五四文學(xué)先驅(qū)對“游戲文學(xué)觀”及“載道文學(xué)觀”的批判,則糾正了這一偏向,其主張傾向基本回轉(zhuǎn)到嚴(yán)、夏之較為冷靜、理性的思路,逐漸將新小說的發(fā)展引向既自尊又獨立的方向。新文學(xué)的締造者之中,連作為政治家的文學(xué)論者陳獨秀都認(rèn)識到“文學(xué)為手段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所以,文學(xué)“自身獨立存在之價值,是否可以輕輕抹殺,豈無研究之余地”?這也是以社會有機體論為依據(jù)的進化文學(xué)觀對文學(xué)及小說作為個體存在的主體性的確認(rèn)。盡管五四新文學(xué)最終還是承載了思想啟蒙的社會使命,甚至還潛存著走向為政治革命服務(wù)的傾向,但文學(xué)的主體性存在確已成為五四文學(xué)意識的構(gòu)成要素之一。
從現(xiàn)有史料來看,在日本,最早使用“小說”一詞的是西周。他在介紹西洋文藝的《百學(xué)連環(huán)》一書中,分別提到了 “稗史”和“小說”,但和我們今天的看法卻有很大的不同。以后則很長時間看不到“小說”一詞的出現(xiàn),盡管當(dāng)時翻譯的西方小說很多,卻代之以“情史”“奇談”“情譜”“人情話”等名稱。政治小說興盛時期,“稗史”和“小說”之名目問題漸受重視,從而出現(xiàn)了為小說正名的歷史契機,最后終于在坪內(nèi)逍遙那里有了定論。小說是日本近代文學(xué)的主流文體,從這個意義上說,坪內(nèi)逍遙確實堪稱開日本近代文學(xué)先河的一代宗師。當(dāng)然,坪內(nèi)逍遙的貢獻主要還在其小說理論的創(chuàng)設(shè)上,尤為重要的是,在他發(fā)現(xiàn)“小說”這一概念的同時,也發(fā)現(xiàn)了“小說”這一文體,“是他,最早提出了‘真’為唯一的文學(xué)理念,與封建主義的‘善’(封建主義的文學(xué)功利觀)相對抗,為日本文學(xué)的近代化開辟了道路。”成為日本小說近代轉(zhuǎn)型的引路人。
由于受儒家文化及漢文學(xué)的影響,日本文學(xué)傳統(tǒng)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尊詩文而輕小說的觀念;到了近世,“文以載道”觀大行其道,“道也者文之本也,文也者道之末也。末者小而本者大也。”當(dāng)這種文學(xué)觀借助小說的通俗性和娛樂性來實現(xiàn)時,就形成了日本近世“戲作”文學(xué)中的勸懲小說。從近代意義而言,這幾乎是將小說文體托下了深淵。從而,深受儒學(xué)影響的明治啟蒙思想家們當(dāng)然要把小說列為有害的文體,拒絕用小說作為啟蒙的工具。其后,雖然民權(quán)派政治小說的出現(xiàn),一定程度上對江戶戲作文學(xué)觀構(gòu)成了沖擊,但此時的小說文體又被現(xiàn)實的功利主義宣傳所左右。所以,此時的小說成了有用的文體,而不是被人尊重的文體。正如坪內(nèi)逍遙所說,“我國習(xí)俗,自古以來,將小說看作是玩物,作者也滿足于此,無人敢于想去改良小說,使之成為娛悅大人、學(xué)士們的藝術(shù)。”“而將小說視為婦女童蒙的玩物,這種錯誤的看法皆出于不承認(rèn)小說為藝術(shù)。”坪內(nèi)逍遙從進化論出發(fā),向世人揭示出小說的應(yīng)有地位及近代價值,徹底扭轉(zhuǎn)了小說在近代日本文學(xué)中的不利地位。“Novel即地道的小說在世上出現(xiàn),總是在戲劇趨于衰微的時期。”推其原因,“這是因為在文明尚淺近、蒙昧未開的社會,”“由于這個時期的人情世態(tài)都顯露在外,所以刻畫這類人物并不困難,”“但是隨著文明氣運的進展,每個人、每件事的懸殊性質(zhì)已越來越少,只用所謂‘思入’這類表演方式,有許多是難以表現(xiàn)出來的。這也是為什么戲劇逐漸讓位于稗史、小說的緣故。”通過對日本小說變遷史的梳理以及同戲劇等文體的比較,他認(rèn)為小說隨著文明的進步,自然而然地在社會上盛行起來,并受到重視,是“優(yōu)勝劣敗,自然淘汰的規(guī)律所使然,時代所趨,無法抗拒的”。這是從歷史進化的角度對小說的發(fā)達(dá)及其在近代文學(xué)中的重要地位的學(xué)理性論證,賦予了小說以時代的尊嚴(yán)。在闡述小說的裨益時,他認(rèn)為小說的直接利益,“在于娛悅?cè)藗兊摹男摹敲础男摹质鞘裁茨兀坎煌饩褪敲烂畹那榫w。”“更何況約翰·穆雷先生也曾說過,對人間世界的批判,乃人生一大樂事。”“有識之士讀了它,其感受之深,遠(yuǎn)非讀其他經(jīng)書或讀正史所可比擬。”這里,他把小說的目的與人類的美妙情感直接關(guān)聯(lián)起來,并把小說直接的社會批評作用置于經(jīng)書、正史之上;同時他還把“使人的品味趨于高尚”列為小說間接裨益的首位:“小說這種東西,它所致力的,并不是給人以官能的享樂,而是致力于投合人們風(fēng)雅的嗜好,給人以娛樂。而風(fēng)雅的嗜好,美妙的情感,是一種最高尚的情緒活動。如果不是文化發(fā)達(dá),具有高的文明的民族,是絕不可能具有這種情緒的。”總之,在坪內(nèi)逍遙看來,小說具有促進文明發(fā)達(dá)的妙機妙用,小說的發(fā)達(dá)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文明時代之所需,從而有力反駁了小說無用論及游戲文學(xué)觀,為小說爭得了在近代日本文學(xué)中應(yīng)有的位置;另一方面,因為其所謂“妙機妙用”是以“真”為基礎(chǔ)和前提的,所以,他提倡局外人式的純客觀的小說創(chuàng)作原則,主張如實模寫,將“載道”觀念拒之于文學(xué)的大門之外,這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日本小說主體性的一次徹底解放。
從上面的梳理可見,中日近現(xiàn)代的啟蒙主義文學(xué)家都在用進化論為小說正名,并對小說作為一種文體的特性進行了近代意義上的規(guī)約,由此,使得傳統(tǒng)意義上的小說變成了適應(yīng)新的時代要求的尊貴、獨立的新小說。這既是歷史進化觀念下對小說歷史使命的重新定位,也是社會有機體論中的個性意識所帶來的小說文體意識的覺醒。但是,近代中日兩國本土化的進化論中的“個體”觀念是有差異的。加藤弘之的社會有機體論在日本影響最為深遠(yuǎn),其中的個體觀念是以“唯一利己的根本動向”為核心的。這種動向可以附著于國家或民族作為個體的存在之中,從而導(dǎo)致國家主義或民族霸權(quán)主義;也可以附著于個人作為個體的存在之中,從而形成近乎極端的個性意識乃至極端利己主義。當(dāng)然,如果把文學(xué)視為一種個體性的存在,則很有可能對文學(xué)的獨立性意識和主體性意識產(chǎn)生極端性的影響。從《小說神髓》盡力排除一切作者主觀因素干擾的創(chuàng)作原則看,坪內(nèi)逍遙小說理論的文學(xué)主體性意識,應(yīng)當(dāng)也附著了這種“唯一利己的根本動向”。而在近代中國的社會有機體論中,既強調(diào)個體的進化本位作用,同時又強調(diào)群體的進化實現(xiàn)功能,個體與群體始終處于一種緊張的對立統(tǒng)一關(guān)系之中,個性意識的伸張程度是以國家或民族的歷史使命為底線的。所以,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xué)中的個體觀念中總能發(fā)現(xiàn)群體的影子,文學(xué)的主體性訴求似乎也不像近代日本文學(xué)那樣強烈和執(zhí)著,在作者的主觀能動性與作品的客觀存在之間,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比日本近代文學(xué)更強調(diào)前者。當(dāng)然,進化論的影響并不是絕對的,也不能說是唯一的因素,其實,從兩國近代的文學(xué)史中也可以發(fā)現(xiàn)影響近代文學(xué)個體意識的傳統(tǒng)因素。據(jù)葉渭渠先生的觀點:“‘真實’與‘物哀’兩種思潮作為日本古代文學(xué)的主潮,不僅顯示了日本古代文學(xué)思想的完成,而且‘真實’文學(xué)思潮成為‘物哀’‘幽玄’‘閑寂’諸文學(xué)思潮的基底,推進了一個時代文學(xué)的發(fā)展。”日本古代文學(xué)的“真實”精神雖然主要體現(xiàn)于主流文學(xué)之中,但肯定會在精神層面對坪內(nèi)逍遙的小說理論有一定的影響,同時在追求“真”或“客觀”的技巧上,坪內(nèi)逍遙更多地借助了心理學(xué)等近代科學(xué)成果。相比之下,中國古代文學(xué)傳統(tǒng)則更注重作者的入世態(tài)度甚至“經(jīng)世致用”的目的意識,“載道”也好,“言志”也罷,其中的“載”和“言”都可能意味著作者主觀對文學(xué)主體性的主動干預(yù)以致支配,這一文學(xué)傳統(tǒng)對于由非主流文學(xué)近代化為主流文學(xué)的小說文體自然會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