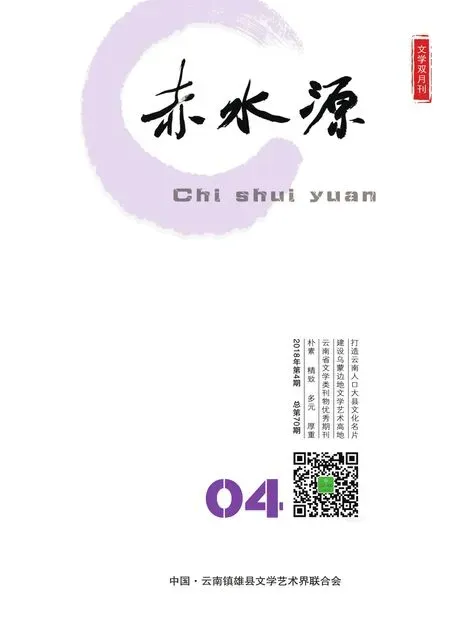溫水記憶,鄉紳的背影
散文 汪舒
作為白水江的上游,溫水的水一開始就不平靜。千回百轉之后,峭壁林立中,滿山桑果容易在不經意之間吐露出另一種農業的臉龐。然而在很多年前,這個地方的人并沒有在咆哮的江水聲中妥協下來,而是在一個鄉紳的帶領下,用石頭刻畫命運的硬度,用堅韌的毅力和生命為后人留下福祉。
國泰石橋
七十年前,鎮雄羅坎境內溫水王國泰與數十位鄉鄰沿以者河而上,用竹筏將修建橋梁的石頭運往橋梁選址地兩合巖,那里聚集了滇川接合部一帶的能工巧匠,這座即將修建起來的橋梁,給方圓百里之內的農戶、商戶及地方政府太多的期望。這座后來被命名為“國泰橋”的石拱橋,在歷史風云和時光年輪里,逐漸失去了原有的光彩,直到今天,“國泰橋”連接起來的兩岸懸崖峭壁間的山路,已經荊棘遍布。
“國泰橋”不遠處,最多三公里之外的地方,鳳鎮二級公路上車來車往,這個角落在過去的時光里,已經被遺忘。
按傳統紀年年號,王國泰生于光緒九年(1883年),在“國泰橋”一端峭壁的灌木林里,斑駁的石碑上,字跡已經模糊。可以推測的是,碑上記錄的是修橋的一些簡單信息,可惜只能依稀辨認出上面排列出的是人名,碑文的最后字體變大而清晰起來:“大中華民國三十六年歲次丁亥二月是日”。
王國泰為修橋費盡心機,甚至搭上性命,“修橋”這個強烈的愿望始于何時,溫水一帶的王氏家族后人不得而知,在后來兩代人的耳口相授中,侄孫王效忠勾勒出一個遠房祖父的形象:二老爺王國泰被鄉鄰稱為王二善人,每天早上起床,王二善人先穿上新衣服,把舊衣服套在外面,喝二兩酒后,在陽光下走到地里看看莊稼長勢,偶爾看見有人偷地里的包谷,他不露聲色悄悄走開,過了幾天,假裝若無其事的樣子和偷包谷的人拉家常,問是不是沒有吃的,不等對方解釋,他迅速將藏在新舊衣服之間的糧食遞過去,“先救急吧”。
簡樸的生活,讓王二善人在溫水一帶置有數百畝土地,部分鄉鄰和四川逃荒的人成為他的雇農。他吃飯從不會與雇農分開,過年殺豬,要邀請所有雇農一起吃飯,不能到的,也要割一塊豬肉送去。不僅于人,冬天大雪封山,鳥雀無處覓食,他都會把糧食放在樹上,任由那些饑餓的鳥類叼啄。
修橋需要足夠的財力、物力、人力,王國泰年輕力壯的日子里,他似乎在為修橋蓄勢,所有的準備似乎都是為修橋而來。以至于多年以后,除了“國泰橋”,他還修建了“鹽溪橋”和當地周姓人家共同出資修建了“軍備橋”。
王國泰最終還是沒有看到橋梁完工,沒有看到這塊石碑,甚至更沒有設想到這座橋竟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連續多年的操勞、風雨中的奔波,“國泰橋”臨近完工,王國泰的腳被石頭砸傷,鄉鄰們將他抬到家里,因傷口感染不治而亡。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64歲的王國泰遺憾地閉上了雙眼,他的身后是一座未完的橋梁。鄉鄰悲愴,嘆其早逝,便齊心修橋,刻碑紀念,命橋名為國泰。
溫水之水
“國泰橋”所在地當地村民稱之為兩合巖,在今天的鹽源鎮溫水村境內。上世紀1984年、1988年以及2012年,行政區劃幾經變革,鹽源名稱經歷了區、鄉、鎮等稱謂,如果時間再往上追溯,從毗鄰的羅坎鎮劃分出來的鹽源鎮,到今天仍然是鎮雄、威信兩縣進入昭通到達昆明、進入宜賓到達成都及重慶的要隘。只是幾年來陸路交通發達,削弱了一個小地方與長江經濟帶潛在的聯系。
地理結構上的解讀,從四川盆地向云貴高原抬升過渡帶的今羅坎、鹽源,由于水流劇烈的下切作用,形成山峰林立、溝壑縱橫的地表特征,當地居民分散生活在海拔高差1000米左右的深山峽谷間。這里是川滇兩省商賈來往頻繁之地,川滇文化的交流,孕育了較為豐厚的人文。“雙流幾曲浴丹蒼,冠翅居然鳳欲翔。莫漫吹笙明月夜,便教飛去白云鄉。”鎮雄縣志里記載,今羅坎鎮鳳翥村清代舉人王廷桂曾賦詩,描繪出一幅田園風情、人文歷史畫面。
站在當下回望歷史,總是會找到一些有趣的東西。一個地方的記憶,一方面來自史料記載,一方面來自不變的風景。溫水村境內肆意流淌的以者河、馬過河與羅坎鎮鳳翥白水江、小溪河相遇經橫江匯入長江,河流的走向,給當地找到文明的寄托和對未來發展無限的遐想。
2018年4月19日,鹽源鎮溫水村舉辦第二屆蠶桑采摘節,主辦方意在通過農事活動促進產業發展和帶動鄉村旅游,最終達到鄉村復興的目的。早上從昭通市昭陽區出發,三個小時車程,溫水到了,鹽源鎮黨委書記汪繼金說,下午的時間,你們隨意看看,鹽源會給你們留下什么印象。這給前來采訪蠶桑采摘節的媒體記者一個意外,同時也激發出職業好奇。遺憾的是,剛出發不久,一場大雨悄然降落,等到雨過天晴,已經是下午時分,最后選擇向溫水村出發。
雨后清新的空氣來自茂密的深林,也許來自奔流的溪水,呼吸的享受還未盡興,一道彩虹突然間出現在眼前,那一瞬間呈現出來的曼妙色彩竟然讓所有人大呼一聲“你看”之后,都屏住了呼吸,想起要拿相機時,橫跨在兩座高山之間的彩虹已經于迷幻中慢慢消失。同行的人說,彩虹下面是以者河,我們所在的位置看不見。那一刻,我知道,鹽源鎮的山水給我們的也許是十分之一的側面,以至于第二天汪繼金倡議考察以者河時,所有人改變采訪完采摘節活動就回單位的原計劃,走到一個鎮黨委書記埋下的“伏筆”里。
4月20日中午,本想在以者河與白水江交匯的兩河口處,靠竹筏擺渡進入以者河上游,這條河流經過鹽源境內的木歪、杉樹坪、鐵爐、付家寨、倉海、溫水等地,但竹筏陳舊加之枯水季節,這一愿望并未實現,最后選擇沿著懸崖峭壁間的一道山路,走到“國泰橋”,然后返回乘車對鹽源鎮作了一個環線考察。
上世紀40年代或者更早時候,竹筏穿行在夾在懸崖峭壁間的以者河,除了渡人,還運送上游生產出來的鹽礦。從巖縫中流出的泉水,含有豐富的鹽礦,作為一種當時稀缺的資源,它吸引了滇川接合部一帶的淘鹽者蜂擁而至,在鼎盛時期,來取鹽水的人每日有數百人之多,一些頭腦精明的商人還制作了沉鹽裝置,對鹽水進行過濾加工,將固態的鹽運往外地。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鹽源這一地名固定下來,因鹽泉所在村落鹽水溫度高,溫水一名迄今沿用。
發現于清代的鹽水之源如今已成為遺址,而在其兩三公里范圍的倉海景點月窟禪光及鐵爐的古老民居,將成為鹽源鎮鄉村旅游開發的引爆點。但是,這需要吸引企業參與,也需要回流鄉村人才,對于鹽源鎮政府而言,養在深閨的人文自然風景在等待發現它的伯樂。
紅色基因
鹽源考察隨行的有溫水村民王效忠。走向國泰橋時,他走在前面,撥開雜草與帶刺的灌木,辨認著這一條久無人跡的路,半個小時左右,到達懸崖間在巖石上開鑿出來的路,雖然驚險卻豁然開朗。在路途斷斷續續的講述中,王效忠揭開了王國泰的一段往事,這一段往事的另外一個主人公名叫王應崧。
“二祖父樂善好施,紅軍經過羅坎,知道王區長支持紅軍,悄悄送給王區長家錢糧”。
鎮雄縣志里記載,清雍正七年到宣統一年,羅坎屬上北迎恩里;民國二年屬上北區團;民國二十三年設為第六區,王應崧為第六區區長。王效忠講述的王區長就是王應崧。
可查詢的資料顯示:1935年4月,鎮雄縣第一位共產黨員周一戎按瀘縣中心縣委布置回鄉隱蔽。當年6月,特委委員、瀘縣中心縣委書記鄒風平被敵追捕越城,身負重傷,化名周子和帶著地下黨員侯建成到羅坎隱蔽養傷,在周一戎和時任國民黨羅坎區區長王應崧等人的協助下,在王家祠堂開辦“錦莊小學”,以教書為掩護,開展地下黨活動。1937年3月,駐羅坎圍剿縱隊的滇軍二旅楊連準備逮捕鄒風平和王應崧,周一戎聞訊后,冒著生命危險將鄒風平送出鎮雄。王應崧因此被捕,后經多方周旋,方得釋放。
在公開出版的王杰、王點主編的《歷史的真實與真相:王應崧與中共鎮雄羅坎地下黨(1935年—1950年)》一書里,找不到王國泰、王應崧之間交集的文字敘述。關于王應崧,其后人王樵的紀念文章里,有較為詳細的敘述。
王應崧畢業于清末改建的鎮雄高等小學堂,1922年,他開始在家鄉辦理羅關國民小學,先任教,后任校長。隨著學生的增加,后來還參建了攔馬墳小學校舍一棟。1942年,王應崧又帶領族人將石頭溝修建的王氏宗祠改為石谷小學。1934年,王應崧始任鎮雄第六區區長,1936年聽從王樵勸說賦閑家居。1940年,臨時任過約有半年的茶蔚鄉長,以后就再沒有任過地方公職。
王應崧在地方任職期間,建學校、修道路、勸種桐漆桑麻,盡力倡導籌謀,從清寒教師到地方官員在到普通百姓的人生旅途中,始終不忘從教育、經濟、交通等方面發展一個地方。
2015年,曾經的“錦莊小學”被確定為“中共黨史教育基地”;2017年,“錦莊小學”修繕結束,作為紅色教育基地,它在以后的時間里迎送著一撥撥瞻仰者。
而偏于一隅的“國泰橋”,在鹽源鎮謀劃的鄉村旅游里,也許會產生另外一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