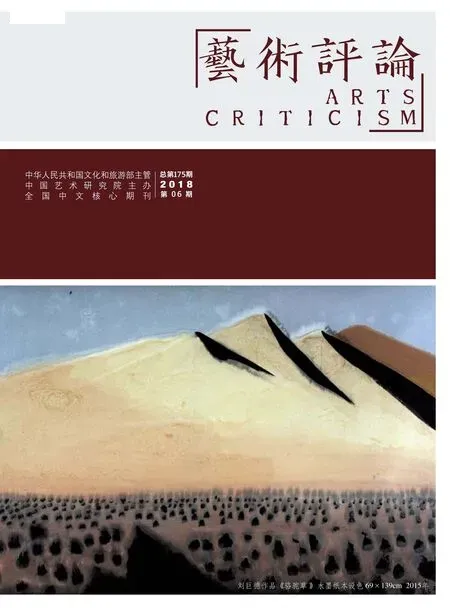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電影表演學派漸行漸近
厲震林
[內容提要] 回首改革開放40年,中國電影表演以自己的激情與沖動,結合洶涌而至的國內外各美學潮流,戲劇化、紀實化、日常化、模糊化、情緒化、儀式化和顏值化表演美學思潮輪番“粉墨登場”,在表演觀念上都有著開創(chuàng)性思維的歷史階段意義。在一種“糅合”和“雜交”的文化方式中,呈現出表演的價值觀、兩次“去戲劇化”表演思潮、二次結構主義表演美學等電影現象。電影表演以一種“變法”的主體意識,逐漸觸及中國電影表演學派的底色部位,從中國實踐、中國經驗到中國理論,電影表演學派已經到了需要命名和定義的時候。
一
改革開放40周年,內心充滿一個感慨:如此盛世,如你所愿。它使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都超過了自己的預期。從小農經濟到市場經濟,從人文政治到生活方式,從國際地位到國族認同,這是兩千年以來中國社會轉型最為巨大的時期,在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后,驚如天作。40年,中國走過了其他國家一百年以及二百年的歷程,驀然回首,中華民族復興從來沒有如此之近。
中國電影以自身的方式親歷其間,并迅速站立前沿部位,掀起中國新電影美學運動思潮。從開始的文化精英主義,到中途的文化世俗主義,到后來的文化商業(yè)主義,到現在的文化浪漫主義,40年間電影已然成為中國文化的領袖者、記錄者、抒情者和娛樂者。它既自身受到時代的政治動力所驅動,或立于潮頭,或深度呼應,或負重前行,或輕裝狂舞,同時,又構成時代的文化動量,對中國文化密碼“基因”以及電影市場進行思潮式、拓荒式、娛樂式以及黑色幽默式的文化“破譯”及其重構。雖然中國電影文化訴求和表述仍然是單面式或者碎片式的,甚至某一時期或者某些作品與文化訴求和表述關聯不大,尚未建立十分清晰的文化原點和出發(fā)點,缺乏成熟而沉穩(wěn)的哲學思想系統,無力形成價值論的意義,還徘徊于方法論的層級,但是,中國電影以自己的文化“指紋”深深鑲入了改革開放40周年的文化“指紋”之中,并在世界電影史學和版圖上開始真正確立了中國電影的國別概念以及形象。
電影表演非表演自身的事情,它關涉其背后的各種顯在以及非顯在的意義,包括文化、政治、產業(yè)以及宣發(fā)方式等,存在著“意識形態(tài)腹語術”功能,可謂一種“時代情緒表演”或者“社會表演”,無法回避時代的規(guī)范性、階段性以及局限性。它不是僅僅關聯于演員的美學選擇以及劇作和導演的技術處理,其被動性和依附性還擴大到時代的整體性格和氣質,優(yōu)質的電影表演往往是時代的假面和表情,頗類似于一種“人類表演學”,在表演邏輯之中體現著“存在(being),行動(doing),展示行動(showing doing),對展示行動的解釋(explaining showing doing)”,呈現為一種“合力”以及“潛表演”現象。從此意義而言,40年的電影表演,也是改革開放的形象史、表情史和精神史,充蘊著充沛的時代人文含量,呈現著激情、茫然和理性等各種復雜而微妙的轉型情感以及情緒。“它既有集體無意識,也有集體有意識;既有時代的‘規(guī)定表演’,時代的氣質規(guī)范了表演的氣質,也有電影從業(yè)人員的‘自選表演’,開創(chuàng)出某些屬于個人的表演形態(tài);既有政治與歷史層面的因素,也有文化和工業(yè)的使然。應該說,表演成為新時期發(fā)展歷史最為生動的形象注釋,是它的一種精神成長影像化,或者說是一種精神形象標本。從某種意義而言,新時期電影表演美學仍然屬于精英文化產物,它也以自己的力量反作用于社會,并且或隱或顯地引領著社會審美趣味,同時,在電影以及電影工業(yè)領域產生一種導向意義。”40年,電影表演經過如許的震蕩、迭宕和淬練、凝結,其優(yōu)點和弱點漸顯出來,并不斷走向中國電影表演學派概念,呼吁它的出生以及成形,從而向中國電影學術界召喚,表演學派已是到了需要命名和定義的時候。
二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電影表演或隱或顯地表述了若干的美學文脈。筆者曾將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電影表演美學思潮分為7個發(fā)展階段:戲劇化表演、紀實化表演、日常化表演、模糊化表演、情緒化表演、儀式化表演和顏值化表演。若以此作為基本原理,則可發(fā)現40年電影表演的中國實踐、價值和理論,其間沉浮騰挪,均是關乎美學,它非直線發(fā)展而是迂回曲折,如同鏟土一般,乃是一左一右輪流使力,不斷地推向完善和目標。在此過程中,主要電影表演美學思潮已然檢閱一遍,其間孰優(yōu)孰劣初步分辯,內中邏輯路線或深或淺呈現,并在博弈狀況之中逐步沉淀成為中國電影表演學派的寶貴質素。
第一,表演的價值觀。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戲劇化表演,乃是傳統影戲表演的慣性使然。只是它與“文革”時期“超古典主義”表演美學比較,已經從“神性”走向了“俗性”,并且,與“十七年”表演方法逐漸接通,作為初期的基本表演“拐杖”以及信念,并逐漸呈現一種開放的態(tài)勢,表演向“意識流”等精神領域拓進。自然,這一時期,表演處在電影美學的中心地位,盡管導演意識已經“初醒”并強化了對于表演的美學控制。80年代中期的紀實化表演既是對于戲劇化表演的反撥,“技巧美學”的“花里胡哨”表演已為業(yè)界和社會所厭倦,也是響應“實事求是”政治潮流的文化行為,在巴贊、克拉考爾“紀實美學”理論的“掩體”保護之下,強化了表演與生活的契合度,使表演的各個元素“類生活化”。此時,表演仍然是電影美學的核心成分。日常化表演,則開始驅逐電影表演的中心地位,認為表演只是電影系統語匯的成員之一,而且,表演只有在整個畫面甚至整個影片中才能產生意義,屬于結構主義的美學功能,表演失卻了中心地位的絕對權力。
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紀的模糊化表演、情緒化表演、儀式化表演的三個發(fā)展階段,則又將表演引向了各自的美學方向,從表演的不同側面、方位以及功能進行了本體探索,與哲學、社會和產業(yè)層面或者平臺產生文化對接。模糊化表演,是模糊的“中性”表演,企圖達到人性學和人類學的層面,使表演產生一種文化的整體把握和哲學體悟,“有意識地尋找多義和復合的表演內涵,發(fā)現空白并讓觀眾裹卷進來,體驗角色的‘復合情緒體驗’,并逐漸發(fā)展到在整體性象征上與影片發(fā)生全域化的聯系和深度化的‘深觸’”。90年代的情緒化表演,則是緣于俗稱“第六代”導演集團的特定電影題材及其風格,使電影表演“自由嬉戲”,通過情緒勾連表演邏輯,演員在一種迷茫的精神追求、混亂的情感糾葛、瑣碎的細節(jié)描寫以及俚語臟話式的臺詞包裝下本色表演。新世紀的儀式化表演,使表演再度進入結構主義美學體系之中,表演成為“東方奇觀”及其“圖譜”的主要元件,于“大色塊”與“大寫意”的奇觀電影景象中,呈現出一種大開大闔的儀式化表演方法。上述三種表演美學思潮,表演既不是如同戲劇化表演一樣成為中心地位,也不是類似紀實化表演一樣去中心化,而是根據各自的美學目標進行選擇和塑形,與中心部位若即若離,時而緊密,時而散淡。近年來的顏值化表演,顏值成為電影美學中心動能,甚至是非顏值表演不能成事。它似乎又回到戲劇化表演階段,表演成為影片中心地位,只是它與美學無關,只是票房號召力量。
由此,40年來電影表演頗是“繞了大圈”,從表演的中心地位,到去中心化,又蔓延到不同的拓展分析,或模糊,或情緒,或禮儀,最后折回原地,表演又是中心神話,只是物是人非,同是中心權威,美學面貌已是不同,戲劇化表演尚關注表演自身,而顏值化表演所選擇的已非表演而是明星。電影表演經歷如許迭宕,可謂“閱潮無數”,冷暖自知,理性狀態(tài)漸次展開。2017年,可以表述為“電影表演美學現象年”,《演員的誕生》《聲臨其境》《今日影評·表演者言》等一批表演類綜藝節(jié)目,成為“現象級”的社會熱點,并涉及到對表演藝術的再定義、對表演美學的再認識以及對演員市場價值的再評估,表演美學進入科學理性的反思和總結階段。
第二,兩次“去戲劇化”表演思潮。電影表演與戲劇表演恩冤日久。其恩而言,電影表演乃是在戲劇表演的扶持以及“營養(yǎng)”滋潤之下成長起來的,影戲表演是中國電影表演傳統之一,但是,到了紀實化表演階段,為了保持與“原生態(tài)”生活的親近度和鮮活度,一些編排痕跡過重的戲劇性表演橋段被拒絕了,甚至當時有一種觀點認為,電影表演的虛假和做作,皆因戲劇表演影響所致以及使用舞臺演員而成,其冤日顯。其實,“小劇場戲劇已在戲劇界漸成思潮,追求表演自然化也是戲劇的改革方向之一,故而話劇舞臺上的許多表演形態(tài)已經較為生話化,在銀幕中進行生活化表演探索的演員,許多也是來自戲劇院團”,但是,頗耐玩味的是,當時電影導演仍然大膽啟用舞臺演員,許多經典影片乃是舞臺演員杰作。看來問題并非“電影與戲劇離婚”如此之簡單。此為第一次“去戲劇化”表演思潮發(fā)端,一些戲劇化色彩較重的表演方法受到排斥,而追求“生活化表演探索”。在此基礎上,日常化表演走向了極至甚至“暴力”的“去戲劇化”,從表演的表現形態(tài)、再現形態(tài)演化到讀解形態(tài)。因為影片的哲學和文化的寓言效果,戲劇化表演太“實”、太“顯”而無法進入“歷史想像”通道,沖淡“整體”文化信號的平衡度、建構力以及發(fā)散性,因而采用了“全表演”或者“大表演”概念,所有顯在和非顯在的視聽信息均為表演,演員只是其中成員之一,其表演也被要求非戲劇化的日常化。第二次“去戲劇化”表演思潮發(fā)生在情緒化表演階段,為了實現“原在感受”和“目擊現實”的文化原則,演員表演需要“最大限度地還原劇中人物自身的職業(yè)特點”,表演如同未經加工過的毛坯,或者說是像是即興截取劇中人物生活的某個段落,甚至沒有什么前因后果和來龍去脈,就這么開始,就那樣結束,“去戲劇化”也就成為一種必然選擇。
二次“去戲劇化”表演思潮,“非職業(yè)表演”都成為它的重要“附件”。第一次是從氣質角度選擇具有性格美感的非職業(yè)人士,而非外貌更為優(yōu)越的職業(yè)演員,使角色形象更加“普通人”化。在具體表演處理中,也是高潮戲低調法處理,讓非職業(yè)演員感受多少表演多少,甚至在一些民俗場景中,表演與非表演界限都難以區(qū)別了;第二次個別導演則公開反對使用職業(yè)演員,認為他們無法承擔自己“類紀錄片”風格的影片表演,職業(yè)演員控制力強和臺詞處理性好,難以呈現情緒化表演的現實生活質感,非職業(yè)演員的本色化和真實化,較少出現有著電影經歷和記憶的程式化表演,甚至他們不是在表演而只是按照生活中本來的行為在做,“去戲劇化”強化了電影表演的現場感和真實感。
如此表演思潮,與中國人的表演接受經驗以及習慣有著一定差距,“不過癮”“太平淡”也就成為一種普遍觀感,在市場上不太受人待見。但是,“去戲劇化”表演思潮,彌補了中國影戲表演傳統的某些缺陷和“軟肋”,從一種“異質”角度補充和豐富了中國電影表演“肌體”,在一種互為對峙、妥協和交融中使中國電影表演美學“強身健體”。
第三,二次結構主義表演美學。它的基本特征,即表演的非獨立性,而是與其他電影元素結構關系中才能確立意義,甚至才能確立角色身份,個體的角色表演是貧弱的。如前所述,日常化表演是第一次,表演納入音畫語言“集體表演”中,主角未必是演員而可能是靜態(tài)畫面、空鏡頭或者空白畫面。陳凱歌在《〈黃土地〉導演闡述》中對演員表演作如此要求:“我們的影片只有四個人物,如果分別去描繪四個人物的性格基調本用不了許多篇幅。但我不打算這樣做,尤其不想向你們說明你們將分別擔任的角色各自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他們是什么人,將最終由你們呈現于銀幕上的形象來完成。我的任務不過是把你們扮演的角色置于各自適當的位置。”它包含了三層意思:一是“分別擔任的角色各自是什么人”,并非劇本中所描述的這般簡單,而是“翠巧是翠巧,翠巧非翠巧”;二是“他們是什么人, 將最終由你們呈現于銀幕上的形象來完成”,角色表演因結構而意義;三是“我的任務不過是把你們扮演的角色置于各自適當的位置”,導演將著力于音畫語言“謀局布篇”,使表演置于最合適以及最具表現力的位置。儀式化表演是第二次,只是它與日常化表演的文化出發(fā)點不同,日常化表演是指向哲學和文化,是屬于寓言系列的,儀式化表演則是技術和市場,是隸屬奇觀系列的。儀式化表演的結構主義表演美學,是面對世界市場以及吸引國內觀眾回歸影院的,它也是縵渺奇觀的“點睛”之筆。二次結構主義表演美學,市場待遇頗殊,前者寂寥,后者紅火,但是,在表演觀念上都有著開創(chuàng)性思維的歷史階段意義。
三
中國電影表演自初創(chuàng)以來,可謂披荊斬棘,歷經變革。它的初期,表演源流五“方”雜陳,背景各異。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電影表演方有初步美學面貌,已有經典韻味,可供學術評述,歸結為影戲表演傳統以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劇體系的理論基礎。此后數十年間,雖有《小城之春》之類影片的個案呈現與中國民族演劇表演體系之提出及其實踐,然而,表演美學整體變化不大,基本屬于一以貫之,有表演的絕響、高峰以及思想,也有表演的局限、缺陷以及遺憾。直到改革開放,40年之間,中國電影表演觀念之門大開,國內外各美學潮流洶涌而至,輪番“粉墨登場”,如前所述的戲劇化、紀實化、日常化、模糊化、情緒化、儀式化和顏值化表演美學思潮,中國電影表演從來沒有思潮如此之迅疾、變幻和猛烈的時期,談不上成熟以及來不及消化,已然走過其他國家百年之歷史。回首40年,中國電影表演以自己的改革開放激情與沖動,在一種“糅合”和“雜交”的文化方式中,使中國電影表演美學有所附麗、豐富和壯大,也成為改革開放的中國社會史和中國精神史重要的一部分。
在如此文化轉型的過程中,電影表演從來未曾放棄過自身的主體意識,以一種“變法”精神以及勇氣,使表演表現的美學領域加深、加寬和加魅,并逐漸觸及中國電影表演學派的底色部位。雖然電影表演缺乏充裕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為導演美學追求以及劇作題材所限定和規(guī)范,演員表演仍然以變革的情懷,配合和深化了電影美學的發(fā)展潮流,成為它的標識和符號。戲劇化表演階段,處在影戲表演傳統慣性作用之下,潘虹、斯琴高娃、劉曉慶等演員強力拓展了表演的生活化和內向化以及深度和跨度,并且,在導演美學的帶動之下,形成一種開放性表演觀念,幻覺、意識流和生活流表演頻顯,甚至重場戲沒有一句臺詞的表演方法,顯示了改革開放初期電影演員的主體精神。紀實化表演,雖然要求演員表演“原生態(tài)”化,將戲劇化場面壓淡壓淺,張豐毅、岳紅、辛明等演員仍然在細節(jié)處理中顯示個性化和獨特性,產生一種“潛戲劇性”效果以及美學韻味。日常化表演,是演員表演主體性最被壓抑階段,表演依然充分地表現了第一任務和第二任務的結合,或者近景任務和遠景任務的結合,呈現出一種穩(wěn)定和沉著、凝重和安靜的詩意力量。模糊化表演,是演員主體最為張揚的表演類型,倡導人之一劉子楓稱:“模糊表演是以清晰的指導思想,表現出模糊的中性的感覺、狀態(tài)、情緒、表情等,以達到在觀眾中引起多含義、多層次的感受和聯想,決不是糊里糊涂地表演,還是演員有意識的創(chuàng)造。為了達到模糊表演的效果,我注意在三個方面下功夫:一是想一想戲發(fā)展到這里,我應當是什么感覺、什么情緒,二是想一想同一畫面中,別人會怎么演,我要找出不同的演法來,三是估計觀眾此刻會怎么想,他們這樣想,我盡可能不這樣演,讓他出乎意料,讓他感到難以言傳卻感受深刻。”此等主體意識清晰而又堅定。情緒化表演,由于“去戲劇化”的表演格式,演員不能過多地借助于表演技巧方法,其自身氣質以及對于內心精神的表達也就成為關鍵所在,是表演魅力的主要承載要素。耿樂、趙濤等仍能夠較好地處理藝術表演和生活表演的關系,在融為一體中生成韻味。儀式化表演和顏值化表演,雖然被導演美學和資本逐利所裹挾,然而,許多演員或功力或本色使表演加魅化,頗有東方表演韻味以及青春時尚氣息。近年的“電影表演美學現象年”,表演美學已然呈現理性,是曲折之后的科學歸總和確立方位之探索行為。
這40年,也可看作演員表演的主體意識發(fā)展史,從被動性到主動性又到被動性最后到主動性,從表層到深層又到多元最后到理性,從少學術性到濃學術性又到薄學術性最后到厚學術性,電影表演從依附和裹卷中突圍而出,多方探路辨別方向,積蓄能量漸成大觀,具有東方神韻或者風情的中國電影表演學派已經初顯。從中國實踐、中國經驗到中國理論,表演美學已經到了需要命名和定義的時候。誠如周星所稱:“關于華語電影、華萊塢電影、廣萊塢電影、第三極文化(電影)、大電影等很好的創(chuàng)意,都充滿了對于中國電影需要到梳理規(guī)范、確立旗幟階段的明確意識和積極努力,但除了要超越地域局限、避免以偏概全和減弱對于好萊塢模仿等等的不足外,需要更有傳播的響亮度、概括的恰當性和內涵的凝聚性的稱謂,又能夠和國家響亮的名字掛鉤,對中國電影本身整體性的概括,在有研究性的概括加以標志性的同時,也是真正的能足以代表中國電影的最核心的內容,而形成的學派理論體系的一種闡釋結果。”表演學派不是表演流派,它不是局部或者單一的某種電影表演美學思潮的概念指稱,而是一個國家置于世界范圍之內的獨具一格的電影表演文化觀念、風格和氣質,是一個廣義、整體和概括的概念,有著更為宏大的國家文化形態(tài)的指向;表演學派必須具有醒目的獨特性和標志性,要產生概括的恰當性、內涵的凝聚性和傳播的響亮度的稱謂,能夠和國家響亮的名字緊密關聯,是對中國電影表演本身整體性和標識性的概括,足以代表中國電影表演的最為核心的文化內容;表演學派也需要使觀眾、批評家以至國際都能認同尊崇,既在國際上醒目,又能在國內凝聚,成為中國電影表演研究聚焦的重心與創(chuàng)作的主導趨向。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電影表演美學已成如此基礎,上述論述即是一個案例。40年之偉大意義,世界已有認知,40年表演美學所蘊含的內在價值,學術界也應該有著充分認知,已是“需要到梳理規(guī)范、確立旗幟階段”,出現“傳播的響亮度、概括的恰當性和內涵的凝聚性的稱謂”。
注釋:
[1]〔美〕理查·謝克納.什么是人類表演學——理查·謝克納在上海戲劇學院的演講[J].孫惠柱譯,戲劇藝術,2004(5).
[2]厲震林.中國電影表演美學思潮史述(1979-2015)[M].中國電影出版社,2017:21.
[3]厲震林.模糊表演的歷史任務及其文化邏輯分析[J].當代電影,2013(6).
[4]厲震林.再談“電影與戲劇離婚”[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8-25.
[5]賈磊磊.關于中國“第六代”電影導演歷史演進的主體報告[J].當代電影,2006(5).
[6]厲震林.論日常化表演的文化和美學[J].當代電影,2016(5).
[7]張仲年、劉子楓、任仲倫.模糊表演與性格化的魅力——趙書信形象塑造三人談[J].電影藝術,1986(6).
[8]周星.建構中國電影學派:傳播視域的概念探究與其適應性[J].現代傳播,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