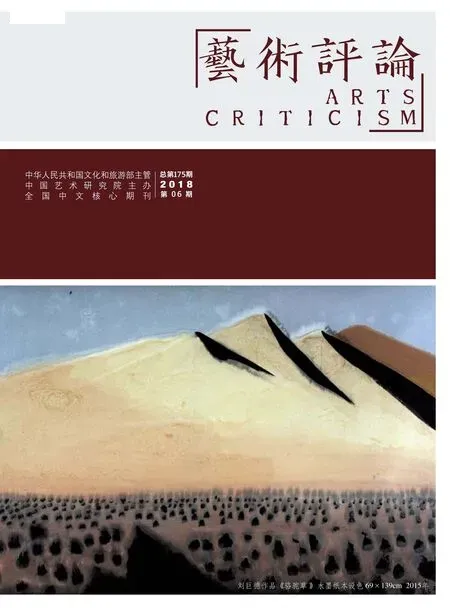以資助促進創作 以引導促就精品
——國家藝術基金資助管弦樂的四年來情況分析
王安潮
管弦樂創作以純器樂語言為主,屬于純音樂藝術的范疇,是音樂創作技術涵量最為集中的音樂體裁所在。它的創作繁興與否是衡量國家音樂創作水平的重要評價技術參數所在。西方維也納古典時期的海頓、莫扎特、貝多芬等所代表的管弦樂創作的巔峰及其對之后音樂發展的影響即是例證,其后,各國以民族音樂為題材而展現出浪漫樂派時期色彩斑斕的民族樂派是其發展,如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門德爾松等。我國的管弦樂創作肇始于20世紀30年代,蕭友梅的《新霓裳羽衣曲》、黃自《懷舊》等是早期探索的代表。由于鄭瑾文、聶耳、劉天華等以西方管弦樂對聲響為基礎而進行的民族管弦樂建構以及由此而改編的《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等成功作品,所以,后來人們在討論管弦樂時也將其納入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西方或民族的管弦樂創作更是呈現出勃發之勢,題材與風格層出不窮,《梁祝》《黃河》《紅旗頌》與朱踐耳的“十部”交響樂、劉文金的《長城》、趙季平的《和平頌》等作品已深入人心。
國家藝術基金資助管弦樂創作的四年來,從外在文化環境的營造、內在文化自信的激勵上對管弦樂創作予以促進,被資助的項目包羅萬千,西方管弦樂有53部,民族管弦樂有54部,申請者既有專業樂團的作曲家,也有專業院校的作曲教授,年齡結構也涵及老中青三代,可以說是最大范圍地影響了中國管弦樂創作。從2014年資助的傳播交流推廣項目《印象·國樂》、舞臺創作項目交響合唱《木蘭詩篇》等7個項目以來,2015年有舞臺藝術創作資助項目交響樂《七闕西湖》和民族管弦樂《絲綢之路》、傳播交流推廣資助項目交響詩篇《土樓回響》和民族管弦樂《巾幗三部曲》等25項,2016年有舞臺藝術創作資助項目交響樂《王羲之》和民族管弦樂《黔韻華章》、傳播交流推廣資助項目室內樂《五行》等21項,2017年有舞臺藝術創作資助項目交響樂《原野》和民族管弦樂《山水重慶》、傳播交流推廣資助項目民族管弦樂《國之瑰寶》境外巡演和交響曲《人文頌》巡演等28項,整體上呈逐年增加之勢。尤其是隨著資助所產生的廣泛社會影響,越來越多的行業開始加入到國家藝術基金申請的行列中。從項目種類來看,有以優秀創意為資助對象的“舞臺藝術創作項目”,有以成形的優秀作品為資助對象的“傳播交流推廣項目”,在新創管弦樂中,近年來還增加了跨界融合類,打破中外音樂體裁間甚至古今音樂種類間的壁壘,使藝術作品服務人民大眾的理念更為深入,“舞臺創作”與“傳播交流”是2種主要資助的對象,此外,從2014年的交響樂青年指揮人才培養項目資助開始,以后逐年增加人才培養項目,涉及中外樂隊指揮、合唱指揮、二胡和古琴乃至室內樂演奏人才的培養領域,是實際解決演繹人才的具體之策。資助對象有著題材與體裁多樣性,種類與風格豐富性,高峰精品創演的前瞻性,并有資助與激勵、引導相結合,切實盤活中國管弦樂發展的良性機制。其中,尤為值得點贊的是對古琴藝術的資助項目,據不完全統計,已有如下古琴項目:由臨沂大學申報的2017年度藝術人才培養資助項目的“諸城派”古琴表演人才培養項目,由洛陽師范學院申報的2017年度藝術人才培養資助項目“中州派古琴藝術表演人才培養”,由諸城市文化館申報的2015年度傳播交流推廣資助項目的“絲竹古韻遍華夏——諸城派古琴展示活動”,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申報的2018年度傳播交流推廣資助項目“古琴音樂展演”的單獨項目,從人才和演繹兩個視角對這一中華傳統優秀經典文化予以鼎力發揚,此外,還有 2015年度青年藝術創作人才資助項目“民族器樂三重奏《琴賦》——為古琴、笙及打擊樂而作”,2016年度青年藝術創作人才資助項目工藝美術創作《漆藝古琴》及工藝美術創作《金漆錯古琴》,2016年度傳統古琴制作技藝傳承項目工藝美術創作《古琴》,2016年度傳播交流推廣資助項目“乘物游心——中國古琴藝術與當代生活展演”,2017年度青年藝術創作人才資助打譜項目《古韻新釋》及工藝美術創作項目《古韻今聲》,2018年度青年藝術創作人才資助項目古琴交互音樂與中國傳統文化《蓮語》等創作類項目,而像有些項目中牽涉有古琴的,如2014年度傳播交流推廣《印象·國樂》、2015年度跨界融合作品《又見國樂》、2018年度的民族器樂劇《玄奘西行》等,也都助力了古琴傳揚,這在同類民族樂器中是沒有的!可見,國家層面的發揚政策對經典文化自信心營造的側重所在,也可見基金管理者用好資金的全局觀、調配度之所在。
一、藝術基金以多元立體模式支持管弦樂發展
(一)多題材、多風格的藝術作品創作
國家性的創作選材有助于引領作曲家的藝術方向,通過四年來的基金資助工作推展,作曲家們將關乎國計民生的題材和風格納入其創作的主要考慮之中。其特點之一是對國家重大文化策略主題的側重,如近年來的“一帶一路”文化題材就在每一年的立項有一定份額,如:2014年的民族樂劇《印象·國樂》、民族管弦樂《絲路長安》,2015年的民族管弦樂《絲綢之路》、交響樂《海上絲路》,2016年的民族管弦樂《絲路草原》、交響樂《梵天凈土》、跨界融合舞臺劇《夢回敦煌》,2017年的民族管弦樂《絲綢之路的回響》、交響樂《敦煌》和《海路的交響》、音樂會《絲綢之路》巡演,2018年的民族管弦樂《意象絲路·龜茲盛歌》、交響樂《絲路追夢》巡演、民族器樂劇《玄奘西行》英國日本巡演等,不同角度的“絲路”主題展現了各具特色的音樂風格,是對國家文化主題的詮釋。其特點之二是文化自信語境下的經典民族主題的眷顧,如2014年的交響合唱《木蘭詩篇》和《朝陽溝》表現的是古今兩個文學經典題材,2015年的交響樂《七闕西湖》《紅樓夢音樂傳奇》《霸王別姬》、民族管弦樂《孔子》《富春山居圖隨想》,2016年的交響樂《王羲之》《上善蜀水》、民族管弦樂《孫中山》、室內樂《五行》,2017年的交響樂《原野》《唐詩之路》、民族管弦樂《國之瑰寶》《孫子兵法回響》、跨界融合作品《中國十二生肖》,2018年的交響樂《中華神話交響曲》《良渚》《霸王別姬》、民族管弦樂《瀟湘水云》、民族器樂劇《玄奘西行》、跨界融合作品《九歌》等,習近平總書記認為中華經典文化是民族長期以來的積淀,是文化自信生發的基礎,以管弦樂的形式利于表現深層次內涵。其特點之三是地方音樂風情的展現,如2014年民族管弦樂《遼南暢想》,2015年的交響樂《土樓回響》《琴島序曲》《云中君》、民族管弦樂《山西印象》《情醉關東》《巴渝風》、跨界融合作品《秘境云南》,2016年有交響樂《彝歌》《長白音畫》、民族管弦樂《黔韻華章》《追夢京華》《絲路草原》,2017年交響樂《社戲》《家鄉的花兒》《草原意象》、民族管弦樂《山水重慶》《高粱紅了》,2018年的交響樂《金陵交響》《重慶組曲》、民族管弦樂《大河之北》《錢塘江音畫》《黃河從草原走過》《長白美眷》《八桂音畫》等,地方音樂的特色是管弦樂重要的選材,藝術基金對此投入較多的份額。不同的文化題材或地域風情會選擇相應的音樂素材,由此而構建了題材多樣的管弦樂風情畫卷和風格多樣的音樂情趣,裝扮了申報人所在地,并以管弦樂而展開地方文化的影響。
(二)多手法、多情趣的藝術創新探索
在當前的管弦樂創作中,借鑒古今中外的音樂手法從而形成情趣多樣的音色音響,是作曲家們探索創新之所在。在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無調性、序列音樂手法在基金所資助的作品中已較為理性地運用,更多地則是依據作品內容表現的需要而進行調性手法的共性寫作,這種理性尤其表現在學院派作曲家身上,而駐團作曲家更是以調性音樂寫法而深入發展更易為大眾所接受雅俗共賞之作。如中國交響樂團作曲家關峽創作的交響合唱《木蘭詩篇》以《樂府詩集》中的《木蘭辭》為戲劇性結構的連接部,將古代歌謠的簡樸五聲性旋律在詠嘆、宣敘、戲劇或舞蹈等場景中予以不斷展開,以抒情的單旋律為主的段落與以緊張的多聲部疊置為主的段落交錯發展。軍旅作曲家張千一創作的《大河之北》以河北豐富的民間音樂為素材,以特色民族樂器為引領,從而構建了七個樂章錯落有致的張弛布局,給人以音色音響豐富的純音樂藝術的地域風情畫卷。中國廣播藝術團作曲家莫凡為表現有教無類、仁政大同的文化主題,并進而展現博大精深的孔子哲學思想,借鑒雅樂音階調式而構成其旋律的特色,并以山東曲阜等地的特色性民間音調而表現,從而在音樂的歷史特征與地域個性上展現出特有的音調。注重鮮明的音調也是學院派作曲家在基金項目作品創作中的主要手法選擇,上海音樂學院作曲家許舒亞創作的《海上絲路》以時間的發展為脈絡,站在宏大的歷史視角看待海上絲路從古至今的發展延續,用音樂展現人文與自然、歷史與現代、民族和世界的對話、交融,融合多種音樂技法和不同流派的音樂元素,如多調性、音塊、音束、簡約主義、電子音樂、流行音樂等,使其閃耀時代色彩,讓更多的聽眾容易理解和接受(云亦云語)。上海音樂學院作曲家周湘林、葉國輝、張旭儒、趙光、尹明五聯合創作的《絲路追夢》構建一條從長安出發而通往西方的音樂“絲路”,作品以“絲路”沿線的地域或歷史音樂素材而構建了一個大美、動聽的旋律,多聲音樂為大開大合的旋律烘托了厚重的背景,這種古今中外音樂手法的融合,使所追的“絲路”之夢蕩氣回腸、恢弘大氣。中央音樂學院作曲家張小夫以西藏文化為主題創作的大型舞臺藝術作品《梵天凈土》并未強調現代作品中旋律的碎片化,而是以母語的獨特,展現了現代理念與傳統原則的并存,現代音樂所擅長的神秘悠遠意境描繪而強化的感官的直接刺激,女高音優美飄逸的歌聲令人陶醉,中國音樂學院作曲家金平評價說:作品聽不出所謂的現代或傳統的痕跡,優美、順暢的旋律聽著很走心。四川音樂學院作曲教授宋名筑以西南彝族民族民間音樂元素發展出的《彝歌》具有優美動聽、色彩豐富的弦樂旋律,即使在普通中小學演出也一樣深受歡迎,足可見這位擅長多調性的實驗音樂寫作的作曲家在藝術基金資助下的手法轉變,“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方向使作品充滿了多樣的情趣。
(三)多途徑、多思維的管弦樂環境營造
正是由于參與的創作者眾多,也就使作品的呈現形式多樣,管弦樂中既有傳統的四樂章交響樂、單樂章管弦樂,也有多樂章管弦樂組曲或交響組曲,還有小型編制的管弦樂甚至各種編制的室內樂,近來,還增加跨界融合類項目,以多藝術形式的綜合而增加表現形式的新穎性,從資助數量上看,各種藝術種類的比例份額也在不斷變化,以多種管弦樂音樂形態的思維而來營造豐富的純音樂藝術情境。如2014年的7項中,有2項是“傳播交流”類,4項為“舞臺創作”類,這其中,除了對已廣為人知的《印象·國樂》進行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交流推廣外,“中國民族音樂世界推廣及數字化整理”是一種新的音樂推展途徑,它的廣度、深度及其由此而衍展的范圍是國家性項目所應有的視野寬度。而民族管弦樂《絲路長安》由“絲綢之路”始發地西安所創意,它所營造的環境更是別有用意。在此管弦樂創作環境之下,2015年有17項“舞臺創作”類立項,而藝術表現的途徑則更為豐富多樣,展現了管弦樂強大的表現視域。在這一背景下,更是催生了很多院團的創造力,很多沒有管弦樂創作的院團發現了此中機遇與樂趣,如北京曹雪芹學會、廣西歌舞劇院有限責任公司,而新疆藝術劇院民族樂團更是在此環境下催生《絲綢之路》這一已成名篇的單樂章民族管弦樂,山西省歌舞劇院有限公司經過充分調研而創演的多樂章民族管弦樂組曲《山西印象》也已成為山西的文化名片,上演于國內外很多舞臺。在藝術產生的途徑上,除了管弦樂院團申報外(第一屆全部是),專業院校、民辦樂團或文化公司都參與到這一申報的隊伍中,他們精心的準備,為精品的推出鋪設了道路,并由此而良性循環,優化了管弦樂發展環境。藝術呈現途徑的變化引發申報途徑的多樣,并進而營造管弦樂發展的良好途徑,這是既往以專業院團創作主體背景下難以見到的情景,從中可見國家藝術基金項目的廣泛影響力。
(四)多領域、多視域的管弦樂機制探索
多方參與創演,必將引發多種表現角度的管弦樂創作現象,由此而促進管弦樂創演機制的探索。其一是變被動為主動,以前的創作是單位領導或上級領導下發創作任務,作曲家再進行管弦樂創作的情況居多,在這種機制下,常會因排演而趕工期,可能會掣肘創作質量,而那些專業院校中的創作之所以常比院團中的作品質量高,就在于其主動創作所致;而藝術基金機制下的創作都是已有成形的作品,并且經過專家的遴選及其立項后的指導修整,是優中選優,再優勢互補,這就在變被動為主動創作中形成了管弦樂——這一高技術含量的藝術作品的有效機制。其二是變一元為多元,以前的創作主體以院團為主,文化管理者尋求創作時也想不到他者,在藝術基金資助語境下,只要有創作能力的單位或個人,不論官辦還是民辦的,均等同視之,這就為需要更多藝術創新因素的管弦樂創作奠定了精品產生的良好機制。而管弦樂發展所需的人才培訓項目,也是只有這樣的機制才能蓬勃發展,為青年管弦樂人才的培育奠定了基礎。
國家藝術基金項目以多元立體的模式資助那些樂于為中國管弦樂發展傾力奉獻者,而優越的資金和優良的精品培育環境及其機制,為高技術含量的純音樂藝術產生創造了條件。
二、藝術基金以高峰促高原的管弦樂資助思維
(一)大局觀與特色觀
應對管弦樂發展的不同領域,將創作的激勵、作品的展演、新形式的探索及創演人才的培育等進行全局通盤考慮是國家藝術基金各申請類別設立的大局觀所致。在舞臺藝術創作資助項目大型劇和作品類上,主要意在支持原創性管弦樂藝術作品,意在從源頭上引導管弦樂創作,激發舞臺藝術作品創作的熱情。如2016年度大型舞臺劇和作品創作資助項目交響樂《王羲之》,在立項成功后,作曲家葉國輝精心籌備,不僅在創作上精雕細琢,還在演繹上網羅名家,以亞洲第一男中音廖昌永、中國竹笛女神唐俊喬為領唱、領奏,并要求世界著名交響樂團捷克國家交響樂團,在上海國際藝術節的平臺上華美首演,使作品所表現的行書之父王羲之的飄逸、俊美的藝術風骨得以完美顯現,這種大局觀統籌下的資助思維,為精品的產生創作了條件。而對于像交響樂《長白音畫》所展現的東北風情的十個篇章、“音樂素描”手法的《山水重慶》所展現八個篇章等,都是以特色而凸顯了創作中對源頭資源的挖掘,激發了創作熱情。在傳播交流推廣類項目中,基金資助思維在于推動藝術品的傳播交流推廣,尤其資助那些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優秀藝術作品“走出去”,通過或能彰顯深厚民族音樂文化或能突出特色民族音樂風情的作品而來影響觀演者。如中國歌劇舞劇院民族管弦樂音樂會《國之瑰寶》在“2017年中澳旅游年”開幕式上特色呈現,使悉尼觀眾直面見識了《春節序曲》《金蛇狂舞》《漁舟唱晚》《牧民新歌》《看秧歌》《夜深沉》《梁祝之化蝶》《年年有余》等最具中華民族音樂特征的作品,領略了竹笛、板胡、古箏、二胡等樂器的風采,給予觀者以極大的藝術美沖擊力。上海交響樂團在具有80年歷史的琉森音樂節所交流的中國聲音,讓國外同行見識了阿龍·阿甫夏洛莫夫首演于1933年的交響詩《北平胡同》和柴可夫斯基《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以及肖斯塔科維奇《d小調第五交響曲》,顯示了用世界音樂語言進行詮釋的能力,引起了包括著名作曲家潘德列茨基及挑剔的德國觀眾的贊譽。在“藝術人才培養”上注意旨在提升藝術人才的專業能力建設,為藝術創作在關鍵環節和薄弱環節上培養創作人才,如2014年由中央歌劇院主辦的交響樂指揮人才培養項目、2016年由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主辦的中國民樂指揮人才培養等,在后者的結業音樂會中,曹波、肖超、高偉等18位青年民樂指揮逐一登臺展現了培訓后的藝術風采。在傳統樣式的創新性發展上,對跨界融合類項目的資助使些藝術性高、新穎別致的跨藝術種類的管弦樂作品得以突出,此類項目有逐年增加之勢。如:2015年玉溪市文化管理服務中心申報的《秘境云南》,2016年甘肅省歌劇院申報的舞臺劇《夢回敦煌》,2017年中央音樂學院申報的《中國十二生肖》、上海音樂學院申報的《笛韻天籟》,2018年湖南省歌舞劇院有限責任公司申報的《九歌》、上海音樂學院申報的《東去西來》等,不同藝術形式與管弦樂的融合并舉,讓觀眾看到了新穎之美,綜合之美,使管弦樂的特色更為凸顯。
(二)人民性與藝術性
管弦樂相對其他音樂形式來說要稍微“高冷”一些,也難免使作品的藝術品位過高而拉遠了與大眾審美的距離。國家藝術基金在資助中特別注意雅俗共賞的視角,這就使創作既要有優美的可聽性,也要有深遠的韻味美,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理念下,將作曲家個性隱于藝術美的包容之中。當然,這也在四類不同類別中略有不同側重。如:國家藝術基金2015年度資助的呂其明的《使命》基于共產黨歷史發展而寫的紀錄片配樂,在烘托畫面感的基礎上,作曲家將其整合出序、四個樂章和尾聲的六個部分,作品注意頌歌主題的親切可感性和交響性思維的厚重維度,以人民大眾自己胸懷的夢想、弘揚的精神、凝聚的力量,以及排除萬難而發憤圖強的使命感為內容,主題鮮明,音響深邃,較好地體現了人民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統一。正是基于此理念,作品鮮明的主題與切實可感的內容吸引了人民大眾,如交響合唱《朝陽溝》《唐詩之路》《通道轉兵組歌》、交響樂《七闕西湖》《云中君》《霸王別姬》《長城》《原野》《社戲》《家鄉的花兒》《霸王別姬》、民族管弦樂《絲綢之路》《山西印象》《孫中山》《意象絲路·龜茲盛歌》《孔子》等。同時,也通過此類作品的資助,可以看出強調藝術個性與眷顧大眾共性審美的關系是可以契合而非割裂的。
(三)區域性與民族性
區域性和民族性是管弦樂創作中常見的兩個關鍵詞,前者注重特色音調、節律、韻味等特定風格指向性,后者注重普遍的民族音樂語言特征,某些區域性風格的管弦樂創作中,作曲家常會注意特性音程關系、旋律線條、節奏律動等,如民族管弦樂《絲綢之路》在調式音階上特別運用了西域特征的七聲音階與維族調式音程,還因“絲路”的向西延伸而加入了大弗里幾亞音階(弗拉門戈調式)、多利亞音階(印度拉格調式)以及新疆維吾爾木卡姆七聲音階與中東波斯音階的混合,在這一整體風格指向性的基礎上而構成的旋律在節奏的渲染和演奏法的衍展后,使作品呈現出一種具有神秘東方氣息的世界音樂風格特點,作曲家還以古箏刮奏而來表現印度西塔爾琴演奏前的調音效果,用不貼笛膜的笛子來表現羌笛音質,嗩吶也以阿拉伯地方的音色為法。這些地域性的特殊效果的凸顯,展現了作曲家的風格定位。民族性方面如《印象·國樂》同樣以表現“絲綢之路”為音樂主題,但它站在樂器復原的角度,挖掘了壁畫中的琵琶、阮、箜篌、篳篥、雷公鼓、龍鳳笛、蓮花琴、葫蘆琴……其目的是旨在再現古雅華美的樂器、古樸蒼勁的音色,為觀眾詮釋民族音樂的全新體驗(席強),作品中的民族性展現的視野要大,不拘泥于某一地域,而意在凸顯更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音樂文化的歷史厚重感。
正是上述資助理念,才使所助作品展現出較強藝術魅力,除了在演出中深受歡迎外,還在參加國際國內藝術節中斬獲大獎,如第十一屆“國藝節”中有90%以上的獲獎作品來自于國家藝術基金項目資助。而資助思維也促使創作隊伍逐漸鋪展開來,除了專業院團的主體外,近來有越來越多的音樂院校參與其中,而社會上的獨立音樂家也開始涉入。
三、藝術基金以可持續性激勵管弦樂創演機制
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增強需要民族音樂文化的縱深發展,而管弦樂創作無疑是其中重要一環,國家“十三五”規劃中也將民族音樂列入其中,這對可持續性地激勵管弦樂創演機制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而要想做到更進一步切合主題的發展,有以下建議可供參考。
(一)重點突出與新銳鼓勵
從四年來的資助項目來看,對于那些能彰顯民族音樂文化特質的,尤其是能重點突出民族音樂文化風格的作品,是資助的主要對象。如2014年中國交響樂團的交響合唱《木蘭詩篇》、中央民族樂團的民族管弦樂《印象·國樂》,2015年上海愛樂樂團交響樂《使命》、上海民族樂團民族管弦樂《大音華章》、廣西歌舞劇院有限責任公司交響樂《海上絲路》、新疆藝術劇院管弦樂團(新疆愛樂樂團)交響樂《跟著太陽走》等,這些作品凸顯了國家文化的最特色之處,將國家語境納入作品的表現視域之中。而對于那些新穎的項目,也有資助的側重,如2015年中國音樂學院民族管弦樂《意象凈土》、中央音樂學院民族管弦樂《巾幗三部曲》,2016年貴州省黔劇院民族管弦樂《黔韻華章》、中央音樂學院交響樂《梵天凈土》、哈爾濱師范大學交響樂《風與詩》等,它們或有著新奇的音樂手法,或有著奇異的樂境,但都是管弦樂現代性表現中的領域之一,值得鼓勵,代表著國家語境下的全局觀照氣度。
(二)規劃布局與自主研發
既然作為國家資助的項目,宏觀的規劃布局自然必不可少,每年申報工作開展前,基金管理中心都會根據詳細調研而推出申報指南,它們雖然較為寬泛,但卻為申報者提供切實的參照。在此語境下,追求個性展現的自主研發也應在上述規劃布局下展開,有些完全偏離的研發屢試不中,就要重新考慮一下創作的研發是否與規劃偏離太多。從已公布的數據來看,交響樂體裁方向五年來(包括2018年)共有53項,其中,舞臺創作類有34項,傳播交流類有13項,人才培養類有6項;民族管弦樂方向共立項54項,其中,舞臺創作類有36項,傳播交流類有11項,人才培養類有7項。
由上可見,民族管弦樂的立項數及立項率略高于西方交響樂方向,這與參與者多,研發得當有關。從規劃布局上來看,總體上略側重于民族體裁,這也使近年來像《印象·國樂》《絲綢之路》《山西印象》《山水重慶》等作品傳播更廣、深入大眾程度更深,那些“雅”者能立于專家之案頭、“俗”者可進入尋常百姓之家的民族管弦之聲,是規劃布局和自主研發協調發展的結果。
(三)針對性的引導與培育
作為國家藝術基金管理中心,以積極的態度進行針對性的引導與培育,有助于提升作品的質量,端正藝術品位,從而以整體性的藝術品質的普遍提高,而最終健康地發展管弦樂,資助只是手段和途徑,但不是目的,真正的立于世界音樂史之林的經典與資金多寡關系不大。但整體藝術環境的構建,卻是提升創作的必要氛圍。作為創作者,也應針對性地迎合并培育管弦樂創作,將這一創作技術含量更大的音樂形式在藝術性、國家化、現代化的發展上借助藝術基金的幫扶而更好地快速發展,最終在世界民族音樂之林中凸顯特色,占得地位。管理中心的領導和相關評審的專家應主動“走下去”,將申報策略與創作水平的引導,協調并舉,切實推進,對那些有潛質成為精品者,還可以后期滾動資助的形式再行助推,而在項目前期、中期、后期的不同節點,都在節點上予以中肯的引導、指導、督導、檢視,以可持續性激勵機制來助推中國管弦樂的創演。這樣,或能將基金資助的外力化為藝術創作的內驅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構更大的民族音樂文化自信。
此外,對于一些中華傳統優秀經典文化或亟待幫扶的民間器樂體裁,基金的培育之功也是側重而有效的,如前述所言的古琴,以及2018年立項的諸多民間樂種如西安鼓樂,而在一些創作項目中所隱含的傳統器樂素材的項目,其立項本身就可看出培育的引領,這些必將引領管弦樂這一音樂體裁更加良性的發展,將“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宗旨貫徹到實處。